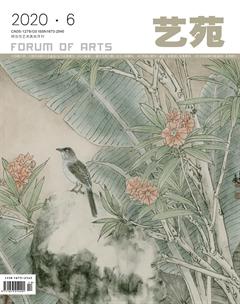“戰疫”題材紀錄片的美學特征
姜常鵬 陳敏南
【摘要】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進行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抗疫大戰。在文藝領域,以呈現真實、啟迪民眾為主要目的的紀錄片成為展現人民“戰疫”事跡、弘揚抗疫精神的極佳文藝形態。近來中央電視臺、各省級衛視均制作播出了眾多以抗擊疫情為題材內容的優秀紀錄片。從呈現形態來看,有單集紀錄片、系列紀錄片、微紀錄片等;但在文本內容里,它們都蘊含了共同的美學特征:崇高美、悲壯美與和諧美,由此真切表達出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
【關鍵詞】 “戰疫”紀錄片;崇高美;悲壯美;和諧美;人民美學
[中圖分類號]J90 [文獻標識碼]A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后,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心,進行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抗疫大戰,付出巨大努力,最終取得了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重大戰略成果,創造了人類同疾病斗爭史上又一個英勇壯舉。[ 1 ]在與新冠病毒的斗爭中,各條戰線的抗疫勇士們眾志成城、艱苦奮戰,彰顯出黨與人民崇高偉大、不懼犧牲、命運與共的精神和理念。而在文藝領域,以呈現真實、啟迪民眾為主要目的的紀錄片成為展現人民“戰疫”事跡、弘揚抗疫精神的極佳文藝形態。中央電視臺、各省級衛視均制作和播出了一系列以抗擊疫情為題材內容的優秀紀錄片,如《同心戰“疫”》《2020春天紀事》《生命至上》《武漢戰疫》《中國抗疫人物故事》《武漢:我的戰“疫”日記》《在武漢》等。就它們的呈現形態而言,有單集紀錄片、系列紀錄片,還有微紀錄片;但從文本內容來看,“戰疫”題材紀錄片則蘊含了共同的美學特征,即崇高美、悲壯美與和諧美,由此真切表達出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以大無畏氣概鑄就的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
一、崇高美:抗疫實踐與精神的能動反映
崇高的美感多源自人類保全自我與他人的沖動。當人們遭遇危險境況和各類沖突時,會自然產生一種以保護自我或他人為目的反抗。[ 2 ] 1若通過反抗斗爭使痛苦與危險得以消除,便會產生歡愉之情——崇高。因而崇高一般是歷經痛苦磨難、克服障礙之后才會顯現,它首先誕生于人類應對沖突、改造世界的社會實踐中,缺少了人民不屈不撓的奮戰和頑強斗爭的精神,崇高也無從談起;在審美領域里,崇高美則是對人的精神與智慧的贊頌,它能夠震撼人心、鼓舞人民。
由此來說,面對新冠病毒的侵襲和危害,通過紀錄片文本真實記錄和呈現人民群眾在黨中央的領導下眾志成城、沖破阻力、構筑起堅固防線并最終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的實踐過程,其本身即具備鮮明的崇高美學特征。例如在六集系列紀錄片《同心戰“疫”》中,第一集《令出如山》以時間為線索展示了疫情出現后面對十分困難的局面,黨和政府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成立中央應對疫情領導小組,果斷及時地做出“封城”決策。之后《生死阻擊》《堅強防線》《眾志成城》《人民至上》等各集文本則分別記錄呈現了醫護人員逆行出征、基層工作人員和普通民眾守望相助、各地支援湖北,直至在與病毒的斗爭中取得決定性成果。通過文本敘述我們直觀看到,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舉全國之力僅用10多天的時間先后建成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346支醫療隊4萬多名醫護人員馳援武漢和湖北,交付700多輛負壓救護車,46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沖鋒陷陣,數百萬快遞員冒疫奔忙等無數宏偉壯舉。
上述一系列事件無疑洋溢著崇高的美學意味,而且數量與力量上的“大”本就是崇高美的基本特點。[3]90如此,“戰疫”題材紀錄片對抗擊疫情斗爭中時間、數字、速度等要素的著重描繪,呈現出的即是典型的崇高美。雖然有的不單是體積的大且不能用計算或邏輯的方式進行推演,但在以視聽影像進行敘述的紀錄片文本里,數量、力量上的生動展示依然能夠直觀喚起人們內心的崇高觀念。況且那些事跡與數量背后是各條戰線的抗疫勇士們歷經痛苦磨難后換來的,有身患漸凍癥依然奮戰第一線的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有共同參加救護工作的劉敦禮、劉凡父女,還有無數各司其職、視死如歸的志愿者、外賣騎手、快遞小哥。因而“戰疫”題材紀錄片中的崇高美是人民抗疫實踐的能動反映,是一種富有深刻內涵的艱難而卓絕的美。
在審美上,崇高是對人的精神與智慧的稱頌和贊美,它能夠震撼人心、鼓舞人民。因為崇高美誕生于人類應對沖突、改造世界的社會實踐中,是歷經痛苦磨難之后才會顯現的精神美感。面對某一新生事物或困難局面時,會由于它們遠超出自己的認知能力而心生恐懼;然而伴隨人們的努力探索和奮斗,對事物的認知逐漸加深,恐懼感隨之消散,斗爭的過程則攜帶了崇高的美感,用以贊美人的精神與智慧。因此,在諸多美學家那里,能引起人恐懼的東西都是構成崇高的因素。就“戰疫”題材紀錄片的內容敘述來說亦是如此,起初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人們發現病毒遠超自己的心理準備,顯得有些驚慌失措。紀錄片《2020春天紀事》的第一集中,流行病學調查員辜潔泥發出感嘆:“疫情來的時候,我們始料不及有這么大的殺傷力”;重癥醫學科醫生尹萬紅在一次搶救失敗后失落地說:“我們真的非常非常想把他給救回來。”經過艱苦的探索和研究,科研人員成功地獲得了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為病毒的檢測診斷和疫苗的研發奠定了基礎。同時經過臨床探索,醫生們提出采用“治療戰略前移”的方案對患者進行診療。紀錄片的第二集接續講述了陳薇院士對新冠疫苗的成功研發;國家疾控中心通過流行病學調查,明確了病毒的傳播渠道。
可見,崇高不在于對象,而在人類自身的奮斗和精神,是人對自身力量勝利的愉快、對自己本身的使命的崇敬。[ 3 ] 1 0 0所以崇高美首先誕生于沖突和抗爭的實踐過程中,是對人的精神與智慧的反映、稱頌和贊美,能夠給人帶來巨大的精神感染力。“戰疫”題材紀錄片呈現出的崇高美學特征充分展現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越性,彰顯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和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能夠增強人民的自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說的那樣,面對疫情,中國人民沒有被嚇倒,而是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壯舉,書寫下可歌可泣、蕩氣回腸的壯麗篇章。
二、悲壯美:對困難與犧牲的抗爭超越
有沖突斗爭就會有犧牲和失敗,若主體被嚴峻的客體障礙徹底壓倒,便會產生悲劇性的意味。亞里士多德指出悲劇引起的憐憫與恐懼能使欣賞者的情感得到陶冶。[2]165朱光潛則認為“崇高”也是悲劇的主要美學特征,只不過這種崇高來自于對失敗的反抗。悲劇雖然源自人類與它者斗爭中的失敗或犧牲,但悲劇意味仍可激勵人心,鼓舞人們繼承他人未臻的事業,與困難抗爭,前赴后繼直至勝利。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數萬名醫務工作者和普通民眾投身抗疫前線,他們不畏艱險,即使面對犧牲、恐懼和失敗也從不怯懦屈從。因此“戰疫”題材紀錄片中的悲劇性集合了悲愴、崇高與壯美,呈現出悲壯的美學風格。
這種悲壯美首先表現于一線醫護人員的付出與犧牲。《武漢戰疫》第二集《救治》中,省救治專家組組長趙建平坦言初期戰斗并不順利,感染入院人數激增以及太多未知因素導致醫務人員過度勞累乃至犧牲;《同心戰“疫”》第二集《生死阻擊》里,武漢市肺科醫院醫生胡明因得知同行不幸感染而痛哭流淚。在湖北共有3000余名本地醫務工作者感染新冠肺炎,多位以身殉職,這些平凡英雄的離去昭示的正是無言的悲壯美。此種悲愴非他人搬弄是非所致,也不是命運式的遭遇,而是“由于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明知其害,依然不畏懼退縮,這也讓人們意識到同危險的病毒戰斗反而是一種必然的崇高。因為悲壯美的意味不僅在于它帶來的痛苦,更在于我們對待痛苦和災難的反抗方式。如此,紀錄片悲壯的美學特征才能激勵現實中的人們不怯懦屈從,直至獲得斗爭的勝利。同時面對犧牲、目睹失敗,亦會讓人們認識到必須更好地認識病毒、掌握規律,才能進行更有效的防護和治療,其也暗含了人類奮斗的最高可能性。
其次,悲壯美還表現于無數投身抗疫斗爭中的普通群眾。日常平凡和最不引人注目的普通群眾,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不幸更具悲壯意味。魯迅說,“有價值”的小人物遭遇,強調的是悲劇的正義[ 4 ] 3 8,它更能彰顯人生的價值意義和悲壯精神,也會直接鼓舞現實中人們的奮斗與抗爭精神。例如在《武漢戰疫》第一集《迎戰》中,武南社區居民趙泉的父親不幸感染,病情危急,卻因疫情爆發初期醫療資源嚴重緊缺而無法入院治療,最終離世。再如《2020春天紀事》第三集中,負責調配物資運輸車隊的志愿者李小熊不幸感染新冠病毒,社區工作人員黃恒因身體不適居家隔離;《在武漢》第一集《車輪上的生命》中車隊隊員簽署生死協議,志愿者丹丹感染病毒。可見悲壯的美學特征揭示的是生命的偉大以及人性之美,在與病毒的斗爭實踐里,人的認知總是有局限的,失敗、犧牲難以避免,但不可戰勝的是人的理想情懷、精神意志和善美人性。普通民眾的無私奉獻說明悲壯性給予恐懼和哀傷之后,還有憐憫、珍惜與震撼,它讓人們領悟抗疫精神的豐盈和堅實,從而產生真實的審美快感。
“戰疫”題材紀錄片的悲壯美學特征喚起的不僅僅是同情式的憐憫,還能激起觀眾的贊美心情和英雄氣魄,這與崇高的美感十分相近。雖然人物的不幸遭遇叫人痛心惋惜,但又為他們的力量和堅毅而折服,悲壯美同時含有否定性的和肯定性的兩種情感形式。抗疫斗爭中個體的犧牲與恐懼從外在方面看是失敗了,但在另一種意義上卻能激發我們強烈的情感和生命能量。因而悲壯是全國人民阻擊新冠病毒過程中對自身和他者的觀照、感悟和認知。與之相連的雖是苦難與犧牲,但其中蘊含的美感意味卻洋溢著偉大的抗疫精神,激勵著后人繼續戰斗,直至獲取勝利。
三、和諧美:矛盾沖突的調適與統一
美的本質屬性是和諧,無論崇高美還是悲壯美。從另一方面說,崇高、悲壯蘊含的驚人力量也直接來源于主體與對象間的和諧狀態。如許多美學家認為的那樣,只有矛盾、沖突的危險性得到緩解時才會產生更多美感,并發揮最強烈的作用。在“戰疫”題材紀錄片中,和諧美主要存在于沖突的調適與統一中,包括人與病毒的沖突、人與他者的沖突和人們自我內心的沖突。
和諧的關系與美感產生于對立因素的互補、調適和統一。在與新冠病毒的抗爭中,歷經磨難最終獲得重大戰略成果自然就蘊含和諧的美學特征,它源自人們不屈從怯懦、敢于戰斗的崇高精神。但沖突對立面導致的犧牲、失敗和悲壯也構成另一極的和諧關系,例如《武漢戰疫》中的趙泉一家,父親感染不幸去世,隨后感染病重的母親則得到了及時救治并康復出院。這里雖然充滿悲劇意味,卻也是一種和諧,展現了在與病毒斗爭中人類逐漸占得上風,各地醫療隊逆行支援、擴建醫院收治重癥病人、開設方艙醫院醫治輕癥患者、分診治療等決策及時解決了“一床難求”的矛盾。如趙泉自己說的,“要是父親晚一個月感染病毒,也不至于現在這個狀況”。此為一種“主觀的內在和解”[ 5 ] 1 5 5,少數個體為了整體利益而犧牲,矛盾沖突的雙方最終都實現了一種揚棄,重新達到和諧。
其次是人與他者沖突形成的和諧美。關閉離漢離鄂通道之后,無數普通群眾居家隔離,日常生活用品均由社區工作人員統一采購派發,其中的利害糾葛必然會引發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紀錄片《在武漢》第四集《最后一公里》主要講述西城壕社區委員會的日常工作。社區封閉中的居民作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會產生多樣的需求,而社區委員會只有18名工作人員。副主任凃卉因不能及時滿足居民購買藥品的需求而發生爭吵;年長的居民會由于無法使用手機支付而心生不滿;還有的厭倦菜品種類單一。但最終這些矛盾都得以妥善解決,下沉干部王敬業單獨外出為居民購買藥品;社區開設現場登記以滿足年長者的需求;菜品種類也逐漸豐富。作為阻止新冠疫情擴散的最前線,居民與工作人員皆依道而行,彼此交感,在抗擊疫情的斗爭中發揮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從整體上看即為一種和諧的狀態,彰顯的是家國同構的和諧精神與美感。
再者則是人們自我內心沖突生成的和諧美。如《武漢:我的戰“疫”日記》第四集中,軍隊支援湖北醫療隊的90后隊員李晨述說自己向母親隱瞞投身一線的消息;第十一集里女性醫護人員在糾結的心理斗爭后,為了工作便利而剪掉頭發。《在武漢》中放射科醫生黃維告別妻兒父母,獨自駕車從成都出發支援武漢;吳悠遭受群眾質疑爭吵,本要放棄志愿工作的他深思之后依然堅持義務救助他人。《2020春天紀事》里的志愿者施洋不顧家人反對,直言“不管發生任何事情,你不站出來誰站出來”。紀錄片中的這些普通人物都妥善調適了自我內心的沖突,以內在精神來充實肉體價值,投身抗疫斗爭中,讓本已失衡的社會生活、身心關系重獲和諧。此種沖突生成的和諧,無論看見與否都會比外在形式的和諧更高、更美,因為它源自人心情感、理智、欲望、道德、正義之間的權衡與抗爭,沖突和解之后誕生的即是真實的崇高美和悲壯美。
在某種程度上,和諧是崇高美與悲壯美的共同基點。崇高、悲壯多基于數量較“大”的和諧來生成震撼人心、鼓舞志氣的美感,而和諧美本身則是從一個人、一件事的矛盾沖突中得來。因此在眾多“戰疫”題材紀錄片中,對抗疫精神的呈現和贊美都落腳于個體人物和事件上,將崇高、悲壯、和諧的情感意味投射至廣大人民群眾身上,進而共同構建、弘揚黨和人民的抗疫精神與大無畏氣概。
結 語
以上主要從“合目的性”的視角,即紀錄片應具有“普遍、深刻、重要的社會意義”[6]的角度,對“戰疫”題材紀錄片所共有的美學特征予以簡要闡述。若從“合規律性”上看,如紀錄片創作方式、文本結構、敘事手法、畫面聲音,則會發現“戰疫”題材紀錄片又蘊含著鮮明的人民美學特征。它們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如深圳衛視制播系列vlog《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記》;由央視新聞、嗶哩嗶哩聯合制作的紀錄片《在武漢》則從普通志愿者的視角進行拍攝;央視紀錄頻道的《武漢:我的戰“疫”日記》亦是從武漢疫情親歷者的視角出發,向觀眾講述武漢抗擊疫情的真實境況。這些靈活的呈現形態和創作方式既滿足了全媒體時代受眾的接受習慣與審美需求,也讓紀錄片文本內容的構建始終以人民為主體,凸顯出鮮明的人民美學特征,進而承載崇高、悲壯與和諧的美學風格。由此,目的與規律的有機統一讓“戰疫”題材紀錄片的美學特征厚重宏大且真實細微,悲壯源自人民、崇高由人民構建,正是無畏無私的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共同奮戰,才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斗爭重大戰略成果,鑄就偉大的抗疫精神。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EB/OL].人民網.https://baijiahao.baidu.com/ s?id=1677311283946579874&wfr=spider&-for=pc.
[2]陳偉.崇高論——對一種美學范疇和美學形態的歷史考察[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3]走進崇高研究院.中外崇高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郭玉生.悲劇美學:歷史考察與當代闡釋[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5]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6]鄭征予.紀錄片美學筆記[J].中國電視,1999(3).
作者簡介: 姜常鵬,浙江師范大學文化創意與傳播學院講師、博士;陳敏南,浙江師范大學文化創意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萬書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