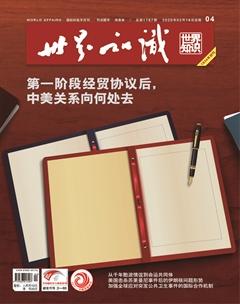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有三個特點
卞永祖
2020年1月16日,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華盛頓簽署。這一協議的達成代表著兩國愿意對等、理性地解決彼此重大分歧,體現了兩個世界大國的責任與擔當。就像習近平主席在帶給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口信中所指出的,中美雙方完全可以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通過對話磋商找到有關問題的妥善處理和有效解決辦法。
協議文本十分翔實,具體看有三個主要特點。
首先,這是一份對等的協議。與談判前期美方曾單方面提出的種種過分和苛刻要求相比,第一階段協議把雙方放在對等的位置,義務和權利是對等的。比如,在第一章知識產權部分,強調“雙方應確保公平、充分、有效的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對于依賴知識產權保護的一方,對方應確保為其提供公平、平等的市場準入”。權責對等、互信合作的支持產權和技術轉讓不僅讓國外企業更加放心地讓更多知識產權進入中國,也有利于我國發展創新型企業、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兩國還將“對等”落實到溝通和執行程序上,明確了常態化的爭端解決方式,從而規避了歷史上大國爭端最后升級為政治摩擦、軍事斗爭甚至滑入長期冷戰的風險。協議明確了貿易爭端處理的具體流程,并設立“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辦公室”。辦公室將評估雙方協議履行中出現的具體問題,接受中美任何一方提交的申訴,這就為實事求是地解決爭端提供了基礎。協議同時強調各自的“雙邊評估和爭端解決辦公室”可向具有相關專業能力的政府部門咨詢,對“信息請求”的相關要求細節也做出了規定,足以體現雙方對于建立更高效溝通和減少誤會的誠意。協議體現出的“對等”反映了中美兩個大國在競爭中尋求有效合作、建立適應于未來雙贏機制的努力,人們對于中美貿易爭端是否會轉化為軍事、政治沖突的擔心大大降低了,常態化的經濟競爭與合作將會成為總體趨勢。
第二,這是一份多贏的協議。在擴大貿易的部分,雙方本著互惠互利以及市場化原則,擴大雙向貿易,推動雙向投資。中美兩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相加占全球約40%,是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推進器。在當前世界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背景下,協議的簽署不僅有助于推動中美兩國經濟增長,也有利于穩定世界各國的貿易和投資,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和更進一步的經濟全球化。協議規定美國對中國3000億美元商品加征的關稅稅率將由15%降至7.5%,3000億美元的第二部分關稅減免,不再加征,這顯然有助于中國企業維持和擴大出口。
中國正處于全面轉型升級的時期,人民生活質量快速提高,但“人口眾多、耕地稀缺”的現實也決定了必須加強農業國際合作,合理增加農產品進口。根據海關總署的公開數據:2017年中國大豆進口量是9553萬噸,其中從美國進口3258萬噸;2018年進口大豆8803.1萬噸,其中從美國進口1664萬噸,同比分別減少7.9%、49.4%,這是自2012年以來的首次減少,主要原因就是受到中美貿易戰的影響。未來兩年,以保證主糧“自給自足”的安全底線為前提,加大對大豆、玉米、肉類等農產品的進口,不僅可以更好地滿足老百姓食品消費結構升級的需求,也為農業提質增效提供更多時間空間。2019年由于非洲豬瘟的影響,中國豬肉價格高企并引發物價上漲,當年12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達到4.5%,自美國加大肉類進口也會有助于緩解國內物價上漲壓力。在其國內經濟復蘇緩慢、農民日益不滿的情況下,美國也迫切需要找到刺激經濟增長的有效手段,農產品出口至少是維持經濟穩定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對中國農產品市場預期較高。
總體來看,中美兩國第一階段協議的達成是兩國經濟互補性強、滿足雙方利益的結果。盡管過程曲折,但最終達成共同認可的協議,不僅符合兩國期待,也讓世界其他國家懸著的心暫時落了下來。
第三,這是一份理性的協議。在近兩年的中美經貿摩擦過程中,兩國國內都曾出現過情緒激動甚至是非理性的言辭。不過在談判過程中,中方在恪守原則與展現靈活性之間保持了動態平衡。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指出的,中方始終堅守“三條紅線”,同時采取漸進方式來逐步解決問題,增強了文本的平衡性和協議的公平性。協議內容體現出雙方相互尊重對方制度和法律體系、尊重對方訴求的原則,本質上體現的是兩國的理性。

2020年1月9日,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發布會上宣布,應美方邀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將于1月13日~15日率團赴華盛頓簽署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對于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在“涉及侵犯商業秘密責任人的范圍、民事程序舉證、藥品相關知識產權及數據、一般市場準入相關的地理標志問題”這些問題上,“美國確認,美國現行措施給予與本條款規定內容同等的待遇”,這從一個側面表達了美國對中國經濟和科技自主發展成就的理性認可,消除了近幾年國際上尤其是美國國內對中國企業的不實指責和誣陷,為我國產業升級并在全球制造業鏈條中向高附加值轉移創造了條件。客觀來看,中美未來科技合作互補性強,潛力巨大,加強合作是各自和共同發展的必由之路。美國《科學美國人》雜志發表的數據顯示,在全球十大科研資助巨頭中,七個來自中國,三個來自美國,排名第一的是中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比如在人工智能領域,中美兩國均領先世界各國的發展,雖然美國在人才、技術方面具有優勢,但中國在應用、市場、數據方面更有潛力,如果兩國能攜手合作,無疑能極大地推動該領域的發展。
協議也提出要尊重雙方的貨幣政策自主權,對我國未來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提供了保障,對人民幣匯率也有適當安排。在反復磋商與博弈之后,中美兩國都從大局出發,正視分歧、管控分歧,就兩國間的匯率問題達成協議,不僅顯示了美國更加理性,也表明中國更加成熟。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這個協議確實會給國內某些行業帶來壓力,但壓力同時也應轉化成我國加快相關領域改革的動力。比如在金融服務部分,雙方就“平等互利銀行服務”具有重要意義達成了共識,并將在資產管理領域加快合作,允許美方機構可以“直接從中資銀行收購不良貸款”,加快金融領域對外開放步伐。截至2018年底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總規模約124.03萬億元,是2012年27萬億元的4.5倍多,2019年全球銀行業排名中,我國四大行的資產規模占了前四名,銀行業的總資產達到284.67萬億元,折算成美元超過了40萬億美元,但大而不強的特征還比較明顯。隨著這幾年供給側改革的加快,一方面銀行體系內存在越來越多需要處理的不良債務,這迫切需要加快建立現代化的銀行體系,同時,我國資管行業粗放式發展特征明顯,與當前人民群眾財富管理的要求還存在距離,管理能力亟需提高。隨著資管新規的實施,部分資產管理機構將會難以適應新規定,同時在加大對外開放的背景下,可能面臨被淘汰的壓力。類似的,我國評級機構實力相對落后,而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家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共占據了全球市場超過90%的份額。因此,加大開放力度,讓更多國外先進金融服務機構來推動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同時也要形成改革的壓力,提高國內相關機構的經營效率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