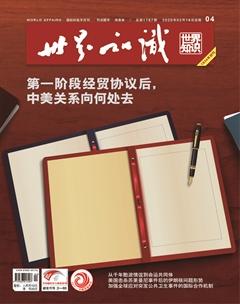美國史上最年輕的總統競選人布蒂吉格
陳佳駿
進入2020年,美國民主黨競選人隊伍的輪廓越來越清晰。在1月14日的第七場民主黨競選辯論會上,參加人數精減到六人,除前副總統拜登、現任聯邦參議員桑德斯、沃倫和克洛布查以及億萬富翁湯姆·斯泰爾五位“老人”外,還有一位年僅37歲的參選人,他就是只做過七年小城市(印第安納州南本德市)市長的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這位被譽為“神童”、具有“不可思議的中西部精神”的年輕市長在去年11月的艾奧瓦州Selzer & Co.民調中一度躍居榜首(現處在第三位)。隨著民主黨首場初選“艾奧瓦州黨團會議”的臨近,他會受到更多關注。
唯一的“外交政策候選人”
民主黨總統競選人之間的角逐已展開一年有余,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參選人對外交政策都不怎么熱情。在他們關注的主要議題中,只有氣候變化、對外經貿摩擦、美國與伊朗關系勉強與外交有關。布蒂吉格算是個例外,去年6月,他在宣布參選后僅一個多月便到印第安納大學發表了闡述對美國對外政策看法的演講,此后接受了多家美國主流媒體和智庫的訪談,詳細闡述了他的國家安全觀,外交政策儼然成為其競選政綱中的“旗艦”。《時代》周刊將布蒂吉格稱作“外交政策候選人”,《華盛頓郵報》專欄文章評稱“外交政策將是布蒂吉格能否出線的關鍵”。
布蒂吉格之所以如此重視外交政策,原因可能在于:第一,外交政策是他為數不多的可具體操作的領域,早早拋出相關綱領對于鞏固其民調靠前的位置有一定必要性。作為名氣不大的政治新人,他需要盡早與在外交政策上毫無章法的特朗普區分開來,以期向選民展現出一個頗為專業的競選人形象。另一方面,考慮到資歷太淺,他沒有太多的議題資源可以用來進行自我表達,唯有通過外交政策顯示其“少年老成”。
第二,關注外交政策與他的個人成長背景也有很大關系。布蒂吉格在演講中說,9.11事件深刻影響了他的世界觀,自己是“9.11一代”。美國“政治”網站的一篇報道稱,9.11事件震撼了布蒂吉格的內心并激起了他的“激進外交思想火苗”,當時還在哈佛大學念書的他希望民主黨能夠更加具有戰斗精神。2005年,布蒂吉格加入被譽為“新一代鷹派民主黨人重新思考‘后9.11世界安全問題”的左翼智庫“杜魯門國家安全計劃”。該智庫官網上寫明,它“致力于塑造和倡導強硬、智慧的國家安全解決方案”。2014年,布蒂吉格在擔任市長期間以海軍情報員的身份短暫參與了阿富汗戰爭,實現了“軍人夢”。事實上,布蒂吉格的家族有著深厚的軍人傳統,他的舅舅曾是陸軍航空兵上尉,殉職于二戰,其外祖父也是一名職業軍人。
第三,外交智囊團的加持。在許多民主黨建制派精英看來,雖然布蒂吉格年紀輕輕,但沉穩、鎮定、理性,反倒更像是競選人群體中的“成年人”。或許是這個原因,數位經驗豐富的“老人”甘愿充當他的外交政策智囊,包括曾擔任過奧巴馬政府助理國防部長的威爾遜、前白宮國家安全理事會發言人及總統特別助理普萊斯、前副貿易代表霍利曼、布魯金斯學會美國與歐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斯洛特等。美國“政治”網站報道,還有100多位外交政策專家以志愿者身份為其提供建議。去年12月,218名外交及國家安全專業人士公開發表了一封聯名信,表達對布蒂吉格的支持,其中不乏重量級人物。
對華政策如何表述?
不同于其他競選人只是在涉疆、涉港議題上發表一些對華消極言論,布蒂吉格有更多的著墨,目前他已經通過多種場合基本向外界呈現了強硬的立場。
在經貿方面,布蒂吉格雖然反對濫用關稅手段,但對中國處理對外經濟關系的行為方式的界定與特朗普并沒有太大區別。布蒂吉格在去年6月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訪時表示:“僅僅用關稅來‘戳他們(中國)眼睛然后看他們的反應,是一個真正的戰略錯誤。但我也認為,感知中國的真實挑戰并沒有錯,特朗普對中國的定位并非完全錯誤。”布蒂吉格有這種想法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他是來自中西部工業城市的民主黨人,具有一定的經濟民族主義傾向。在他看來,任何外交政策必須與其國內意義聯系起來。換言之,外交需要服務于內政,在采取每一個具有地緣政治影響的行動之前,都需要事先評估其對美國普通民眾的影響。因此,布蒂吉格主張“通過有序而非混亂的方式”來改變中國的行為,從而降低美國工人承受的實際成本。布蒂吉格也在2019年7月回復美國媒體Axios的一封郵件中寫道:“關稅手段應有明確的戰略目的,而且應將與盟友的協調行動作為全面戰略的一部分,由此來改變中國的經貿行為。”

皮特·布蒂吉格

美國印地安納州南本德市市郊的界牌。
鼓吹“道路和價值觀之爭”是布蒂吉格對華政策最突出的部分。他去年4月接受《紐約客》雜志采訪時給中國貼上了所謂“技術威權主義”的標簽,并且直白地說:“我確實相信中國正在崛起成為競爭者,而且不僅僅是競爭者,在許多方面甚至是對手……我確信我們的模式正在與他們競爭。”顯然,他把中美兩種價值觀對立起來。在他看來,美國要在競爭中勝出,必須堅持和強化自己的主張。布蒂吉格曾加入“杜魯門國家安全計劃”,事實上他也十分崇拜杜魯門。“杜魯門主義”強調對共產主義的遏制以及推行美國的全球霸權。從布蒂吉格的一系列言論來看,“杜魯門式”的冷戰思維在其世界觀中根深蒂固。
綜觀其他民主黨競選人,他們并不刻意擴大對華“攻擊面”。桑德斯說中國不是經濟和政治威脅,而是氣候變化的全球伙伴。斯泰爾說中國是美國的“友敵”(frienemy)。布隆伯格說“美國需要中國”。就連此前被認為可能對華強硬的沃倫也沒有在對華議題上過早“攤牌”。拜登則為了證明自己是“外交專家”,從說“中國不是競爭對手”的一面轉向了對華“評頭論足”的另一面,但目前為止也僅流于浮表。部分觀點認為,民主黨競選人正試圖避免在選民心中樹立對華“馬可·盧比奧式”(盧比奧是美國共和黨國會參議員,以對華強硬著稱)的形象。唯獨“后起之秀”布蒂吉格早早擺出一副對華鷹派的姿態,這恐怕不是冒進且缺乏經驗的表現,更像是為了擴大支持者陣營贏得共和黨高層青睞而采取的政治策略,這樣的表現會隨著2020年大選的逐漸白熱化而在兩黨其他競選人身上有更多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