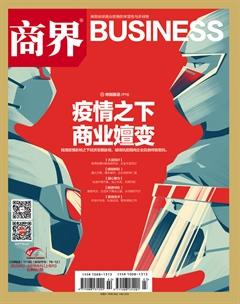疫情防控里的經濟賬

在風險社會,新冠病毒帶來的不僅僅是一場傳染病,而是一場公共社會危機。它似乎在昭示:任何時候,我們熟悉和珍愛的生活方式,都可能會為一些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而終結。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全國人民在勠力同心、堅定戰疫之余,也逐漸清楚地認識到:新冠病毒不僅會讓人的肌體發生呼吸衰竭,更會讓社會短期經濟發展陷入衰退。
對經濟體來說,疫情是一種外部沖擊,擾動經濟走勢,打亂社會秩序,使經濟系統和重要經濟變量偏離既定軌道。
在疫情爆發早期,短期的經濟發展成為一種控制疫情、保障人民健康的代價被支付,封城、延長假期,千方百計防止局部危機演化成為整體危機;而戰役進入相持乃至全面反攻階段時,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就成為了化解風險的共同著力點。
迅疾而至的外部沖擊
今年新型冠狀病毒的病情之危急、發展之迅猛、牽涉面之廣,對比SARS有過之無不及。疫情的發展尚存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經濟企穩的內生性動能被階段性壓制是毫無疑問的。
從經濟增長的底層動力來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消費、投資、出口這“三駕馬車”來拉動。
新冠肺炎對消費的影響是肉眼可見的。消費者緊閉家門足不出戶,商鋪集體歇業,跨區域交通也被受限制,讓消費的服務與供給能力斷崖式下降。
受此次疫情沖擊最大的是服務業,尤其是交通、旅游、住宿餐飲、線下培訓、零售、會展等行業,這些行業恰恰是中小企業的聚集領域,也是吸納就業的“海綿”。如果不在短期內解決疫情,失業問題很有可能會接踵而至。
以電影市場為例,去年春節檔取得58.59億元票房,2020年春節檔卻幾近顆粒無收;去年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國零售和餐飲業完成10 050億元銷售額,今年很多餐企囤下的食材白白浪費;去年春節假期,全國旅游接待總人數4.15億人次,實現旅游收入5 139億元,今年初的旅游市場一片黯淡;全國鐵路發送旅客數量降幅超8成,大量航班因疫情熄火……有專家預測,春節后的短短7天,電影、餐飲和旅游3個行業的經濟損失就達到了10 000億元。
也有很多人寄希望于疫情結束后的報復性消費反彈。然而,這是并沒有太多根據的樂觀,消費的止跌回升并不能覆蓋掉前期的損失。
各地的嚴防死守,讓經濟處于半癱瘓狀態。很多國內的投資項目也被按下“暫停鍵”。春節本就是返鄉高峰,延長假期、復工復產被推遲,企業的生產、投資都會受影響,制造業、房地產、基建投資短期基本停滯。還有部分盡調無法進行,企業投融資計劃擱淺,港股IPO節奏被打亂,據說京東、百度等公司的港股回流計劃也因故押后。
世界衛生組織將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項世衛組織對流行病發出的最高預警,勢必打亂跨國貿易的節奏。這方面,我們有著深刻的記憶: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后,2003年春季廣交會成交額僅為44.2億美元,只有16 400多位客商到會,遠不如2002年春季廣交會到會客商逾12萬人、成交額168億美元。
總體來看,一段時期的消費低迷、投資乏力、貿易降低以及失業率提高是客觀存在的挑戰,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將承擔較大壓力,恐會影響全年表現。
敏感但不脆弱
新冠肺炎疫情是時代的新考題。同樣是冠狀病毒,同樣在春節前后發動突襲,它不僅給我國社會和經濟形成了巨大的壓力,也喚起了整個民族關于2003年“非典”疫情時期的集體記憶。
但今天的局面同“非典”發生的時代不能完全類比。
17年后,中國擁有了擊退疫情更足的底氣:比之2003年1.4萬億美元的GDP總量和1 000美元的人均GDP水平;2019年的GDP總量達14萬億美元,人均邁上10 000美元新臺階,整整翻了10倍,公共衛生體系和體制建設也更加完善。
但焦慮也由對比產生。2003年正處于中國經濟狂飆突進的黃金時期,投資熱潮下,經濟波動的自我修復能力配合政府的“救市”,并未使經濟陷入困境。
當下的中國,面臨內部結構調整和矛盾釋放、外部世界經濟和貿易下行、國際貿易環境不確定性提升以及中美經貿摩擦等不利環境,增速放緩、債務壓力沉重、中小企業生存狀態不佳,逆周期調節尚在進行時。
從時間窗口來講,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之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攻克脫貧攻堅最后堡壘,補齊全面小康“三農”領域突出短板,已經到了沖刺階段。
這是全面復興的最關鍵時期,這是一場輸不起也絕不能輸的斗爭。
經濟失序不僅不能成為新冠疫情的次生災害,反而要成為打贏疫情阻擊戰的支撐與托底。
正是如此,政府和企業不再在“延期”與“復工”間搖擺。分城施策,有序推進復工復產,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正如發改委的表態:沒有經濟保障的防控措施是不可持續的,也難以達到戰勝疫情的目標,最終受損害的是人民群眾的利益。
越是望向歷史,我們就會越堅定:近幾十年國際上大的疫情持續時間一般不超過一兩個季度。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比任何時期要強,我們抵御重大災害的能力也比任何時期更強。
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經濟表現可能敏感但不會脆弱,新冠肺炎不會改變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這場暫時性的外部沖擊,不會改變發展的根本驅動力,無法撼動經濟基本盤。
走出陰霾 重塑肌體
拋開國家層面的宏大敘事,企業的命運隨著疫情高低沉浮,憂慮正爬滿無數中小企業家的心間眉宇。他們的掙扎渴望被關注,他們的困難值得去紓解。
誠然,疫情是企業思考轉型的時點,擺脫路徑依賴的良機。但眼前的問題是,疫情終將結束,可企業能不能等到它結束?嚴峻的形勢下,部分企業的倒閉和小范圍的群體失業,已經出現了征兆。
面對大考,中國可以使用哪些財政和金融政策工具來抗疫情、促增長?
疫情爆發后,政府快速反應,財政金融協同精準發力,在2月初密集推出多維度的政策工具應對經濟下行壓力。
疫情防控是第一要務。截至2月13日,各級財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資金805.5億元,實際支出410億元,力度大、行動快,試圖發揮集中動員的體制優勢,打一場速戰速決的阻擊戰。
為了穩住經濟,一整套開閘放水、減負降費的“禮包”接續而來。人民銀行送上“及時雨”,在宣布超預期開展市場公開操作,2月3日和4日兩天累計投放基礎貨幣1.7萬億元,保持疫情防控特殊時期銀行體系流動性的合理充裕;設立3 000億元專項再貸款與財政貼息,規定對受疫情影響暫時遇到困難的企業,不盲目抽貸、斷貸、壓貸。
同時,政府出臺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的政策措施,助力企業穿越“火線”:例如減稅降費、調低社保繳費基數、提供低成本融資等等,上海更為中小企業出臺細則,由房屋所屬國有企業免除2020年2-3月的租金。
從中央到地方一套組合拳下來,不僅強力保障抗疫前線的救治和物資供應,也將企業的實際融資成本降至1.6%以下。
如此支出,財政赤字率必會上揚,但套用前財政部長金人慶在防治非典時的那句名言:“財政減收終可數,經濟發展難限量。”

為企業減負就是為發展蓄能。
2019年,企業債務違約金額達到1 165億元的歷史新高,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是3.22%,標志著我國企業將進入一個整理資產負債表的緊張時期,將有一批民營企業被迫收縮版圖甚至破產重組。
對日子早就不好過的民企來說,疫情的到來無疑是雪上加霜,甚至會成為壓垮個別企業的稻草。
小微企業不良貸款率的上升,會不會演化為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銀保監會副主席周亮表示,“小微企業的不良占比較小,另外銀行業撥備覆蓋率達到180%以上,有充足的資源應對不良率上升。”疫情是暫時的,從中國經濟的韌性和回旋余地來看,不會對金融造成大的影響。
政府在不斷“提氣”,企業家也在“爭氣”,大家都憋著勁熬過2月份的蕭條。病毒逼著社會治理體系的成熟、企業的成長和優勝劣汰。積極展開自救、正視困難又滿懷希望,是企業家該有的思想姿態。闖關奪隘,化蛹成蝶,經濟的韌性恰恰來自于每一個不服輸、有闖勁的經營單元,處理公共風險需要政府與市場、企業、個人等形成合力。
新冠肺炎的爆發是中國穩健發展之路上的插曲,無需妖魔化災難,疫情帶來的磨難值得銘記與反思。
熨平經濟波動之后,大國將錨定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適時調整財政和金融政策,規避短期經濟刺激政策的“后遺癥”;同時重塑信心,培育新的增長動能、孕育新的投資機會,讓復興之力充分涌流,盡情釋放。
大國是從無數磨難中走過來的,我們應該從殘酷的教訓中習得更多。
2003年的“非典”,讓人驚覺完善公共衛生系統和提升應對突發事件能力的重要性。這次疫情是對我國治理體系和能力的又一次大考,重新暴露出很多問題。這些議題涵蓋重大的經濟意義,但又絕不僅限于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它促使著人們去反思目前公共衛生防疫系統存在的漏洞、去探討如何建設政府危機管理機制、去思考如何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及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