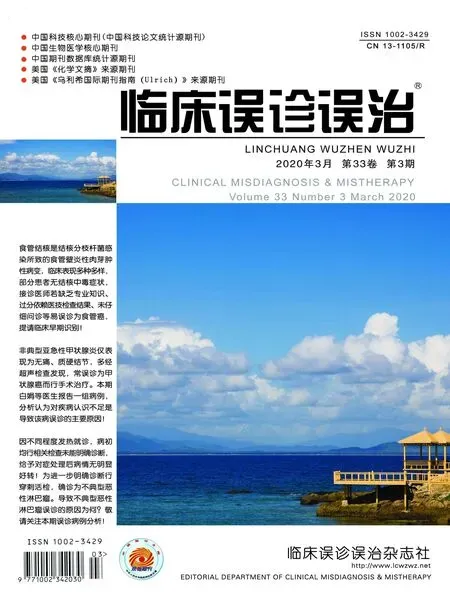小劑量雷公藤總苷聯合甲氨蝶呤對類風濕關節炎患者臨床癥狀、炎性因子及關節功能的影響
陳士軍,朱衛民,田培軍
類風濕關節炎是臨床常見的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發病原因及發病機制尚未明確。有學者認為類風濕關節炎的發病及轉歸與腫瘤壞死因子、致炎性細胞因子等水平增加相關,臨床表現為典型的癥狀及體征,包括關節疼痛、關節腫脹、晨起關節僵硬、畸形,如手指“鵝頸畸形”、膝關節屈曲畸形、髖關節屈曲畸形等,隨著病程的進展至中晚期時,致殘率較高,直接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質量[1-2]。甲氨蝶呤是臨床治療類風濕關節炎常用的免疫抑制劑,長期應用甲氨蝶呤的不良反應發生率較高,但中西醫結合治療可有效提高治療效果[3]。本研究分析小劑量雷公藤總苷聯合甲氨蝶呤對類風濕關節炎患者臨床癥狀、炎性因子及關節功能的影響,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安康市中心醫院2017年10月—2018年2月收治的類風濕關節炎68例,根據治療方法的不同,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每組各34例。觀察組女21例,男13例;年齡19~71(46.12±6.45)歲;病程6個月~8.4年(3.89±1.26)年;合并冠心病3例,糖尿病4例。對照組女22例,男12例;年齡19~70(47.26±6.96)歲;病程7個月~8.3年(3.89±1.26)年;合并冠心病2例,糖尿病3例。兩組年齡、性別、病程等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②無本研究相關藥物過敏史;③符合“2010 ACR/EULAR類風濕關節炎分類標準”制定的類風濕關節炎診斷標準[4]。排除標準:①存在嚴重心、肝、腎等臟器疾病者;②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③入組前30 d內服用免疫抑制劑者;④臨床資料丟失或不完整者。
1.3治療方法 兩組均予常規治療,即口服吲哚美辛(廣東華南藥業集團有限公司生產,國藥準字H44020701)0.1 g、3/d,配合合理飲食,避免食用高脂肪、高膽固醇食物。在此基礎上,對照組予甲氨蝶呤(上海上藥信誼藥廠有限公司生產,國藥準字H31020644,規格:2.5 mg×100片)15 mg口服,每周1次;觀察組予小劑量雷公藤總苷聯合甲氨蝶呤治療,即口服雷公藤總苷(江蘇美通制藥有限公司生產,國藥準字Z32021007)10 mg、3/d,氨甲蝶呤7.5 mg、每周1次。兩組均治療3個月,其中吲哚美辛于治療1個月后劑量減半,治療2個月后停止服用。
1.4觀察指標 比較治療前、治療后臨床癥狀、炎性因子相關指標、關節功能變化,記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
1.4.1臨床癥狀評估:臨床癥狀包括晨僵時間、關節疼痛程度、雙手平均握力、關節壓痛數及關節腫脹數,其中關節疼痛程度采用視覺模擬評分(visual analogue score, VAS)進行評估,總分0~10分,分數越高表示關節疼痛程度越嚴重;利用手捏血壓計球囊測壓法測量雙手握力,并計算平均握力。
1.4.2炎性因子相關指標檢測:采集所有患者治療前、治療后清晨抽取空腹肘靜脈血5 ml,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 IL-6)水平,利用免疫散射比濁法檢測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類風濕因子(rheumatoid factor, RF)水平,檢測方法均嚴格按照說明書進行;利用魏氏法檢測紅細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1.4.3關節功能評估:根據“關節功能障礙分級標準”[5]進行關節功能評估:①Ⅰ級:患者可進行日常生活、工作;②Ⅱ級:患者可進行一般日常生活、某種職業工作,存在活動受限;③Ⅲ級:患者可進行一般日常生活,但無法參與某種工作或項目,活動受限;④Ⅳ級:患者日常生活不能自理、工作能力受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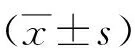
2 結果
2.1臨床癥狀比較 兩組治療前晨僵時間、關節疼痛程度、雙手平均握力、關節壓痛數及關節腫脹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治療后晨僵時間、關節壓痛數、關節腫脹數減少,關節疼痛程度降低,雙手平均握力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5.104、P<0.001,t=9.978、P<0.001,t=9.563、P<0.001,t=12.939、P<0.001,t=12.891、P<0.001);與本組治療前比較,兩組治療后晨僵時間、關節壓痛數、關節腫脹數顯著減少,關節疼痛程度明顯降低,雙手平均握力顯著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觀察組:t=34.570、P<0.001,t=25.840、P<0.001,t=27.125、P<0.001,t=16.611、P<0.001,t=18.591、P<0.001;對照組:t=15.681、P<0.001,t=15.063、P<0.001,t=12.906、P<0.001,t=7.6757、P<0.001,t=13.284、P<0.001)。見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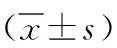
表1 采用不同治療方法的類風濕關節炎兩組臨床癥狀比較
注:觀察組予小劑量雷公藤總苷聯合甲氨蝶呤及常規治療,對照組予甲氨蝶呤及常規治療;與對照組同一時間比較,bP<0.01;與本組治療前比較,dP<0.01
2.2炎性因子相關指標比較 兩組治療前IL-6、ESR、CRP、RF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治療后IL-6、ESR、CRP、RF水平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或P<0.01);與本組治療前比較,兩組治療后IL-6、ESR、CRP、RF水平顯著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觀察組:t=17.039、P<0.001,t=12.861、P<0.001,t=6.441、P<0.001,t=6.247、P<0.001;對照組:t=9.616、P<0.001,t=7.774、P<0.001,t=3.553、P<0.001,t=4.619、P<0.001)。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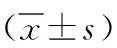
表2 采用不同治療方法的類風濕關節炎兩組炎性因子相關指標比較
注:觀察組予小劑量雷公藤總苷聯合甲氨蝶呤及常規治療,對照組予甲氨蝶呤及常規治療;IL-6指白細胞介素-6,ESR指紅細胞沉降率,CRP指C-反應蛋白,RF指類風濕因子;與本組治療前比較,bP<0.01
2.3關節功能障礙分級比較 兩組治療前關節功能障礙分級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對照組比較,觀察組治療后關節功能障礙分級Ⅰ級比例升高,Ⅱ級、Ⅲ級比例降低,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與本組治療前比較,觀察組治療后關節功能障礙分級Ⅰ級比例上升,Ⅱ級比例下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7.124、P=0.008,χ2=4.300、P=0.038)。見表3。

表3 采用不同治療方法的類風濕關節炎兩組關節功能障礙分級比較[例(%)]
注:觀察組予小劑量雷公藤總苷聯合甲氨蝶呤及常規治療,對照組予甲氨蝶呤及常規治療;與本組治療前比較,aP<0.05,bP<0.01
2.4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 兩組不良反應總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308,P=0.253),且治療過程中均未出現嚴重不良反應,給予對癥處理后癥狀好轉。見表4。

表4 采用不同治療方法的類風濕關節炎兩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例(%)]
注:觀察組予小劑量雷公藤總苷聯合甲氨蝶呤及常規治療,對照組予甲氨蝶呤及常規治療
3 討論
類風濕關節炎是一類外周關節非特異性炎性疾病,其病因尚未完全清楚,約2/3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為女性,主要好發于手、腕、足等小關節處,臨床表現為關節、肌肉疼痛或紅腫,發病緩慢,隨著病情進展,嚴重者可出現關節畸形、骨骼肌萎縮等癥狀,并且病情可反復發作,約21.1%的患者伴有心肌炎、心內膜炎、心包炎等疾病。若類風濕關節炎患者出現心悸、氣促、心前區疼痛等癥狀,可對其日常生活及工作產生重大影響[5-7]。甲氨蝶呤是目前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常用藥物,屬于抗葉酸類抗腫瘤藥,作為一類葉酸還原酶抑制劑,有直接抗炎作用,主要通過抑制四氫葉酸水平,阻止嘌呤核苷酸、嘧啶核苷酸生物合成,影響免疫活性細胞DNA合成,以達到控制類風濕關節炎病情進展的目的[8-13]。有學者報道,單一使用甲氨蝶呤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臨床療效欠佳,無法達到預期效果[14-15]。
本研究收集了68例類風濕關節炎的臨床資料,觀察了單純甲氨蝶呤及小劑量雷公藤總苷聯合甲氨蝶呤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臨床效果,比較臨床癥狀、炎性因子相關指標及關節功能變化,結果顯示,兩組治療后晨僵時間、關節疼痛程度、雙手平均握力、關節壓痛數及關節腫脹數均較治療前明顯改善,且觀察組上述指標改善程度大于對照組,提示小劑量雷公藤總苷聯合甲氨蝶呤改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臨床癥狀的效果明顯優于單純甲氨蝶呤。雷公藤總苷提取于衛矛科植物雷公藤根,具有除濕消腫之功效。現代藥理研究已證實雷公藤總苷有抗炎、抑制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等作用,與甲氨蝶呤聯合使用時,減少了甲氨蝶呤劑量,提高了治療效果[16-17]。本文進一步研究發現,觀察組治療后IL-6、ESR、CRP、RF水平均明顯低于對照組,且關節功能障礙分級Ⅰ級、Ⅱ級比例較本組治療前改善,說明小劑量雷公藤總苷聯合甲氨蝶呤改善了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炎性因子水平及關節功能,與既往研究結果相符[18-20]。CRP、IL-6主要促進機體炎性反應,作用機制為刺激自然殺傷細胞加快分泌γ-干擾素,誘導T淋巴細胞高表達FasL分子以損傷相應器官,其水平降低證實機體炎性狀態好轉。
綜上所述,小劑量雷公藤總苷聯合甲氨蝶呤能更有效改善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臨床癥狀、炎性因子水平及關節功能,且不良反應發生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