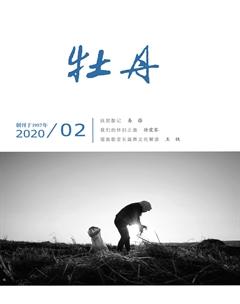黔北苗族的婚姻規則與文化制約
苗族是一支擁有燦爛文明的世界性民族。在上古時期,苗族聚居于長江中下游及黃河流域部分地區,后根據地域、服飾和習俗的不同,逐漸分為了很多支系。本文所研究的便是位于黔北的一支自稱“蒙嚷”的苗族支系群體,從族群與婚姻、地域與婚姻圈、開親規則與意識轉變三個方面,洞悉黔北苗族內部通婚規則和文化制約間的族群認同和潛在關系。
一、族群與婚姻
苗族,是一支擁有燦爛文明和多系分支的世界性民族。據史書記載,在上古時期苗族聚居于長江中下游及黃河流域部分地區,后西遷聚居沅江流域為中心的今湘、黔、川、鄂、桂五省毗鄰地帶,其族屬上古時稱“九黎”“三苗”,春秋戰國時期稱“武陵蠻”“五溪蠻”。唐宋以后,遂從若干少數民族混稱的“蠻”中脫離出來,作為單一的民族稱謂——苗族,后根據地域、服飾和習俗的不同,逐漸分為了很多支系,在貴州的苗族支系有“紅苗”“花苗”“白苗”“錦雞苗”“仡兜苗”等。本文所研究的便是位于黔北的一支自稱“蒙嚷”的苗族支系群體,大概位于貴州北部和中部的湄潭、甕安兩縣之間,今湄潭縣茅坪鎮轄區內,其所操語言屬于漢藏語系苗瑤語族苗語支西部方言中的川黔滇次方言。
婚姻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也導致了家庭組合方式及形式的變化,同時當地通婚圈及結締模式也隨之改變,變化的過程中本民族文化和“他文化”的碰撞也使得婚姻儀式中的某些內容被舍棄、被改變,或是被傳承。研究當地的婚俗文化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蒙嚷”苗族的民俗文化,其中潛在的通婚規則與結締行為也集中展現了本支苗族強烈的族群文化符號和身份認同意識。
“蒙嚷”苗族的婚俗文化形成于特定的苗族社會文化體系中,但同時又依附、歸屬和受制于其社會文化制約,并也不得不隨之發生變化。在當地婚俗儀式中,有一套固定、規范且世代相傳的口頭說唱和蘆笙演奏藝術,涉及面廣泛,其附著于儀式流程和系列民俗活動得以傳承下來。由于外出務工、求學現象的增多,黔北苗族青年的思想也在隨著生活環境和方式的改變而發生變化。據調查,在近5年內,當地的婚姻儀式急劇減少。研究者對“蒙嚷”苗族的原始信仰、民間節慶、儀式流程等進行剖析研究,可以了解黔北苗族傳統社會文化功能及特征,有利于黔北苗族婚俗文化的保護與發展。
二、地域與婚姻圈
“蒙嚷”苗族早期婚姻形態分自由婚姻和包辦婚姻。包辦婚姻主要與黔北當地地域文化及婚姻圈有著直接的聯系。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弗里德曼(M. Freedman)和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兩性之間的交往是社會構成的重要機制,不同群體的結合是共同體形成的基礎,而群體結合的最初紐帶正在于兩性之間的通婚行為和關系。婚姻圈有著象征擇偶觀念和結締結構的關鍵“標準”,婚姻圈的縮小或者擴大也側方面反映出該區域內不同成員擇偶的來源和取向,也能折射出一個家族、族群、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程度的交融情況。
黔北民風習俗、文化信仰等影響和制約著“蒙嚷”苗族的結締行為,并在生命繁衍的過程中漸漸形成了一種聯姻契約,從而使得“蒙嚷”苗民不斷改變自己的結締模式,使之與黔北文化發展的大背景相吻合。從田野調查中得知,黔北苗族的通婚范圍從最開始的村內通婚到與鄰近村通婚,再到后來出現省外通婚現象。通婚圈的擴大化發展,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中國“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黔北地區經濟的發展也隨即有了改良和提升,耕作制度的變化、公路設施的建設,使得人口流動性增強,苗族青年在異地打工或者完成學業后,便會有留居異地的想法,從而結識新的人、事、物,為婚姻圈的擴大提供了基礎和可能性。
第二,村內通婚雖然起初是該區域最為主要和普遍的通婚形式,但隨著越來越多異地聯姻的成功案例,使得當地苗族同胞對原本單一的村內通婚的依賴度減少,為婚姻圈的擴大注入了機會和可能。之后,越來越多的苗民認識到異地婚更有利于傳播族群文化,彰顯族群魅力,實現文化交融的互利共贏,這也是婚姻圈得到擴大的原因。
第三,如今是一個信息和數據化時代,政策的支持、婚姻法的普及、文化的迅速傳播,使得當地村民思想意識轉變,在婚姻選擇上不再固定于狹小的范圍內,婚姻自由是年輕人追求選擇遠距離婚姻的主要因素。
三、開親規則與意識轉變
“蒙嚷”苗族在運行他們的通婚聯盟模式過程中有著他們自己的開親規則。這樣的規則首先必須是建筑在“我們一定不能和那些人結婚”的基礎原則上,而長輩們所考慮的地域遠近、年齡差異、性格匹配等因素都歸為其后。上文提出的聯姻類型、婚姻圈的形成和延展,種種締結模式的存在,都基于一定的開親規則。筆者在調查中,發現當地在早期有異姓不婚、同系不同支不婚、異族不婚的現象,但之后隨著外界文化反作用力的介入,逐漸打破了這種規則。
苗族婚姻習俗受傳統文化的影響,是當地民族特點和民族心理的反應。過去在這個地方苗民可以包容異姓、同族通婚,但與漢族開親仍屬當地最大開親禁忌,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較大。筆者在調查中發現以20世紀80年代為一個分界線,在此之前,幾乎無一例苗漢通婚現象,到了80年代后才開始略見一兩例,再逐漸遞增,最后儼然成為境內通婚一最大趨勢。
“蒙嚷”苗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保護甚至閉塞自己來維系本族群的聯姻制度,歸根結底也是一種自我保護,保護自己的族群,保護自己的族群文化及其生命。他們深刻地意識到,開親規則的改變、婚姻圈的擴張,每前進一步,就意味著自己的族群離“消亡”就更近了一步。然而,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維系得再完美的東西,當它無法與這個社會、這個時代、與自然規律相適應時,也就意味著另一種消亡。改革開放、《婚姻法》的深入貫徹實施,國家政府對少數民族建設投以高度關注和幫扶,為苗民興教育、修公路、蓋高房,使得當地苗民的族群自信和地位漸漸得到了提升,不同民族團體開始相互接納對方,并認識到各民族是可以同發展、共進步、和睦相處的。
(貴州師范學院音樂舞蹈學院)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9年度國家民委民族研究青年項目“黔北地區少數民族婚俗文化研究”(項目編號:2019-GMC-05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舒然(1989-),女,仡佬族,貴州貴陽人,碩士,講師,研究方向:民族音樂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