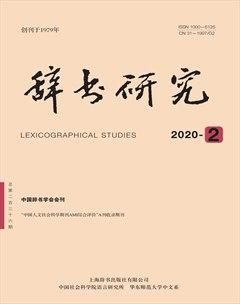嘉絨語東部方言的輔音對應和歷史演變



摘?要?《嘉絨譯語》記錄了清乾隆年間的四川嘉絨語東部方言,目前學界關注甚少。文章將譯語記錄的嘉絨語和現代田野調查的嘉絨語資料比較,發現其輔音對應關系,歸納語音演變規律,包括: -m韻尾與-n或者-合流;t-腭化為t-;邊擦音-變為擦音或者邊音;mb-和b-中的阻塞成分弱化、消失。
關鍵詞?川番譯語?嘉絨譯語?嘉絨語?輔音?歷史音變
一、 引言
《嘉絨譯語》是清代“川番譯語”之一種,于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1748—1750)由四川地方政府采集和編寫,用漢字和藏文記錄了當時川西地區的嘉絨語東部方言,(孫宏開1989)可視為一部“漢語嘉絨語”雙語辭典,通過藏漢注音可以窺探近300年前嘉絨語的語音面貌。[1]《嘉絨譯語》收詞與四川采集的其他“川番譯語”相同,共收740個詞語,分為20個門類。每個詞語上面書寫藏文,下面書寫漢字注音。藏文多非正字,其主要功能應該也是為嘉絨語注音。目前可見的比較權威的《嘉絨譯語》版本即故宮藏清抄本(見圖1),該抄本已于2018年由故宮出版社影印出版。另有一份藏于日本,西田龍雄(1973)研究《多續譯語》時提及了今西春秋所藏的《嘉絨譯語》,應為初編本,但目前未見刊布。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故宮藏本,同時參考聶鴻音、孫伯君(2010)的校錄本。
圖1?故宮藏《嘉絨譯語》清抄本(正文前兩頁)
與其他“川番譯語”相比,學界對《嘉絨譯語》的關注和研究相對不足。本文將《嘉絨譯語》用藏文和漢字記錄的嘉絨語讀音,與現代嘉絨語東部方言代表點的讀音進行比較,總結出輔音的對應關系,進而分析不同讀音的歷史層次和歷史演變規律。用來比較的現代嘉絨語材料涉及馬爾康、小金、理縣、汶川等地,涵蓋了東部方言的大部分土語。其中,馬爾康土語以卓克基話為代表,材料主要引自黃良榮、孫宏開(2002),理縣薛城話材料引自嚴木初(2014),其余理縣(古爾溝和甘堡)、汶川(綿虒)、小金(沃日和四姑娘山)等地材料均為筆者田野調查所得。
《嘉絨譯語》中用來注音的漢字和藏文存在個別不對應的情況,即漢字與藏文無對音關系,藏、漢文字所記錄的或許是不同的詞,應與當時譯語編寫方法與程序有關——藏漢注音可能是不同的人分別采寫然后匯于一冊。這種情況下,我們根據所掌握的嘉絨語材料,如果與藏文明顯對應則以藏文注音為準,如果與漢字明顯對應則以漢字注音為準。
二、 輔音韻尾-m的對應與演變
嘉絨語鼻音韻尾有-m/n/三個,這三個韻尾在譯語中均有直接的表現。其中-n與-韻尾變化不大,但-m尾不太穩定,在現代嘉絨語部分方言中已經消失,變為-n或者-。相關詞條列舉如表1所示(由于版面所限,現代嘉絨語方言材料只列出與-m相關的音節)。
表1顯示,馬爾康、小金等地依然保留-m尾,理縣甘堡、薛城以及汶川嘉絨語-m尾已經或者正在消失。譯語利用藏文的后加字-m準確記錄了清代嘉絨語中的-m尾,但注音漢字多為-尾字,這與注音漢字的讀音有關。“川番譯語”是乾隆皇帝下旨由四川負責采集和編寫的,其中的譯音漢字反映當時的四川方音。(西田龍雄,孫宏開1990;鈴木博之2009;Chirkova2014;施向東2016;王振2019)明末四川方言-m韻尾業已消失(黃尚軍1995),清代譯語編寫之時便選擇用-尾來記錄-m。
對表1的例子進行簡化,可以看到各地韻尾主要的對應情況,如表2所示。
單就*am和*om的韻尾而言,小金和馬爾康保留鼻音尾,甘堡*m>n,汶川和理縣*m>,但是各點*-em音節中的-m保持不變[4],可能韻尾的演變與主元音有關。馬爾康和小金保留-m尾,理縣薛城少數詞語保留-m尾,多數變為-,說明理縣薛城一帶存在-m>-的音變。而譯語的*-m與理縣甘堡的-n和-m對應,說明音變的規則是-m>-n,與薛城不同。汶川材料相對較少,但從已有材料來看,音變規律是*-m>-。可見,嘉絨語中*-m韻尾不穩定,但在不同方言點其演變的趨勢有所不同,可能與-n或者-合流。不同方言之間-m韻尾的演變情況不同。藏語也是如此: 藏語衛藏方言各土語中-m尾較為穩定(瞿靄堂,勁松2016);安多方言牧區話保留-m;但是少數北部農區話中-m>-n;而康方言中-m主要演變的特點是與-合流。(王雙成2012)
三、 舌尖塞音的腭化
譯語中的一些舌尖塞音T-[5]在絕大多數現代嘉絨語中也是T-,馬爾康、小金、汶川以及理縣甘堡、古爾溝均是如此,但在理縣薛城讀塞擦音T-。相關詞條列舉如表3所示。
這些詞條在各方言中聲母以T-為主,韻母多數都是偏前、偏高的元音-i,推測T-是早期形式,理縣薛城的T-是T-受前高元音的影響腭化形成的,即T> T/V[+front +high]。
但就譯語的記錄而言,部分元音并非前高的-i,有如下兩種情況: 第一種是“云-sdum-色登”,此處元音為u,而譯語第34和第35詞“云厚、云薄”中的語素“云”譯語記錄為sdem,另結合漢字注音,可以推測譯語所記錄的嘉絨語元音為e,同類的例子還有“墻-sa sde-色帶、伯-da te-葛皆”等。第二種是“狐-ku thu wa-各腿”,與輔音直接相拼的元音為u。
針對第一種情況,結合現代方言材料,我們推測,譯語中記錄的這種非-i的情況是更早的面貌,后來發生元音高化而變為-i,并進一步引發輔音腭化。這應是語言中較為自然和常見的音變,在其他藏緬語中也是存在的。例如羌語支中的“那”,史興語thi55、爾蘇語th55、道孚語th、羌語th:,納木義語中讀音thi55,(馬學良1991)體現出了th>thi>thi的元音高化和輔音腭化的音變過程。資料顯示,薛城“墻”音zi,或是輔音腭化后發音部位進一步后移所致,即: zde>zdi>zdi>zi。
第二種情況例詞較少,但是可以確定的是th與u拼而h與y拼合,這一腭化應該是y而非u引起的,因此這一音變涉及兩個環節: ① u>y;② th>/y。這兩條音變具有饋給(feeding)關系,后者以前者為條件。
四、 邊擦音-的相關對應與音變
譯語中涉及邊擦音-的詞條共有8個,排除重復出現的語素,實際語素數量是3個。[8]相關詞語及其對應的現代嘉絨語音列舉如表4所示。
譯語藏文聲母為lh-,注音較為確切,以lh-記-,漢字無邊擦音故以讀l-的漢字注音。又因為四川方音中泥來母有混,故漢字注音中用泥母的“那”對藏文的lha。現代嘉絨語音形式多樣,反映出*-在現代嘉絨語中的不同演變情況,包括-、hl-、xl-、-和l-等。邊擦音-本身既有邊音特征、也有擦音特征,即[+lateral,+continuant],其演化主要表現為這兩類特征的變化。可以分為三種情況:
a. 失去擦音特征變成邊音l-,即[+lateral,+continuant]>[-continuant]。
b. 失去邊音特征變為擦音-[11],即[+lateral,+continuant]>[-lateral]。
c. 邊、擦特征分離變成復輔音hl-,一個音段變為兩個音段,即:
[+lateral,+continuant]> [-lateral,+continuant] [+lateral, -continuant]
小金沃日的hla快讀的時候是-,因此可以認為是-的一個變體;理縣甘堡的“佛”也有兩個變體,分別是xli和la。由此可以推測,-的演變可能會經歷邊擦分離(c的情況)和擦音丟失(a的情況)兩個連續的過程。而邊音丟失(b的情況)則暫不確定中間是否經歷的邊擦分離的過程。不過,從音素響度角度看,邊擦分離之后形成的hl-,前一個輔音是擦音,屬于阻塞音類[+obstruent, -sonorant],后一個輔音是邊音,屬于響音類[+sonorant]。邊音的響度高于擦音,響度較弱的音應該比響度較強的音更容易弱化和丟失,即hl-更傾向于丟失擦音而保留邊音,所以小金四姑娘山嘉絨語中的-可能是直接從*-變來的,而非hl-中邊音丟失的結果。因此,邊擦音的演變有兩種路徑,如圖2所示[12]:
五、 mb-和b-的弱化音變
這類詞在譯語中出現不多,但是將各方言點的資料對比之后可以明顯發現其弱化過程。相關資料列舉如表5所示。
表5各類資料中的聲母均有一定差異,反映了音變方向或音變階段的不同。譯語藏漢文字對嘉絨語的注音采用了音節重新分析的方式,例如以漢字“斗惹”注音t wre,以藏文khavu re注音kha wre。表5中的注音顯示,譯語讀音與理縣、汶川更為接近,而與馬爾康明顯不同。馬爾康音中的b-在譯語藏漢注音中基本上沒有表現出來。我們認為馬爾康的b-或者mb-可能代表了早期的語音層次,其余各點的讀音是后期演變的結果。為使比較更加簡明清晰,可以將表5簡化如表6所示。
雖然相關例詞不多,但從表6亦可見此類音變的復雜性和規律性,主要表現為三類(1)*mb->w-;(2)*mbro一般分化為兩個音節——mo ro(或bo ro);(3)*br-> wr-。雖演變方向和具體音值在各地有所不同,但都呈現出弱化趨勢,都存在塞音b-弱化為w-以及復輔音mb-弱化為單輔音的情況。從表5資料來看,這類弱化的音變傾向于出現在非詞首音節。
從明代乙種本《西番譯語》中的藏文ba和bo的對音情況看,當時處在非詞首位置的b-也已經弱化。例如: 3月-zla ba-剌瓦,9雪-kha ba-渴瓦,13雹-ser ba-謝耳瓦,16煙-du ba-毒瓦,62園-ra ba-剌瓦,176柔善-zhi ba-失瓦;58河-chu bo-初俄,158叔-khu bo-庫俄,166弟-nu bo-奴俄,167侄-tsha bo-擦俄,195頂-spyi bo-思畢俄,281鼓-rnga bo-兒阿俄。其以“瓦”對ba、以“俄”對bo,說明b-已經弱化。
另外,清代其他記錄藏語的“川番譯語”中也存在類似情況。舉例如表7所示。[13]
故宮藏另外一種收錄2000多詞條的清代《西番譯語》抄本也有類似的現象,該譯語中非詞首音節ba、bo通音化為wa、wo,如: zla-ba(月)譯音“達斡”、kha-ba(雪)譯音“喀斡”、chu-bo(河)譯音“儲倭”、zo-bo(匠人)譯音“莎倭”。(施向東2019)
可見b-的弱化音變是較為普遍且歷史悠久的,嘉絨語和藏語都存在此類演變,且均傾向于出現在非詞首音節,體現出音變的共性規律。
附?注
[1]嘉絨地區語言的地位和系屬學界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是藏語方言,有學者認為是藏語支的獨立語言,有學者認為是羌語支的獨立語言。(多爾吉2015)我們尊重學界前輩的不同觀點,但本文重點不在討論嘉絨地區語言的地位問題,暫時以“嘉絨語”稱之。
[2]編號指詞條在譯語740詞中的出現次序。表中空格表示相應資料闕如。
[3]此處以小金縣四姑娘山為代表點。表中小字地名為具體的資料來源地,是鄉鎮級別的行政單位名稱,以此作為所在縣嘉絨語的代表點,下同。本文列表比較時,某縣可能只選一點作為代表,這有兩種情況: 一是資料限制,例如汶川縣只有綿虒一鎮的材料,故所有汶川縣的嘉絨語資料均以此為代表;二是如果某縣諸點語音差別不大,則本文做比較研究時只選擇一個資料相對豐富的點作為代表。如果某縣各點語音有明顯差異,則分別列舉、逐個比較。
[4]汶川缺少對音材料,暫不考慮。
[5]本文首字母大寫的音標用來記錄一組同部位的塞音或者塞擦音。
[6]“伯”原藏文作(da re),“麥”原文藏文作(drevi),根據兩詞的漢字注音以及現代嘉絨語讀音,并參考《嘉絨譯語》中“皆”的對音傾向(多與藏文te對音)等,推測此處的re或為te之誤寫、drevi或為tevi之誤寫。因為藏文無頭字中的(r)、(dr)、(t)字形接近,故宮藏譯語為抄本,輾轉傳抄的過程中可能出現錯誤,也可能是此抄本所依據的版本本身就有誤。
[7]理縣甘堡和小金沃日的“一”為t rki和ta rk,與譯語和馬爾康不同源,故未在表中列出。
[8]這三個詞均為藏語借詞或者藏嘉絨同源詞。即使是借詞,仍能反映嘉絨語的音變情況。首先,由于這些詞均非新詞,應該是早期借詞,借入時期的讀音應該是比較原始的讀音即*-。其次,同一個藏語借詞可能有不同的藏文寫法,如“佛”即有lha、lho、lhang等不同的寫法,說明《嘉絨譯語》藏文并非規范的藏文正字,而是記音的工具,如果當時的“佛、南、靴”等詞的聲母不是-,已經讀為邊音或者擦音,則譯語應該不會都用lh-去記音,而會直接用藏文l-或者h-注音。因此,譯語中的lh-記錄的音值是-,后來發生的語音演變出現的邊音或者擦音不是借自藏語而是嘉絨語音系內部演變的結果。
[9]理縣甘堡的“佛”有兩種讀法,單說為xli,而佛寺、寺院音為la kha,該詞的構詞理據為“佛+房子”,這里的“佛”音la。
[10]漢字注音“可估”疑似有誤,或為其他詞條注音誤抄此處,這種抄錯位置的現象在《多續譯語》中也出現過。(王振2017)
[11]b和c兩種音變還涉及發音部位的變化,音變之后產生的擦音部位不固定,可能是h/χ/x-,但都是部位較后的[+dorsal, -coronal],而-的部位是[+coronal,+anterior]。
[12]從hl-到l-也許會經歷一個中間的過渡階段,即擦音消失之前的弱化的階段,可以表示為* ->hl->hl->l-。
[13]表7根據聶鴻音、孫伯君(2010)《〈西番譯語〉校錄及匯編》一書中的資料制作。
參考文獻
1. 多爾吉.嘉絨藏區語言研究.中國藏學,2015(4).
2. 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年編華夷譯語.北京: 故宮出版社,2018.
3. 黃良榮,孫宏開.漢嘉戎詞典.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2.
4. 黃尚軍.《蜀語》所反映的明代四川方音的兩個特征.方言,1995(4).
5. 鈴木博之.《西番譯語》〈川七〉18 世紀チベット語打箭爐方言の性格につい て.京都:京都大學言語學研究,2009(28).
6. 馬學良主編.漢藏語概論.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239.
7. 聶鴻音,孫伯君.《西番譯語》校錄及匯編.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8. 瞿靄堂,勁松. 藏語語音的鏈移變化.∥瞿靄堂,勁松.漢藏語言研究新論.北京: 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 19、83-95.
9. 施向東.《西番譯語》藏漢對音中的一些問題.∥南開大學文學院.漢語文化學院合編.南開語言學刊,2016(2).
10. 施向東. 故宮清抄本《西番譯語》藏漢對音譯例研究.民族語文,2019(4).
11. 孫宏開.《西番譯語》考辨.∥白濱等編.中國民族史研究(二),北京: 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 327-342.
12. 王雙成.藏語安多方言語音研究.上海: 中西書局,2012: 304.
13. 王振.《多續譯語》版本考察.新世紀圖書館,2017(9).
14. 王振.《栗蘇譯語》所反映的清前期四川官話音系特點.語言研究,2019(4).
15. 西田龍雄.多續譯語研究.京都: 松香堂,1973.
16. 西田龍雄,孫宏開.白馬譯語研究.京都: 松香堂,1990: 60.
17. 嚴木初.嘉絨語詞匯研究.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4.
18. Chirkova K. The Duoxu Language and the Ersu-Lizu-Duoxu Relationship.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014,37(1): 104-146.
(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成都?610068)
(責任編輯?馬?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