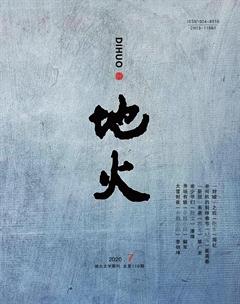蒼蒼蘆葦(外一篇)
尹建國
說起蘆葦,很多人并不陌生。即使沒有見過蘆葦的樣子,就那么一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有位佳人,在水一方”也會讓你浮想聯翩,心潮澎拜,自然會生出去看看蘆葦的想法來。
蘆葦就是《詩經》中所說的蒹葭。古人常常通過蘆葦來抒發春來秋去的時序、漂泊之感,有時候還通過蘆葦來寄托江湖逍遙的隱逸情趣和清貧志守的名節抱負,因而蘆葦被賦予了許多的人文意義。
“白鳥一雙臨水立,見人驚起入蘆花。”“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川原秋色靜,蘆葦晚風鳴。”“淺水之中潮濕地,婀娜蘆葦一叢叢。”像這樣描寫蘆葦的詩句自然能背誦幾首,至于為什么喜歡,卻說不出子丑寅卯來。
我記得一個叫帕斯卡爾的外國人也很喜歡蘆葦。他喜歡的理由很簡單,就一句話:“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蘆葦。”他這句話讓我很是驚訝,沒想到蘆葦也是有思想的。每每穿行在蘆葦叢里,走在蒹葭深處,微風拂過,葦聲颯颯,蒼蒼茫茫,頓感心曠神怡,這大抵是我喜歡蘆葦的天性吧。沒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
我工作的地方有一片蘆葦。說是一片,其實是一片連著一片,用“蕩”字來形容更恰當、更現實。這片蘆葦蕩不知什么時候有的。當地一位漁民說,他祖祖輩輩就靠著這片水域打魚為生。這片葦蕩存在于蒲河濕地下游,蒲河水系屬于遼河支脈,遼河存在了多久,這葦蕩便存在了多久。
站在浦河岸邊瞭望過去,大有接天葦葉無窮碧之感。水天一色,萬頃碧波,密密實實,一望無際。走近看,每一株蘆葦都筆直峻拔,傲然天地之間,蒼茫之下。它們不爭不擠,不靠不倚,亭亭玉立,笑對四季。
春天到來的時候,伴隨著一場又一場的“隨風潛入夜”的雨水,這片濕地上便開始有了生機。那褐黃色的地表之上,一個又一個小小的生命像破繭而出的蛹,頂破堅硬的地表,爭先恐后地伸出尖尖的觸角來。一夜之間,這片濕地便不再枯萎,不再荒蕪,不再寂寞和寒冷,開始變得柔軟、濕潤、明快。那小小的蘆葦見風就長,你追我趕,不管不顧。10多天不見,一片又一片的濕地就變成了葦蕩。葦蕩漸漸蒼翠,綠得葳蕤,綠得蕩漾,綠得醉人。
夏天的蘆葦也好看,不僅好看而且壯觀。用壯觀一詞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因為這片葦蕩里散落著一些油田的抽油機和采油井站以及一些插入云天的鉆塔。這些石油設備無規則地排列著。晴朗的日子里,茫茫蘆葦像是碧空下的一池深藍,那些高低錯落的設備,便成了那深藍下的一片風景。多雨的日子里,河水漫過堤壩,那些沉重而又堅硬的設備,便似浮在蘆葦上的風帆和燈塔。至于那些常年在蘆葦里行走的人們,就像葦蕩里的鳥兒,整天在蘆葦里穿來穿去。
在所有的季節里,秋天的蘆葦是最好看的。“一片一片又一片……飛入蘆葦都不見。”每當秋風乍起,遠處次第漸黃之時,蘆葦便迎來它最為華彩的一章。“江頭落日照平沙,潮退漁船閣岸斜,白鳥一雙臨水立,見人驚起入蘆花。”那些迎風搖曳的蘆花,在白露未己之時很像一個個宛在水中央的美人,在翹首以盼著心上人的歸來。
我第一次走近這片葦蕩時,正逢蘆花正白時節。沒想到,迎接我的就是這片富有詩情畫意的場景,讓我從此喜歡上了這片土地。這一喜歡就是30年,就連頭發也長成了蘆花的顏色。
喜歡蘆葦也不是沒有理由的。老家蘇北屬于黃泛區,村子南頭有一條叫南河的河。河不寬,也不疾,據說是黃河發水沖出來的一條大水溝。溝里長滿了蘆葦。小時候,生活留給我的第一印象便是貧窮和苦難,而這苦難又恰恰與蘆葦有關。
春天,青黃不接,唯見母親挖了茅根晾在院子里,晾干后的茅根便用棒槌搗碎摻在谷子里。那時候便知道蘆葦的根是甜的,能吃。冬天,寒風刺骨,棉鞋是穿不起的。沒有棉鞋,就無法越冬。每當蘆花見白的時候,母親就會去南河里采割蘆花。上凍的日子,一株株蘆花柔順地在母親手里翻來覆去跳躍,半天工夫,一雙用蘆葦編織成的鞋子便大功告成。鞋子樣子雖然丑陋,但穿在腳上即使走在冰面上,腳丫也感覺滾燙滾燙。
從那以后,我便漸漸明了蘆葦的諸多好處來。鋪在床上的涼席,買菜用的提籃都是蘆葦制成。除此之外,蘆葦還可以蓋房子、搭棚子等等。后來,我又查閱了一些資料,說蘆葦不僅可以造紙而且還能入藥。中醫學上說其性寒、味甘,適合用于清胃火,有除肺熱、健胃、鎮嘔之功效;《本草綱目》上謂蘆葉有醫治霍亂、嘔吐等之功效。
不管怎么說,蘆葦作為一種植物,已經深深地融入到了我的血液里。有水的地方就會有蘆葦, 人與葦伴生,可以說是大自然的造化。
又逢深秋,望著一望無際、茫茫蒼蒼的蘆葦,心情亦如那潔白的蘆花在風中搖曳。站得久了,仿佛自己便成了蘆葦。
白露,白露
我的房前是一個院子。
春天時,我種了一些油菜、菠菜、南瓜、冬瓜等。一個夏天過去了,藤蔓爬滿了院墻,地空出了一片。立秋那天,我詢問鄰居,這個季節還適宜種啥?答復是:白露前后適宜種蔥。白露當然是指節氣,我差點予以忽略。
白露,是二十四節氣中最詩意的一個節氣。知道它,還是從《詩經》中得來。“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最初讀它時,我誤以為白露是一位“在水一方”衣袂飄飄的女子名字,要不是老師及時解釋,必定貽笑大方。
再后來,我便知“白露”在先,節氣在后。也許是古人感覺“白露為霜”很唯美很動人,才被安插在節氣之中,為的是讓二十四節氣更詩情畫意吧。
“秋夜長,殊未央,月明白露澄清光。”白露就像一道清涼的籬笆,把夏天和秋天徹底分開。從此再不必眷戀春之香艷、夏之火熱。有人說,夏天是春天的故鄉,秋天是夏天的故鄉,而白露便是宛在秋天的一個曼妙女子,在思念她的家人、她的情郎、她的故鄉。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聽吧,看吧,那露凝而白的景色就像一滴滴在晨霧散盡后的眼淚,點滴到天明。那像霜一樣潔白,像夢一樣虛幻,像寶石一樣晶瑩的朝露,清雅中透著凄美,高潔中散發著光華,怎能不讓人心醉神迷?
說露有五色,是有依據的。《本草綱目》記載:“漢武帝時,有吉云國,出吉草,食之不死。日照之,露皆五色,東方朔得玄、青、黃三色露,各盛五盒獻于帝。”據說,白露是秋天的顏色。這話一點不假,仔細想來,不無道理。露在哪里凝結,便會透射出哪里的色彩來。比如,露水凝結在枯葉之上,便呈棕褐色;凝結在楓葉之上,便呈火紅色;凝結在稻谷之上,便呈綠黃色。露之所以呈現各種色彩,正因為露本無色。正因露本無色,才被古人奉若圣水。有道是:“秋荷一滴露,清夜墜玄天。”
對于白露的認知,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感悟的。小時候,我對于露水是不喜的,甚至有點厭惡。
思緒回到那個小小的村莊,那片蒼蒼的田野,那縷裊裊上升的炊煙里,有關白露的記憶撲面而來。
老家蘇北,一望無際的大平原。每到白露仲秋,露白而凝,正是秋收秋種秋忙時節。在我的記憶里,幾乎每天晨昏,父母下地回來的時候,褲腿和衣角都被露水打濕。即便這樣,父母也來不及喘息一下,便一頭扎進灶臺生火做飯,被露水打濕的衣褲被柴火烘干。
那時,我最不喜的就是早晨和傍晚。但父母樂此不疲。他們習慣了起早貪黑,他們必須搶在白露前后把麥子種下去,把包谷顆粒歸倉。露水越大,說明地氣越重。如果說把大地比作母體,播種下的小麥便是胚胎,那么白露自然就成了羊水。小麥在羊水的呵護滋潤之下,用力地吮吸著來自大地的營養。
當我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父母已經老去。在一個秋天的早晨,我站在老家的土地上,望著一片片綠油油的小麥,驀然發現,那尖尖的葉子上,都頂著一個個亮晶晶的水滴,在晨光映射下,發出炫目的光來。那光,既柔和又耀眼。蹲下來,如果用心聽,你會聽到露珠滑落時發出輕微的聲響。待到日上三竿,露珠在你不注意時,瞬間化為一股清氣,變得無影無蹤。別看露珠僅僅停留了一夜,卻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一生。這一生不為別的,為的只是滋潤大地上的萬事萬物。
“露珠雖小,它可折射太陽的光輝。”這句話誰說的,我記不清了。有時候,我在想,我也許就是父親手里的那粒麥子。只是這粒行走的麥子,離開故鄉已經太久了。
故鄉一別,30多個年頭。白露時節,走在鋪滿露珠的小路上,腳步變得越來越輕盈,任由露水打濕褲腳和鞋子。看來,同樣的一件事,于不同年代、不同年齡,喜與不喜,大相徑庭。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這是曹操說的。他兒子曹丕說:“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看來爺兒倆的情感都寄托給了白露。我不是詩人,也不是詞人,自然寫不出這樣的話來。
白露那天夜晚,我站在院子中央,仰望星空,很想學著古人的樣子,也拽上一兩句詩來,但是搜腸刮肚,最終還是沒有哼出半個字來,滿腦子始終是杜工部的那句:“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