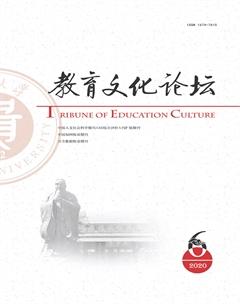圖像學視野下的中國早期電影
王元嬙
摘要:圖像學是西方一種關于視覺文本之主題和內容的分析方法,流行于20世紀。本文以潘諾夫斯基圖像學研究為立足點,選取中國早期具有詩化風格的電影《小城之春》(費穆版)為研究對象,從場景、長鏡頭和符號、格調和內核經驗三個層次進行圖像闡釋,挖掘早期電影中的情感文本、電影圖像與中國傳統經驗之間的潛在聯系,旨在以一種新的文化解釋的方法切入《小城之春》,促進中國電影史論方面的發展,以及相對彌合從圖像到電影基于視覺圖式的藝術理論的距離。
關鍵詞:圖像學;《小城之春》;長鏡頭;失語;時代之眼
Abstract:Iconology is popular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is an analysis method of the theme and content of visual text in the West. Based on Panovskys image research, this paper selects the early Chinese poetic film Springtime in a Small Town(Fei Mu Edi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illustrates the imag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scenes, long shots and symbols, style and core experience, digging out the potential links connecting the emotional texts, film imag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experience in early films, so as to put forward a new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method to analyse the Springtime in a Small Town, and also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history and relatively bridge the distance from images to the art theory of film based on visual schema.
Key words:iconography; Springtime in a Small Town; long shot; aphasia; eye of the times
1948年,費穆版的電影《小城之春》被公認為是體現了中國電影美學的范例[1],同時也是一部具有“詩性品質”[2]的早期中國電影代表作。因而,對《小城之春》的研究于中國電影史和中國藝術精神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但就現狀而言,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文本的文學性(主題、人物、敘事結構等) 方面,對于影像形式、電影語言的研究則相對較少,從圖像學視野解讀《小城之春》則基本是空白。現代圖像學之父潘諾夫斯基在結構主義基礎上曾提出“圖像三層次理論”,這一理論使得焦點從藝術史研究轉移到圖像學研究,即對作品的解釋主要分為三階段方案:一是前圖像志描述(列舉視覺藝術中所看到的人和物),二是圖像志分析(確認主題和題材),三是圖像學闡釋(藝術家賦予作品更深刻的含義與內涵)。本文嘗試從圖像學視角,立足時代高點,對早期詩化風格電影《小城之春》展開分析,并對其圖像研究的不足進行補充,挖掘出背后的時代氣息與文化密碼,以推動中國電影藝術研究在圖像學領域的發展。
一、經典鏡像:《小城之春》長鏡頭的影像特色《小城之春》的藝術表達中雖有短鏡頭用于空間切換,總的來講仍以長鏡頭的藝術感與綜合性為主。影片人物的關系、一草一木,全然體現在以人物運動為前提搖晃且低機位的鏡頭中,人物的運動在搖鏡頭中形成特殊的構圖與動作進而構成不一樣的鏡像。拍攝的角度并非完全符合水平線的標準,而是處于舞臺對準的觀眾席中心的角度,人物動作面對鏡頭的程式化處理,使得以對角線的方式構成的對稱的電影畫面顯得具有平面感但卻不失舞臺劇的效果。這似乎吻合了在圖像學理論中潘諾夫斯基的解釋,即在“前圖像志描述”這一層次中,解釋者不僅要涉及屬于形式分析的范疇中,列舉視覺藝術所看到的人或物以及自然題材等元素,同時要對圖像關涉到的風格、歷史背景所運用的方法進行了解。
電影的每一幀畫面、每一組構圖、女主人玉紋的每一個動作,都可以說是構成了不同韻味的電影圖像。潘諾夫斯基在其《電影的風格和媒介》中提及電影圖像學的概念以及許多關于電影藝術與類型的觀點,并認為歷史片和情節劇影片已經為名副其實的電影圖像學與電影象征主義奠定基礎[3]。似乎聲音脫離了畫面的視覺形象的聲畫對位、主客混合的構圖方式,以及影片人物的程式化動作與觀看方式的表達都具有顯著特征,尤其是以固定視角拍攝的人物對話的長鏡頭中,在城頭上站立,發梢微微卷起且身穿旗袍的玉紋,她架置在腹前的雙手以及回眸,禮言在屋內以背對鏡頭的方式與玉紋對話等,似乎加強了影像的藝術魅力,在視覺與聽覺上表現出電影圖像的一種不確定性,通過主客混合的構圖方式有效避免了人物之間激烈的沖突。《小城之春》中的旁白是以周玉紋的自述直至結尾,但當章志忱出現后,旁白似乎從第一人稱帶有的純粹感傾向于第三人稱的客觀感。從影像的拍攝邏輯而言,章志忱來到周玉紋家中第一次與之見面的場景,聲畫對位由此表現出來。章走向前來,鏡頭畫面是章的中近景,當周玉紋從全景到中近景向中心走來時是章志忱帶有觀眾認同的主觀視角,她在走來的過程中影像表現的是章志忱眼中的玉紋,此刻女主人玉紋成了被觀眾以及章志忱作為主體所凝視的客體,而在此時畫面的旁白卻成了女主人周玉紋的旁白“他竟不知道我跟禮言結了婚……”這些長鏡頭中聲畫對位的表現在《小城之春》中比比皆是,聲音不符合影像標準的正反打的形式打破了畫面的時空局限,賦予了新的寓意,給受眾以獨特的審美感受。
《小城之春》在技法上沒有鏡頭的切換,使得觀察角度的變化無法形成,進而影片中不會呈現出主人公之間“看與非看”的狀態。在四個主人公去郊外游玩劃船的場景中,妹妹和禮言坐在船頭,周玉紋在中間,章志忱在船尾負責搖櫓。這場戲突出章志忱和周玉紋多次的對視,在開始捕捉章望向周的鏡頭中并沒有呈現出任何異樣,畫面是一個章對向周的中近景,接下來對接的鏡頭倘若按影像邏輯而言,本應是章主觀視角中的周的動作與姿態等,然而,畫面呈現的卻是以“他者”身份介入的四人全景式客觀的鏡頭。與此同時,畫面中近景鏡頭中的周玉紋往后面看時,她看向章志忱的鏡頭不是其主觀視點的人物,而是其在章志忱后側方的平視的中近景鏡頭。這種跳脫的鏡頭嫁接方式打破了傳統的連續性較強的一鏡到底式的敘事,雖表達的情感表現極為溫和,敘事上具有較強的寫意性,但始終營造著一種縹渺、迷離、游蕩的言外之意,似乎《小城之春》影像的鏡頭刻意顛倒非看與看的秩序性,打破以主體邏輯的視點出發本該有的鏡頭的連貫性,造成觀眾無法確切地通過鏡頭表現來真實感知人物的關系。這種非看的程式化設計卻在影片的場景中以詩意化視點的表現呈現出來,從而使得場面調度的縱深感、人物關系的連續化更加具有層次感、藝術感。
在長鏡頭跟隨室內拍攝中,使用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和文人擺件。室內畫面構圖中的層次設計:人物處于鏡頭中心,前景、后景的不同身份營造層次,塑造畫面縱深感,影片構圖中道具繁多,費穆更是通過人物的分組、站位和排列使得鏡頭具有縱深感。在電影圖像角度,《小城之春》通過場域來構建的中國式意境表達較為突出,以廢墟設置的城墻的鏡頭穿插在多個場景,空中搖擺的樹杈,斷墻,凌亂的磚頭,延伸至視點邊界的小路,構成了人們運動的場所,并在人物行走時以光影映射放大人物內心的變化。同時也是在這無名小城,對于周玉紋和戴禮言來講是其破落家園的象征,但導演費穆巧妙地避開了正面鏡頭的全景拍攝,并沒有給予小城一個全貌或者中近景的捕捉圖像。而影片中的戴家庭院屬于舊式構造,是由古老且帶有蒼涼感堆砌的青磚與隨風而倒的草組成,隔斷嚴格又整齊的空間,局促且有些昏暗,營造了一種壓抑與失語的格調。電影中仰拍剔除了雜亂的環境,只剩下天空、人物和菜籃,主人公玉紋背對太陽而立,面向畫面右側,菜籃垂落在外的葉子使得畫面增加了層次感,進而人物的背影又增添了些許孤獨與凄清之意。這一幕幕鏡像雖顯得有些破碎與瘡痍,卻平和安寧。一方面反襯了室外的荒涼景象;另一方面配合故事設計通過鏡頭夸大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同時也無形淡化人物實際關系,將人們的哀思與苦悶表現出來,這也為后續進行圖像志描述、圖像志闡釋奠定基礎。從前圖像志角度的描述,僅僅從鏡頭本身對人與物或經典意象來描述,可以看出,他們是擁有傳統的性格與禮教的中國早期一代知識分子,朦朧表達著中國傳統文人對春天的一種體驗,對于季節的感知——感知到的是生命的情緒。而小城之“春”的到來,是對那平庸、壓抑且綿長的詩情的惋惜,就像詩詞中蘊含著詩人的情緒,影片的圖像由始至終流露出一種悠悠的正在漂流著的感傷。而小城的春天到底是哪一種感覺?章與周在城頭上郁郁絮語,好似在相互埋怨當初的彼此沒有主動,而后鏡頭閃回到十年前的場景,讓兩人以一種旁觀者的視角來靜觀曾經這對互訴衷腸的戀人。與此同時,間接性的穿插疊化鏡頭使得此場景具有了平靜又完整的雕塑感。這種閃回的技法在影片中極為常見,似乎是以一種難以消除記憶與現實之間的差異感或對峙感的方式出現,但不免會被認為是一種拼糅的主觀心理化且時空交錯感十足的電影世界。
《小城之春》中的長鏡頭在時空方面追求事件的完整性,并嘗試用每一個鏡頭講述一個獨立且獨有情感韻味的故事。其中以傳統中國畫式的形式展開的長鏡頭構架的是時間的永恒性,基本上每一個鏡頭之后都留有深長的意味,凸顯寫意美的同時,將生活與生存的表達延展至無限。影片在視覺語言應用方面,有較為穩定的“語法規則”,在這些長短鏡頭的功能承擔、鏡頭切換的技巧設計和畫面層次的構圖等影像修辭背后,不乏戲劇舞臺式的表達與蒙太奇理論的成分,具有超然于表現媒介之上的時代氣息與文化闡釋。
二、傳統格調:“賦、比、興”與詩化風格
如若以詩化電影《小城之春》為例展開討論,展示了圖像學中第一層次到第二層次的過渡:身陷小城的女主人玉紋除了買菜和帶回丈夫需要的藥,總喜歡在城墻上走一遭,并長久地在城頭徘徊,好似她有著勇氣突破邊界向往城外的天地沖蕩,回過頭來卻每天過著周而復始的日子。這樣的敘事讓受眾不僅從形式上、內容主題上都能窺探到她那顆受盡壓抑而又不安分的內心世界。從長鏡頭對殘破小城的寫實中,不僅看到了這滿目瘡痍的毀于戰爭的家園,以及對處于困境中的章、周表示出無限的道德同情,同時看到了些許對于婚姻與未來走向的“苦悶”與“哀思”,氤氳著濃郁的感傷詩情。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理論通過在不同背景下對解釋對象和事件所表現的特定主題與概念的方法的準確把握,選擇以圖像、故事大綱與寓意的世界等為主約定俗成的題材作出解釋,進一步辨明藝術作品的題材和故事,并體會其中寓意,這一層次稱為“圖像志分析”。
《小城之春》的圖像志分析,可以說是挖掘傳統理論即“詩詞賦、比、興”的影像表達,與西方電影美學不同在于,其在尋找圖像文本背后的詩化特性的同時,對影片中體現的“賦、比、興”的美學功能進行二次圖像學詮釋與建構,并形成一種處于中庸表達的突出節奏與韻律的中國電影美學風格。古代詩詞文人早已對賦、比、興作出了美學功能性的判斷,閨怨、哀怨的基調和傳統詩詞的韻調,其在視覺藝術尤其與電影中的意境或影像程式化的表現極為相似。《小城之春》中長鏡頭的存在,與疊印鏡頭的運用,介入到主觀、客觀之間的視點中,使得內心情感與現實場景的碰撞交融,在城墻、院子等鏡頭的交替中,周玉紋的面龐、身影疊加到殘垣的城墻之上,似乎有種畫面所創造的情感魅力,移情給觀眾,彰顯一種言外之意的意境美。電影是一種視覺影像,麥茨曾用“令人絕對信服的模式”來評價類型電影[4]。而“模式”并非“視覺模式”,指涉的是具有結構主義意味的電影符號的模式,更多凸顯的是此模式背后的符號的含蓄意指或隱含的“深刻之義”。劉成漢也曾在著作《電影賦比興》中確立了一種電影理論,無論文字與圖像,任何電影影像都會超越純賦體,賦體就是影片藝術性所在,從而更加具備比興之美。同時有學者把電影中表現的“賦、比、興”認為是修辭的表現,其實不然。對比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闡釋,可以簡要歸納為:賦,主在列舉、描寫、刻畫、敘述;比,強調對比、比喻、借比與擬人;興,意在情感層面的移情作用上的交互和融合。《小城之春》看似為寫實主義的影片,實際卻是以傳統詩詞賦、比、興的寫意美學為主要審美基調。導演費穆無論在內涵與主題方面似乎是編排了一部“發乎情、止于禮”的舞臺感強烈的戲劇,其大量女主人的對白、旁白以及內心獨白聲畫同步、情景交融,影片的電影語言經典性地體現了內心情感受到現代性影響的東方女人、中國傳統女人對感傷經驗的態度,卻仍然在傳統禮教規訓中沉默與讓步,發散出一種郁郁的、零碎的情愫。
圖像學不僅在麥茨的電影符號學理論中有所呼應,且托馬斯·沙茨在分析電影敘事中認為,要運用結構主義和圖像志的方法對類型語言與視覺慣例進行深刻解剖,對影片中含有的特殊類型的圖像志需要進行視覺解碼工作[5]。如此說來,影像之間的關照早就留下了苗頭,對于中國早期電影《小城之春》從電影符號學角度看,直接意指是對周玉紋、章志忱等人的不同形象所呈現的圖景或聲景的直接意義為主,而含蓄意指是符號整體本身作為另一個符號的能指并在其他符號的刺激與相互發作下指向新的意義,影片營造的以揭示普遍人生況味、生命體驗的價值意義的真諦的“詩意氣氛”,它的研究才使我們更接近作為藝術的電影。“能指”與“所指”是同構的一種心理實體,“能指”包涵外部的實體產生的影響,“所指”則是在電影畫面中能夠直觀的感知,一級符號系統中的“能指”與“所指”共同構成了二級符號系統中的“能指”。所指是同一個實體,如《小城之春》的風格、象征隱喻或詩意氣氛等。而其能指包涵了外部的實體產生的影響,它們都是由若干符號組成的符號,不論是被意指的還是意指著的[6]。電影表面呈現的是情感文本,背后顯露的卻是深刻的政治隱喻。再者,把“春”寓意著希望的到來,導演為了傳達古老中國的灰色情緒,用“長鏡頭”和“慢動作”構造本劇,大多是凸顯一種整體性的兩人或多人鏡頭的空間感,夾雜著零散化的敘事和一步三嘆息的抒情,讓受眾體會到前所未有的真實自然的表演程式,由此成為中國自成范式的詩化電影作品。
《小城之春》的藝術手段是在規律性、常規性的基礎上表現得更為細膩與溫和,它體現的是中國傳統的格調。如在出游的一場戲中,妹妹哼著情歌《在那遙遠的地方》,似乎聲音與情調互通形成了讓人留戀不舍的聲景,那個美麗的好姑娘對于章志忱而言似乎就在眼前,但這一切想要噴涌出的愛意在理性的面前只可遠觀。長鏡頭的呈現體現了圖像學第一層次到第二層次的轉變,在一個寂靜荒蕪的小城里,從她的神情、動作到無奈和頹唐,苦悶與哀思,還有那不斷的訴說,是戀人之間詩一般的絮語,是關于生活、生存的無限韻味,既體現出對早期傳統中國人作為獨立的個體存在意義上的深刻解讀、糾結與徘徊、倫理與使命,又將人置于一個沉郁疏離的生活語境中,揭示出生活廣延意義的有常與無常。而站在城墻上的周玉紋向遠方眺望或手里拿著籃子在城頭走著,這一切似乎具有了“圍城”的意味,城墻內外是不同節奏的生活模樣與圈定,在這個看似“回”形空間中,卻印證了男女主人公的生存境況與場景設置的互文性,中藥與西醫,風衣與西服,玉紋手中的菜籃、紗巾等,這些道具、服飾等細節場景在空間中呈現出濃厚的“有意味”的形式。從人物動作、神情等或影片的背景得知,外圍或具有現代性意味的一切與個人的傳統思想意識都讓這個家不再完整,在影像呈現上無論是整體建筑還是房子、廳或堂都顯得格外空洞與動蕩。“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在這破敗空虛的城墻上”“一天又一天地過過來,再一天又一天地過下去”,繡花時的姿態、整齊不亂的發髻、買菜的行走、眺望的眼神等,玉紋的內心旁白與身體語言不斷交叉疊印于熒幕前,在傳統禮教的規范下透著柔和與激情,這是一種在社會轉型時期女性外表與內心的現代性表現,但終究被傳統觀念與情禮規訓所囚禁、拋棄,只能無望地成為愛情的犧牲品。
不妨說《小城之春》關注的最主要問題是生活、生存,不僅表現在場景的重復上,也是每個人心理情感的重復,更是對社會平面化與個人創傷性經驗交織的一種極為特別的、多重的關照態度,生活、生存也是遍及小城每一個角落的影像元素。圖像對于觀眾而言,如若意識到生活的苦難,這就是一種積極的姿態。在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理論中,我們不難發現索緒爾、皮爾士和羅蘭·巴特等結構主義者的影子,能指與所指、語言與言語、歷時與共時等概念,同時還能隱約嗅到拉康后結構主義的味道,他對象征主義的深刻理解實際上與他對鏡像理論的看法是一致的。這不僅有利于對利用舞臺表演的方式呈現的寫實式《小城之春》的電影圖像的解讀,與在當時背景下對社會群體命運的真實寫照和思考,透過圖像文化文本的表層意義,更加深入體會到影片的詩意化境界與隱喻的闡釋。
三、經驗內核:沉郁、疏離與失語
“春天”本應是萬物復蘇具有生命力的季節,但作為《小城之春》的季節背景,導演并未把其視作表現主體而給予更多語言進行展現與描述,它的“春”與影片內存的經驗內核一樣似乎始終處于一種抑郁、失語的狀態,雖具有心理抒情與意識流的特點,但不參與任何關于影片故事情節的推進,而只是一種持續縈繞在主人公與受眾心理的季節特征,隱含著超越表現媒介以外的某種象征性意味。第三個階段稱之為“圖像學分析”或“圖像學闡釋”,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明確指明藝術和歷史、文化、社會之間的密切關系,即在這一階段是通過對所呈現圖像的歷史表達的傾向進一步洞察與追問,挖掘其在場的或缺席的圖像背后的隱含內涵。死氣沉沉的春日與受到理性約束且小心翼翼的情意、國與家的破碎與頹敗,萬物百廢待興等待復活,它們因相似性而呈現出隱喻的特征,這些場景同時也映射出圖像作為電影與世界之間的溝通媒介細致入微地把小城中人的落寞與失語的精神圖像外化。同時,在中國藝術表達受到制約的三四十年代里,女性意識、男權異化等意識形態話語,加之價值取向天平的扭曲與失衡等問題,沉郁、哀思與失語成了中國早期藝術、文學創作等方面經驗內核的真實寫照。尤其是導演費穆在影視探索中,內容方面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秉持中國藝術精神,始終堅守作為創作者的文化底蘊與藝術追求,在民族與國家、歷史與文化等方面作出積極探索;形式方面在電影本體語言中融入傳統戲劇的舞臺創作經驗,如“三一律”、傳統戲曲“手、身、法、布”等功夫或吸收舞臺劇分幕式的結構等,并形成民族立場鮮明的具有寫意與寫實式美學風格的電影圖像。
“圖像是文化的表征,關乎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一個階級、一種宗教或一種哲學學說的基本態度,這些因素都會不知不覺地體現于一個人的個性之中,并凝結于一件藝術品里。”[7]雖然《小城之春》充溢著詩意氣氛,但從時代視角而言詩意遠非費穆所要到達的終點。空置的環境和沉郁的背影深處,呈現著他對“生存”更多豐富的思考,思考的深度和影像的意義幾乎和16世紀興起的圖像志研究如出一轍,因為費穆的影像解讀也同樣需要對作品鏡頭語言、題材、隱喻象征與文化意義進行闡釋,只有這樣才能對《小城之春》的圖像學意義進行多維把握。就電影史而言,巴贊認為,蒙太奇的使用在本質上是與模糊不定含義的表達相對立的,而費穆的長鏡頭是長時間獨立畫面的獨立事件,在低角度拍攝與簡約布景下衍生出了諸多意義,在“影”“戲”交融與兼顧下,或會形成過度詮釋的可能,這也與圖像闡釋學異曲同工。巴贊在《電影是什么?》中,對蒙太奇的特性的定義是“僅從各影像的聯系中創造出影像本身并未含有的意義”[8]。從這個意義上說,費穆影像世界的分析角度即:沃爾夫林的意義上——潘諾夫斯基的意義上——布雷德坎普的新“圖像學”,其對應為圖像本身——圖像背后的意義——指稱的圖像是包含攝影和電影等影像藝術在內的“新的”有“意義”的圖像。《小城之春》的時代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它誕生在一個個體情感必須被忽略的宏偉時代中,其在歷史的縫隙中艱難喘息卻又在禮和情、傳統與現代、東西方文化并存的歷史時空中懸置。導演利用舞臺劇的表演方式,影片對形而上的情情愛愛內容的傳達著實較為復雜,并且強烈的舞臺腔使得受眾難免有些“出戲”,但影片卻在假人、假戲中給予受眾真實之感。導演費穆運用“說話的藝術”并滲透舞臺元素,在夸張人物動作的同時,放大影片中的日常生活語言,從而透過圖像更好地表現及關懷當下人們的精神世界。影片中的男女交流相談之時,目光聚焦、轉移只是單方面的,并沒有眼神之間的接觸與碰撞,每每戴禮言與周玉紋同處一個場景時,戴禮言的目光都會在周玉紋身上,而玉紋時常是低著頭或看向前方,有一種轉移式或想象式的交流,這也間接促使了主客之間心理的互通互融,實屬微妙。影片借助身體敏感與美感度使敘事充滿張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影片中始終雜糅著人物關系的陌生、疏離與失語感,同時這也正是費穆這類中國早期知識分子懷著苦惱與哀思,對當時的國家、民族,對他們個人所處社會背景的映射與反應。影片不動聲色地把這種詩意的沉郁、疏離且失語表達得淋漓盡致,這種失語不僅是作為早期知識分子個人所處的困境,同樣是國家和民族對未來的關鍵抉擇的失語。“禮言對我就只成了一種責任……我心里是你,我又覺得對不起禮言。”作為象征著知識分子的周玉紋對章志忱緩緩說道。影片無疑是一部以詩的語言來構成電影圖像,長鏡頭的調度與人物的內心獨白、影片的主題基調無一不是在建構著詩意十足高度風格化的藝術空間,通過視覺語言構成的電影圖像展現人物內心與家國選擇之間的糾結與矛盾,從而創造了一種意蘊豐厚的電影圖像學。
《小城之春》以小城入名,無論是沉郁蕭瑟的小城,還是小城內殘破頹敗的戴家庭院,在如此封閉、真實的空間環境設置中,它們都呈現出處處失語、疏離的狀態,這一切不僅凸顯了導演對影像實景表現的簡化,還體現出其對影片時空外延的限制。在圖像學視野下,對于此種影像結構與文化闡釋更加重要。無論是對人類存在感的關懷,還是對社會現實虛無感的呈現,《小城之春》不僅具有一般電影美學中的影像與修辭含義,而且具有潘諾夫斯基藝術史意義上的深度圖像詮釋學,這也是費穆與其他中國電影導演的不同之處。費穆在藝術創作中具有鮮明的個人經驗與風格,其每個鏡頭的詮釋學意義耐人尋味:一是鏡頭形式本身的意義。費穆手中的長鏡頭脫胎于舞臺,從中汲取場面調度的元素,并夾雜蒙太奇的特性,在傳統的長橫幅畫面的同構下,表達中國傳統藝術的寫意性與審美感受。二是在長短鏡頭切換中彰顯出的“沉郁”與“哀思”的生活空間,并將之引向具有費穆特征的生活圖景。觀眾仿佛在詩化氣氛的情境中捕捉到海德格爾的“林中路”,尤其是俯身低拍的鏡頭對準角色進行拍攝,呈現出人物背后較大展示的天空、庭院或樹木等布景。三是通過鏡頭、影像結構以及時代氣息的表達,還原出影片中知識分子以及費穆本人對情與禮、家與國的態度與心聲。失語的狀態、孤凄的背影、殘破的城墻構建的是人們對未來永恒的思考,或因平庸而無法抉擇的無可奈何。形式不僅僅是形式本身,對長鏡頭、聲畫對立、低角度拍攝、陰影等的使用不僅僅是一種攝影技巧,也是更好地傳達導演的影像風格與文化觀感的形式,承載了在舊中國特定時期的審美趣味和精神內涵。
在寫滿隱喻與象征含義的《小城之春》中出現的場域意象(城墻、家園、房間等)體現的“圍城”困境是永遠存在的命題,是一個我世界和一個大世界的隔離與聯系;其中出現的身體意象(周玉紋、戴禮言、章志忱等),如傳統的東方女人周玉紋受現代性的影響形成身體語言與內心種種矛盾的審美景觀,戴禮言身體的疾病不僅是封建宗族社會沒落衰亡的象征,同時呈現一種因追憶往昔而導致心理失衡并且無生命力的疾病形象,他們身體的痛感與情感的感性在倫理道德的規訓面前妥協,蠢蠢欲動的情意與家國的抉擇終以無望與失落而歸,主人公的生存意識詩意性地在希望和絕望并存的驚異節奏中被含蓄地喚醒。
四、結語
文化人類學家格爾茨認為,“對文化的分析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我所追求的是析解,即分析解釋表面上神秘莫測的社會表達。”[9]費穆“把時代完全放到影片故事的后景”[10],在圖像化解讀的同時,又強調了其媒介性,將身體作為感知的媒介,以自身經驗帶有的反思性切實融入實際的感性時空中去,避免在欲望的柔情中被異化,從而縮小受眾與圖像之間的距離。小城之“春”,它是需要被客觀理性看待的,是一種更加開闊的對生命主體的關照的感受,似乎以不在場強調其在場,有一種故意而為之且飽含內蘊性的“傷春”“傷痛”的意味。
對于歷史的圖像而言,圖像是歷史中的符號,米歇爾在《圖像在符號和意義之間的關系》中認為,符號與意義之間是在時代意義上產生的距離,這種圖像是審美的不同,是觀看者對圖像所構成的表層世界進行聚焦,從而形成的一個具有交叉學科的特點的綜合性審視視角,但每個人都不可以超越自身所處的時代,并且每個時代賦予了人們不同的時代之眼。而對于此刻受眾與圖像之間的距離,即電影圖像與圖像內的歷史和文本,對于它們的解讀雖含有差異,但始終是為尋找電影圖像中的圖景、視覺秩序與覺醒意識。而圖像中的歷史,是需要站在藝術史理論與方法的視角下來揭示電影圖像意義生產的密碼,并詮釋圖像之所以成為歷史的根本原因。圖像學是可以利用時代之眼豐富理論,從而加入視覺文化的研究進行意義與空間的生產,且視覺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建構。畢竟藝術史的研究視角是單一的,透過時代之眼,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角度去生產不同的意義并進行文化傳播。拋開中國早期電影的時代背景不說,圖像學領域很少有從文化經驗內核的角度來把握和探討中國早期電影與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聯系。顯然,中國傳統的詩詞歌賦、賦比興、早期的“影戲”、文學以及電影、戲劇本身,都有著傳統藝術韻味的基調與經驗。透過歷史的圖像,可以深入到整個傳統中國的文化藝術中,如早期中國電影《城南舊事》《一江春水向東流》《新女性》《柳堡的故事》等,有以“春”為敘事背景的影片,也有以“春”為敘事動力的影片,以百分之百的 “在場”的身份推動情節和人物矛盾,或象征希望與未來,它們都有著濃厚的、基于季節體驗下的對于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之后的《黃土地》《悲情城市》等詩意電影,在構建中國民族化詩意表達的藍圖中承擔著不容忽視的角色。在詩詞歌賦中,寓景于情、以景襯情、情景交融等表現值得細細品味,有表現傷春愁緒的“準擬今春樂事濃,依然枉卻一東風”;有表現惜春感嘆的“問春何苦匆匆,帶風伴雨如馳驟”等。對于《小城之春》仍有更多立足時代之眼下的多元闡釋,如電影中的西醫隱喻著外來的文化,同時醫學在當時就是中國文化中的“他者”身份,而章志忱這位外來的男子,其身份為何定義為醫生角色?戴禮言在影片中塑造出病懨懨的精神狀態,其實也是對當時中國的一種影射。“他者”的進入,如若放在后殖民主義的東方視角來觀看,是類似西方對中國的拯救的意味,以一種對這個處于殘垣城墻之內的女人的身體以及精神的解救,同時結局的升華使得受眾體會到影片在這種淡淡的無奈與綿延中走向冷靜與理性的處理迷而不亂,感受到感傷詩情的最終歸屬點。所有的一切與中國的漢文化、詩詞歌賦表達的傳統經驗顯得不謀而合。無論從符號、意義抑或是經驗內核,這一切都需要電影圖像發揮自身場域的優勢,使得受眾在圖像制作場域或傳播場域中,更加開放地根據自身的文化背景作出闡釋與解讀。
潘諾夫斯基的圖像學并非對所有的圖像形式信息都能作出社會、文化、心理方面的有效闡釋,從圖像到電影圖像,其基于視知覺心理學的藝術理論的認知,進行從微觀到宏觀的全方位解釋,以探求電影圖像所延展的意義為最終目標。將圖像學理論引入對詩化電影《小城之春》的“圖式”分析中,可以歸納總結圖式的關鍵元素與創作經驗,或進一步運用時代之眼,回顧歷史、心理等深刻成因,更好促進中國詩意電影的實踐發展,更貼切地與當下時代氣息相呼應。圖像學研究不僅對電影研究具有參考價值,同時也為當下視覺文化尤其是電影圖像學的研究開拓了新視野,進而發掘和闡釋影像世界深層結構的文化含義,這對指導當下中國電影創新性發展,無疑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與時代意義。
參考文獻:
[1]黃愛玲.詩人導演費穆[M].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1998:176-177.
[2]陳墨.流鶯春夢——費穆電影論稿[M].北京: 中國電影出版社,2000:30-33.
[3]歐文·潘諾夫斯基.電影中的風格與媒介[M]//李恒基,楊遠嬰.外國電影理論文選: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387.
[4]克里斯蒂安·麥茨.電影的意義[M].劉森堯,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4.
[5]托馬斯·沙茨.好萊塢類型電影[M].馮欣,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9-30.
[6]克里斯蒂安·麥茨.電影與方法[M].李幼蒸,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9.
[7]歐文·潘諾夫斯基.圖像學研究: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人文主題[M].戚印平,范景中,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5.
[8]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60.
[9]克里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M].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5.
[10]費穆.導演·劇作者——寫給楊紀[M]//丁亞平.百年中國電影理論文選:上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374.
[11]劉漢成.從“賦比興電影理論”的建構經驗到“易電影理論”的創建[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20,34(1):37-43.
[12]蘇文瑜,朱怡淼.費穆電影《小城之春》中的美學與道德政治[J].當代電影,2016(8):80-87.
[13]龐博.試論圖像學對類型電影研究的適用性——以Femme Fatale形象為例[J].當代電影,2017(2):145-147.
——以《山河故人》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