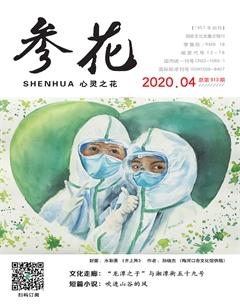從文字禪中看宋詩雅俗關系變革
摘要:禪宗發展到北宋時期,受到空前推崇,形成了“文字禪”。而此時,宋代詩歌也得到了空前發展,形成了“以文為詩”。作為宋代文壇上并存的兩大主流,它們相互影響,相互貫通。本文從文字禪的發展、文字禪對宋詩的影響等角度來看宋詩的雅俗關系變革。
關鍵詞:雅俗關系 禪宗 文字禪
文字禪的解釋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來說,文字禪是從“不立文字”到“不離文字”的轉變,包含了禪宗語錄、頌偈、佛經等各種與禪宗有關的文化現象的語言表達。狹義來說,文字禪是“詩與禪的結晶,即‘以詩證禪,或就是詩的別稱。”①禪宗的傳入,沖擊著宋代詩壇,對宋詩雅俗關系的變革產生了深遠影響,其興衰也影響著宋詩雅俗關系之消長。有學者認為,文字禪發展到宋代,“越來越從無字禪走向有字禪,從講哲理走向講機鋒,從直接清晰走向神秘主義,從嚴肅走向荒誕”。②這是對文字禪的片面理解,文字禪與宋詩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將其與宋詩發展結合起來看,才能真正發掘其內在價值。
一、禪宗頌偈與以俗為雅
(一)宗門語
文字禪的文字往往是簡潔、通俗易懂的,以簡明的語言傳達禪宗思想與人生道理。“達摩曰:‘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③但隨著極端否定文字的發展,另一種潮流悄然興起。在唐代,“宗門語”是一種對話方式,到了宋代向外發展成為一種風氣。“宗門語”由俗語和詩組成,樸素直白,通俗易懂又寓意深刻。例如“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何為立功課。”④語言鄙俗,道理卻淺顯易懂。又如王梵志所寫:“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里。一人吃一個,莫嫌沒滋味。”⑤其通俗程度較之前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正是禪宗中大量“宗門語”的發展,造成宋代詩人引用通俗語言入詩,文體也發生變化,用俗化的語言、體類展現平淡清新之雅。有學者認為,以禪語入詩,情況有三種:一是追求通俗易懂的語言描述;二是追求禪偈的語言平易而含義深邃;三是借用禪偈中的俗語入詩,使其新奇而清雅。蘇軾、黃庭堅、楊萬里、范成大等都有此傾向。
(二)內容之“俗”
文字禪中描繪的內容往往是粗俗鄙陋的,取材于平淡的對話和日常生活,我們以楊萬里的詩歌風格深入分析文字禪對宋代詩人詩歌內容的影響。
楊萬里善于從日常生活的平凡意向中攝取新鮮的形象入詩,語言通俗流暢,提倡口語、俗語入詩,注重表現日常生活場景和自然景象。例如他的《桑茶坑道中》:
晴明風日雨干時,草滿花堤水滿溪。
童子柳陰眠正著,一牛吃過柳陰西。⑥
這首詩以生動、詼諧的語言描繪了一幅生動、清新的田園生活圖景。本是通俗之意象、語言,在楊萬里筆下就有了通俗、淳樸之意。這是楊萬里通俗詩的典型特征,也是其效仿“文人禪”進行“以俗為雅”的成功嘗試。
不同于楊萬里,范成大的嘗試主要體現在新型田園詩上,他運用樸素自然的語言,將細節真實生動地表現出來。風格閑雅,相比于前代的山水田園詩有了生活氣息和通俗化傾向,與文人禪的俗化語言有著密切的聯系。
可見,無論是楊萬里、范成大還是蘇軾、黃庭堅等詩人,他們都嘗試將詩歌的格調降到日常生活,世俗化、通俗化書寫,以俗為雅,使詩歌有了別樣的閑雅之氣。
(三)體類之“俗”
1.“繞路說禪,繞路說詩”
宋代詩人把禪人詩的“繞路說禪”引入詩歌中,而發展出“繞路說詩”。所謂“繞路說禪”是指避免正面解說禪意,而用類似的語言進行替換。“繞路說詩”也是如此,目的是使語義變得迂回曲折,意味雋永。簡而言之,是以借代的方式對詩歌進行語義替換,蘇軾、黃庭堅開一代詩風,江西詩派又大力弘揚,這使得這種寫作方法在當時蔚然成風。蘇軾曾說:“僧謂酒‘般若湯,謂魚‘水梭花,謂雞‘鉆籬菜,竟無所益,但自欺而已。”⑦這是僧人對于一系列佛教戒律的忌諱,宋人卻借鑒這一方法給文章增添新意。
相比于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的特色更為明顯。例如其“打門何日走周公⑧”,這里的“周公”是“夢”的意思,不直接言“夢”而言“周公”,使詩文增添了趣味性和生動性,清新脫俗。
2.翻案法
六祖慧能是翻案法的創始人,所謂翻案法,就是:“正話反做,舊話翻新。”⑨楊萬里在《誠齋詩話》里提出這一概念后,“翻案法”這一方法才算是正式定型。禪宗中的翻案法到文學中便成了新的理論,例如“以故為新”“以文為詩”以及“活法”等理論。我們以呂本中的“活法”為例進行論述。
活法,指的是遵守法度而又超越法度,富于變化卻又圍繞一個本源。活用詩法,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呂本中主張“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這與禪宗中的翻案法是一致的,都是圍繞一個“活”字,正是因為這個“活”才能讓俗變雅、點鐵成金。
二、詩禪滲透與雅俗滲透
宋代提出了空前的重文政策,推動了一大批知識分子的文學創作。同時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市民階層興起,對大眾化、通俗化的要求增強,文化逐漸向大眾化發展。禪宗與宋詩相互融合、相互滲透,詩歌借鑒了禪宗中的語言、技法、寓意以及意境,形成了雅俗共賞的審美特點。在詩歌往通俗化發展時,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傾向,民間崇尚上層的雅文化,上層才子又向往市井生活。
在宋代,曾出現了一股“寒山熱”。唐代僧人寒山的詩歌通俗易懂,對禪宗語言進行了平易的改編,以求更好地接近平民大眾。看似淺顯易懂,實則有著深奧的意蘊,這種詩歌風格不僅在僧侶中受到推崇,在宋代詩人中也備受推崇,尤其得到了上層知識分子的青睞。通過使用簡單通俗的話語,可以使詩歌去掉華麗辭藻的修飾而展現古樸自然之感。在這一點上禪宗和詩歌是一致的,引禪入詩,簡化語言,不是去雅,也不是去俗,而是使語言形成一種強大的張力,達到“雅”和“俗”的至臻統一。
宋代禪宗語錄的流行,促使宋人“做事如說話”:口頭俗語入詩,民間諺語入詩,大眾故事入詩……民間文學對詩歌創作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民間大眾希望效仿上層知識分子之閑雅的文學風格。為了實現其脫胎換骨,詩人采用內容的通俗化與審美風格的雅化,追求高雅、古典的審美風格,將本色與雅之追求融為一體,雅俗相濟。
在南宋后期,繼永嘉四靈詩派后出現了江湖詩派,他們大部分為平民或者身份低微的下層官吏,有江湖習氣。他們的詩風效仿晚唐詩風,字句精巧,長于寫景抒情,大多描寫對隱逸生活的向往以及對社會的不滿。其詩歌刻意求雅,卻往往流于俗套,未能擺脫模擬之氣,卻也成為集大俗與大雅于一體的產物。后期許多江湖詩人將詩歌作為獻媚權貴、謀取利益的工具,這就使雅和俗走向了兩端,背道而馳。
既然詩與禪相互滲透,雅與俗相互交融,我們再來反觀宋詩對文字禪的影響。在文字禪的通俗詩得到流傳時,宋代文人對其表示了強烈的認可,蘇軾就多次對其表示贊賞。如其《子由作二頌,頌石臺長老問公:手寫 <蓮經 > ,字如黑蟻,且誦萬遍,肋不至席二十余年,予亦作二首》:⑩
眼前擾擾黑蚍蜉,口角霏霏白唾珠。
要識吾師無礙處,試將燒卻看嗔無。(其一)
我們只引其第一首,但可以看出,蘇軾對這種寫作方法的效仿和認可。正是蘇軾等大家、顯貴的贊賞,使得使用文字禪的僧人對其由一般接受到積極創作,推動了文字禪的發展及傳播,也對雅俗關系的變革產生了一種強大的沖擊力和推動力。
三、禪宗意境與新雅之構建
禪宗在通俗簡潔的語言背后,有空遠的意境,對宋詩意境的構建提供了一定的借鑒。禪宗將修行分為三個境界:第一個境界是“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芳跡”;第二個境界是“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第三個境界是“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三個境界都有一個“空”字,說明禪宗重視的是一種空遠,一種“悟”,是隔絕人世的幽度清苦,是遠離塵世喧囂的瀟灑解脫,更是一種至高至遠之境。
在禪宗這種超塵脫俗的意境影響下,許多宋代詩人的詩風轉向對“新雅”的探尋,不再單純效仿前代詩歌之語言、結構,而是尋求自己獨特的風格,形成一種“復雅”之潮流。王禹偁、蘇軾、歐陽修、黃庭堅、楊萬里等詩人紛紛為復雅做出自己的努力。嚴羽提出“詩禪說”,主張以禪入詩。試圖一改前人理性詩風,把詩歌變為一種空靈透明、意境高遠的詩歌。
歐陽修也為此做了較大的貢獻。他一反前人對晚唐文體精雕細琢、注重藻飾的文風的學習,對楊億、錢惟演等人的詩風有了較大程度的改變。主張“平淡”,追求“意新語工”的詩境,講求立意新穎、語句精煉,既通俗易懂又內含深意、韻味無窮。我們以其《戲答元珍》為例進行分析: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
殘雪壓枝猶有橘,凍雷驚筍欲抽芽。
夜聞歸雁生相思,病入新年感物華。
曾是洛陽花下客,野芳雖晚不須嗟。
這首詩以小見大,怒而不怨,以平常的景物和簡潔的語言來表現自己的沉思。寫景清新自然,卻又意義雋永,一波三折,感人至深。同時又包含著“繞路說詩”的特點,用“春風”與“花”來借代君與臣。使詩歌表面意義通俗易懂的同時又有著曲折婉轉的深意。這是一種“新雅”之創作文風。這種“雅”不同于文體之“雅”、辭藻之“雅”,而是一種清新自然、通俗明了之雅,意境之雅。
綜上所述,通過對禪宗頌偈、詩禪滲透以及對詩禪意境的分析,可以看出宋詩雅俗之間的關系是相互滲透、相互包容的,以俗為雅又化俗為雅。宋代這種對雅和俗的審美態度,極大地擴大了詩歌主題,使宋代詩歌平民化、大眾化,拉近了詩歌與大眾的距離,也使詩歌題材、內容都向大眾化靠攏,貼近日常生活并有獨特意蘊。
注釋:
①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
②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1頁。
③釋凈修:《祖堂集卷二<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佛藏要籍選刊》第十四冊。④惠能:《六祖壇經》,鳳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頁。
⑤王梵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86頁。
⑥袁世碩:《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三)》,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頁。
⑦《蘇軾文集》卷七二,《僧自欺》。
⑧《后山詩注》卷二《寄豫章公三首》其一 。
⑨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5頁。
⑩蘇軾,撰;王文浩,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
詩集》,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175-1176頁。
參考文獻:
[1]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11.
[2]葛兆光.禪宗與中國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釋凈修.祖堂集卷二《第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和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佛藏要籍選刊》第十四冊.
[4]惠能.六祖壇經[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
[5]王梵志.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6]袁世碩.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三)[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7]蘇軾.王文浩,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2.
[8]邱志誠,黃俊棚.文字禪與宋詩的以俗為雅[J].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8(11).
(作者簡介:李楠楠,女,本科在讀,山東師范大學2017級,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責任編輯 王瑞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