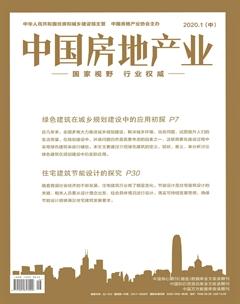西方古建筑的天文學價值研究
劉洋
隨著介紹世界知名古建筑與天文科技相關聯的研究成果的陸續出現,這些從特殊角度觀察古代建筑文明的方式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注意,在理論的支撐下,世界各地陸續發現了與天文相關的古代建筑,這些建筑的深入研究豐富了人們的視野,古代建筑潛在的價值進一步提升,它們所蘊含的科技內容成為人們發掘古代科技,研究人類文明起源的重要依據。
通過本文,我們將通過對西方古建筑的天文學價值實例的梳理與分析,展開了解古建筑所呈現的天文學特征和種種表現。從同類型建筑或單體個案角度深入分析建筑天文學特征和規律。
現如今,人們將古代建筑看成是滿足使用功能的物質產品或具有觀賞價值的藝術品,鮮有人關注到其所富含的科學內容。然而建筑的產生和發展卻不僅限于此。 當科技迅速發展,人類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建筑的多元功能逐漸變化,科學觀測的任務不再由建筑充當,而被先進的科學儀器所取代,人們甚至不再思考建筑是否曾經與天文學有過關聯,古代建筑重要的天文學價值幾乎被忽略了。
天文學是最古老的科學之一,天文學影響著人類建筑活動的始終,離開天文學的影響談古建筑,將不能全面的認識古建筑的價值所在。
在西方,建筑與天文學聯系的研究已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出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語言的障礙,關注亞洲的成果相對較少。而目前在中國此類研究成果還并不豐富。1740年英國考古學家william stukeley對英國巨石陣的研究,奠定了建筑與天文學學科研究的基礎,這也促進了20世紀初天文考古的深入開展,并在20世紀60年代獲得了廣泛關注。
研究初期,人們較多關注巨石陣,金字塔,瑪雅建筑等具有天文爭議的古代遺址,之后,天文考古學者的研究范圍漸漸擴大,一些重要古代建筑的天文特征逐漸被揭示,羅馬萬神廟被專家認定其天窗是巨大的時間指針,哥特大教堂被科學家證實是有濃厚天文科技的“科學的儀器”。
20世紀末,研究天文學因素在古建筑中的價值在西方國家進入了成熟期,研究方法也從初期的現場實測進入到了計算機輔助模擬階段。古代建筑與天文學的研究技術手段逐漸成熟并完善。
為了具體感受一下古建筑中存在的天文學要素的魅力。以下我們具體看幾個實例分析。首先我想提到的是“穹頂”。
自古以來,人們對宇宙的認識達成了一個共識,即天空宇宙是圓形或球形的。不論在中國還是西方,正由于“天是圓的”這一結論成為早期人類社會普遍認可的真理,為表達人們對天空的崇敬之情各國的建筑趨于一種朝向:即模擬天空造型來建造建筑。這種做法在古代中國,印度,埃及等地廣泛出現。
建造穹頂是古代歐洲建筑一直追求的建造理想,簡單來說,穹頂即代表著宇宙。代表著自然。這種建造理想自古羅馬萬神廟開始,之后又有拜占庭時期的穹頂以及文藝復興時期聞名遐邇的佛羅倫薩主教堂穹頂和圣彼得大教堂穹頂。
當我們看到歐洲人設計半球形穹頂的時候,可能大多數時候并沒有想到天文層面的意義。更關心的也許是它是如何建造的,特別是大型建筑的空間,它是如何支撐起來的?
第一個已知,有文字記載的以半球體形式出現的并以天象為裝飾的西方建筑是公元前一世紀由意大利人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年--公元前27年)構思的建筑,它在一本農業著作中被描述,大家并沒有真的找到這一建筑。但學者們被這一文章所吸引,并試圖重現它。可惜,描述遠不能反映現實,在沒有考古遺跡的前提下。公元前47年重現工作以失敗告終。在一幅手稿中,可以看到對它的描述,一條兩邊是池塘的通道通向這個建筑,它在一個池塘的中心,它10.9米高。建筑的穹頂下有圓形宴會廳。穹頂內側標記了太陽,星辰等元素,他這一穹頂設想雖然沒有成功,但從此開啟了人類對建筑融入天文學元素的歷史。
到了公元1世紀,古羅馬用萬神廟造就了人類歷史上穹頂建筑的輝煌。萬神廟位于意大利首都羅馬圓形廣場的北部,是古羅馬建筑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整個建筑的唯一采光口。
從萬神廟開始,西方的宗教建筑開始標榜大的穹頂。之后教堂、法院、議會等重要建筑都開始追求建造大的穹頂。文藝復興時期,由于人們掌握了良好的材料和技術以后,突破了穹頂側推力的技術難題,從而在穹頂造型上愈來愈趨于成熟。
盡管以天文元素為背景的球體建筑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和中東,它并沒有真正的在西方出現和傳播,直到17世紀,主要在大城市如巴黎,倫敦,芝加哥,紐約,波士頓得到擴大。比如,巴黎瑪德蓮教堂,此建筑始建于18世紀末,拿破侖時期,政府決定將他建為贊美法蘭西陸軍榮耀的紀念堂。 整個教堂沒有一扇窗。教堂唯一的自然光線來源是頭上三個圓形穹頂上的圓孔,這一點也是仿照了萬神廟的設計。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教堂“子午線”。
公元325年基督教確立了復活節的日期,但為了能夠提前獲得這個日期,以便充分的準備慶祝,必須投入較多的人力和精力來承擔觀測任務。為了擺脫這種狀況,16世紀教會接納了建筑設計師丹提(Danti)的建議,經過周密的計算,在教皇的獲準下,于1582年在古老的圣瑪利亞(Santa Maria Novella)教堂南部墻面上鑿開一個小孔,用事實記載了天主教向天文學敞開大門的時刻。以最精確的方式測量這個周期,并在教堂的南北軸線上打下一個“子午線”,從南面的墻面上開鑿一個小洞口,被稱作“針孔”,常年接受來自陽光的照射,僧侶或神職人員認真觀察每天中午太陽在經絡上投下的斑點,就可以得出這個數值,從而計算出準確的復活節的日期。
由于大教堂十分黑暗,太陽的光斑經過針孔后在地上的斑點清晰可見,這大大節省了往日繁瑣的計算方法和觀察的不便,子午線并非一條簡單的銅線,在不同長度位置有不同國家城市的刻度。斑點在地上的投影顯示在不同刻度上還可以指示其他信息,另外,一些子午線上刻錄 12 生肖或星座符號,讓正在研讀子午線的人在觀察正午光斑的同時了解當前所在的時間與月份。人們從此可以從每日仰頭觀日的復雜的工作轉到僅關注地上亮斑的簡單行為中。
羅馬教會在天文探索中走在了其他教會的前列,分布在各地的教會紛紛效仿,致使一部分教堂出現了子午線和針孔。這是教會在進行天文觀測和科學探索中邁出的重要一步,也是天文學在古建筑中的價值和應用。
提到子午線,非常聞名的建筑----法國的圣敘爾皮斯教堂一定要提到。它位于巴黎的拉丁區,電影《達芬奇密碼》就在此取景。這個建于1646年的教堂里最有標志性的就是一條金色的線,它橫貫整個教堂,并直指到教堂北側的一座漢白玉方尖碑上,陽光通過窗戶照在這條金屬線上的不同位置,作用類似于我國的日晷。
參考天體的形態或運用天文學知識來建造建筑在古時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古建筑最初建造的目的并非僅為遮風避雨,從一開始就與天文學形影不離。到后來的發展中,建筑雖然朝向更為美觀的形態轉化,但深刻的天文知識卻漸漸巧妙地運用到建筑中。
最后一個我們要提到的建筑,他并沒有真的被實現,但他的名氣非常大。他就是法國建筑理論家布雷 (Etienne-Louis Boullée) 為紀念艾薩克·牛頓(Sir Isaac Newton) 設計的紀念堂,它預示著建筑設計的現代概念開始。18世紀末,布雷只是在他的論文“Architecture, essai sur lart”中發表過。
盡管未建成,但布雷的設計圖紙令人印象深刻并廣泛傳播。他的論文遺贈給法國國家圖書館,在《建筑制圖的藝術:想象和技術》中,美國建筑師托馬斯·沙勒 (Thomas Wells Shaller) 稱牛頓紀念堂為“令人震驚的作品”,它“完美地闡釋了那個時代和人類”。布雷以及他們同時期建筑師的作品對19世紀中期和晚期的法國美術學院產生了深刻影響。
可見,正是由于有了古人對天文因素的研究探索和考量,才讓我們今天有機會能看到如此嚴謹,壯美的古建筑。所以如果當我們站在這些古建筑前只是了解了他的名字,建筑時期,建筑風格,它的材料,他的施工技術等,就認為已經全面了解了這個建筑,進而準備轉身離去,那么它背后更多的故事,那么多人所付出過的心血,智慧就被埋沒了。
通過以上我們對古建筑實例的分析和了解,可以看出研究天文學在古建筑中的價值和意義是:
一、豐富理論研究
在當今中國的理論界,雖對建筑在“象天法地”,“天人合一”等哲學內容有過論述,但研究成果普遍過于概括,而古建筑與天文學內在的科學聯系遠未得到充分認識。而該方向在國內的理論研究資料也寥寥無幾,以至于人們對古建筑的認識不夠全面。
二、提升古代建筑科學價值
在研究建筑史的過程中,古代參考天體的形態,運行方位或運用天文學知識來建造建筑是十分普遍的事情。然而在當前的理論界,人們經常將建筑視為“藝術品”。人們并未認識到建筑內在的天文學價值,本文以古代建筑的天文學特征為研究對象,將建筑內在的科學價值更多的展現出來。
三、深化中外建筑歷史與理論
該研究成果將拓寬和深化中外建筑歷史與理論,使人們對古代建筑有全新了解,激發人們對傳統文化的深挖掘與思考。
我想引用劉松茯教授書中的一段文字:他認為建筑史始終要關注兩個重要的宗旨:其一是拿過來,其二是放回去。拿過來是看,看建筑,看看它們都是什么。放回去是將這些建筑放回到他們所存在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中進行研究。拿過來是看史實,放回去是做理論。拿過來看史實容易,放回去做理論很難。但是學無止境,要不斷地加強自己的專業修養。
從有人類文明活動的三萬多年前到今天,人類把居住空間從洞窟發展為智能化居所,變化之快,每時每刻都有新的風格涌現出來,昨天的風格今天就顯得過時了,我們為什么還要去學歷史,去學那些已經過時的風格?世界確實在飛速發展,但是就像牛頓說的那樣,我們今天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礎之上。前人總結出來的經驗我們要吸取,前人的智慧我們要借鑒,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研究出更有靈魂的成果,才能走得比前人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