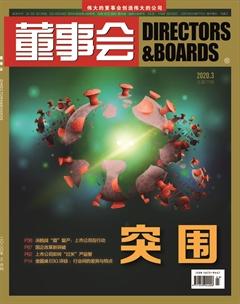“適度監管”才能提升公司治理效率
魯桐
2020年正值資本市場建立三十周年,新修訂的《證券法》正式實施,資本市場面臨難得發展機遇。證監會召開的2020年系統工作會議引人矚目,提出實施推動提高上市公司質量行動計劃,不斷夯實資本市場“晴雨表”功能有效發揮的基礎;今年將啟動公司治理專項行動。
新《證券法》今年3月的實施,使證監會的嚴監管長出了牙齒。新證券法大幅提高對證券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如對欺詐發行,從原來最高可處募集資金百分之五的罰款,提高至募集資金的一倍;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違法,從原來最高可處以六十萬元罰款,提高至一千萬元。保護投資者利益方面,新證券法探索了適應我國國情的證券民事訴訟制度,規定投資者保護機構可以作為訴訟代表人,按照“明示退出”“默示加入”的訴訟原則,依法為受害投資者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在提高上市公司質量行動計劃中,證監會強調要以提高透明度為目標不斷提升信息披露質量。推動上市公司聚焦公司治理、抓實合規底線、強化敬畏“上市”理念:這些當然是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的題中之義。
在任何國家,良好的公司治理都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市場約束、監管約束和自我約束。20世紀90年代以前,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市場約束和自我約束,而缺乏監管約束。過去的二十年,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公司治理已經被列入世界各國政府監管的改革議程。全球經濟一體化在兩個方面影響了公司治理改革。首先,國際競爭加快了各國改善公司治理體制的進程。隨著貿易、投資壁壘被打破,競爭者拓展了市場份額,加速了技術創新,對治理機制帶來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資本市場給公司治理帶來了直接的壓力。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意味著資本更青睞于公司治理好的公司。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積極推動下,各國(地區)不斷完善公司治理的制度架構,在公司治理的制度和監管層面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
但實踐中,公司治理的運作實效并不理想。人們逐漸認識到,依賴自律的公司治理會出現失靈,但一味強調公司治理監管同樣存在危險。加強監管可能僅僅是讓公司、股東更多地做些“畫鉤選項”的表面文章而已。過多地強調公司治理立法導致的最大風險在于,監管者會不顧公司的特定環境是否適宜特定的公司治理架構,而強加給所有的公司。過分嚴格和細致的監管規則,不僅大大增加了治理成本,也侵蝕掉了公司的風險承擔傾向,減弱了公司的創新動力。公司治理的“適度監管”問題值得深思和探討。
公司治理的核心內容是股東會、董事會、經理之間的權力配置。而這種權力配置是來自于公司外部的強制性“規定”還是來自于演變進化的結果,是非常重要的選擇問題。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待公司治理,就能更好地把握其演變進化的實質,特別是能更好地把握公司治理作為“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公司治理規則是由不同利益相關者相互摩擦、沖突而形成的相對均衡,這種均衡的形成需要一個長期演變的過程,而公司治理均衡的狀態是因公司而異的。

既然我們把公司治理看作是一種內生的博弈規則和制度安排,需要各參與方通過反復博弈才能達到相對穩定的均衡狀態。在各參與者進行博弈的過程中,都應該有比較大的策略選擇空間。這意味著,股東、董事、經理之間的權力分配存在靈活的空間,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規定”模式。
因此,有效的公司治理框架應是由法律、法規、自監管和商業實踐共同構成的有機整體。公司治理應以維護市場信譽,保護股東利益和提高經濟效益為目標。當商業環境變化時,公司治理的框架內容和結構均需加以調整。治理體系應避免過度監管,形成支持企業創新、促進提高市場透明度的機制。公司治理的過度監管不僅導致公司治理過度形式主義,降低公司治理的效率,而且導致更官僚化和更短視的公司決策。政策制定者有責任制定足夠靈活的框架,確保透明有效的市場運作,促進問責機制發揮作用。
從近年來公司治理改革的發展趨勢看,維護監管政策的靈活性和平衡性,已經成為下一步各國公司治理政策發展的新方向。一方面,各國積極推出公司治理的“最佳實踐”規則,這些規則并不具備法律或法規效力,屬于自愿性規范和參考性標準。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在給予公司充分的治理選擇權的條件下,通過提高透明度,加強市場約束和問責性。實踐證明,逐字逐句地遵守規范條文不會帶來“良好”的治理,而對廣義的原則的遵循才更重要。良好的公司治理是既能保證企業的控制和責任,又能促進企業價值增值能力的機制和制度安排。
我們期待,改善上市公司治理不是某年或某個時期的“專項行動”,而是堅持不懈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