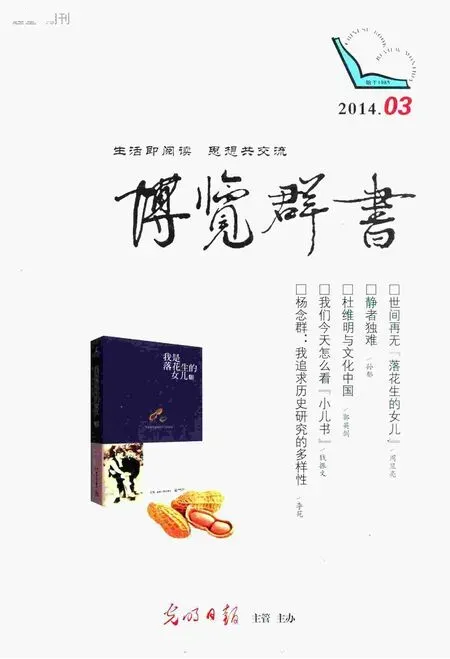聽《論語·為政》講“孝德”
魏學寶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文明古國,在定居農業出現之后,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聚族而居。考古學的研究表明,早在仰韶文化時期(約前5000—約前3000),就已產生了發達的宗族制度。同一血緣關系的人已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族群。他們活著在一起生活和生產,死后也一起葬入宗族墓群。對共同祖先的崇拜與宗族倫理,分別從精神信仰和現實規范兩方面,提升了族群的凝聚力。王朝政治以宗族制度為基礎,宗族制度的維護則離不開宗族倫理。這一社會文化特征的形成,比孔子創立儒家學派還早了幾千年。
儒家學派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形成,孔子“述而不作”(《論語·述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繼承了上古三代文化的精華,因而以族群為基礎的宗族倫理,也成為儒家學派最核心的思想。據存世典籍記載,這一倫理規范,在舜帝時被成為“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左傳·文公十八年》)是其基本內涵。經過三代的發展演變,再經孔子的改造和提升,到了孟子被擴展至全社會,系統化為“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間被規劃化的倫理美德,直至今日,仍對中國社會有重要的影響。
本欄目的三篇文章,即立足這樣的歷史和現實背景,分別對“孝”“義”“廉”三種傳統美德的形成、特點及當代價值等問題做了探討。討論的角度雖有不同,但立足歷史,關注現實,則是其共同特點。因為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國社會雖已有了很大的變化,但敬老孝親、在個人生活及公共生活中“見得思義”、手中有權者能“以不貪為寶”,仍然是我們這個社會需要大力提倡的。這些美德,不僅對我們未來能否繼續“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也將繼續照亮中華民族前行的長途,繼續溫暖人心,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應有的貢獻。
——劉懷榮(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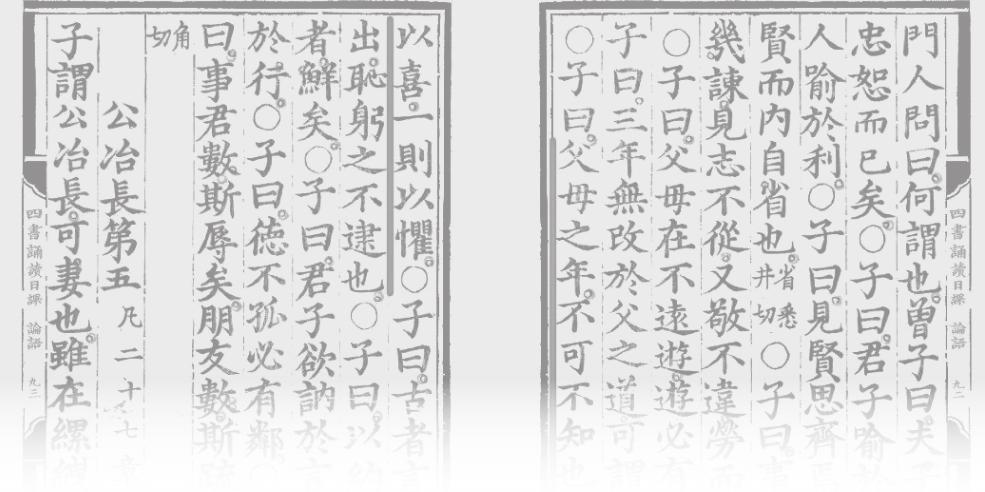
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今天,傳統的倫理道德成為當下討論的熱門話題。在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中,“孝”毫無疑問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論語·學而篇》曾子云:“夫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孝,德之始也。”《孝經·圣治章》“人之行莫大于孝”,唐玄宗李隆基注:“孝者,德之本也。”《后漢書·江革傳》:“夫孝,百行之冠,眾善之始也。”即孝是人之德行的根本。
《論語》中多次討論孝德,最集中的莫過于《為政篇》中孔子針對孟懿子、孟武伯、子游(言偃)、子夏(卜商)問孝而作出的不同回答。
無 違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仲孫氏為魯國三桓之一。春秋后期,魯國公室不振,大權落入三桓之手。三桓僭越公權,多有非禮之為,如“八佾舞于庭”等。
孟懿子問夫子何為孝,夫子回答非常簡短,只有兩個字“無違”,如果沒有后文的話很容易理解為聽從父母的話,不違抗父母。不過后面夫子給樊遲解釋何為“無違”,即“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死”“祭”涵括了人一生中侍奉父母的全過程,簡而言之即“不違禮”。自漢至宋至清,經學家、理學家多以仲孫欺凌公室,僭越禮法為闡釋的切入點,認為夫子告誡、勸導仲孫。不過“無違”的闡釋似乎可以擺脫一時一事之限而具有普遍適用的闡釋可能。在先秦時期法治不彰,禮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后世法律規制、道德規范的智能。從這個視角而言,侍奉父母不可有違社會所認可的、普遍遵守的法律規章、道德倫理。孝是百行之本,擴而充之,尊法守禮,明德修身都是此中應有之義。《鹽鐵論·孝養篇》云:
無其能而竊其位,無其功而有其祿,雖有富貴,由蹠蹻之養也。高臺極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謂孝。老親之腹非盜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
此中,蹠、蹻即盜蹠、莊蹻,前者為春秋后期大盜,后者為戰國初期楚國誤國之奸佞。以無道非禮得之之物侍奉老親,即使再豐厚、再奢華亦不足以為孝,甚而言之,以老親之腹為盜囊,是甚為不孝者。所以遵道守禮是孝的基礎,惟有不違禮、不違社會普遍認可遵守的規范方為孝之始。
當然,這是不是就是孝的全部呢?顯然不是。
“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關于“父母唯其疾之憂”,歷代注家解釋多有不同。王充《論衡·問孔》:“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高誘注:“《論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即做子女的擔憂父母之疾。但馬融、皇侃、朱熹都認為憂者為父母,疾者乃子女,如《論語注疏》引皇侃:
言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為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
如果這句話沒有傳抄的錯誤,那么諸如王充、高誘的解釋在人之常情方面解釋是很困難的,子女只是擔憂父母生病這就是孝,父母其他行為不擔憂,似乎這是對做父母的要求,而非孝德指向做子女的行為的應有之義。因此,馬融等人的解釋更為合理,即做子女的只有生病了才會讓父母擔憂,潛臺詞,其他方面都不會讓父母擔憂。
當然其他方面是什么?皇侃說是“不為非法”,朱熹《集注》:“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即謹言慎行為孝。如果不考慮孟武伯本身自帶的語境的話,似乎“父母唯其疾之憂”的潛臺詞僅僅闡釋為“不為非法”“不容于不謹”似尚有不足。既然云做子女的只有生病才會讓父母擔憂,那謹言慎行、不胡作非為自是應有之義,同時從人之常情揣度,父母關心子女的事情多矣,諸如子女的成長、發展、為人的方方面面都是父母所關注、所關心的,因此,為人子弟,應當克己修身,奮發有為,在父母的期待視野中做出竭盡所能的努力,取得讓自己、讓父母滿意的業績,唯有如此,方能使得“父母唯其疾之憂”。
因此“無違”和“父母唯其疾之憂”從消極和積極兩個角度,從外部約束和激勵明確為人子弟者不應做什么和應做什么,因為比較宏闊,所以具有極大的涵括性。
當然,考慮到“孝”不僅是一種外在的道德規范,亦是源自本真親情的倫理道德,因此僅有外部的約束與激勵來描述孝德的規范是不夠的。
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至于犬馬皆能有養”這句話,歷代注家多有歧義。何晏《集解》引包咸:“犬以守御,馬以代勞,皆養人也。”即以犬馬比喻人子,犬馬皆可為主人服務,如果為人子弟不能尊敬父母的話,所做的奉養之事與犬馬無異。另一種解釋亦見于何晏《集解》所引,“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無以別”。朱熹《集注》解釋:“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意謂人會養自己父母,亦會養犬馬,如果沒有敬重,父母與犬馬就沒有分別了。關于這兩種解釋,陳天祥評價:“以犬馬之無知諭其為子之不敬,於義為安。以禽獸況父母,于義安乎?”翟灝《四書考異》下編卷四亦云:“此義(筆者按:包咸之解)已深足警醒,更何必躁言丑語比人之父母于犬馬耶?”因此,從文字語境和人之常情出發,包咸的解釋更為合理。
當然,跳出這文字詁正之迷霧,這一文獻所強調的核心是“敬”,即敬重父母、尊敬父母。度于人情,父母深溺子女,子女亦多因父母之愛而生狎昵之情,幼時多有撒嬌放癡之舉,而成人之后多有不耐輕忽之言行,因此夫子在此提出敬重的規范要求。《鹽鐵論·孝養篇》云:“以己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因此敬重並不以奉養豐厚與否為標準,而是能夠尊重父母的意愿為準繩,孟子稱衣食奉養為“養口體”,稱敬重父母為“養志”,在《孟子·離婁下》中,孟子舉曾皙、曾參、曾元祖孫三代的例子: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撤,必請所與。問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撤,不請所與。問有余,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朱熹《集注》解釋這一段話:
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撤去,必請于父曰:“此余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余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于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當然,就內在心性修為而言,是否做到了敬即可為孝呢?顯然還不是,對曾子之孝,程頤認為:“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余哉?”
色 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后世對這一段文字的解釋也是頗多紛爭,主要集中在兩點,即“色難”和“弟子”“先生”所指。就“色難”而言,何晏《集解》引包咸:“色難,謂誠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毛詩正義·邶風》引鄭玄注“和顏悅色是為難也。”包、鄭闡釋的分歧在于面容氣色為誰之面容氣色,包認為是父母,鄭認為是子女,二者通俗解釋即為:順承父母的情緒(包);子女對待父母要和顏悅色、柔聲和色(鄭)。朱熹為代表的宋儒多繼承鄭注。關于先生、弟子,何晏《集解》引馬融:“先生,謂父兄也。”潛臺詞,弟子即為人子弟者。這一觀點為朱熹等所繼承,但清儒對此頗有不同看法。翟灝直接認為“先生字似可無訓”(《四書考異》下編卷四),鄭浩《四書集注述要》:“《集注》以先生訓父兄,家庭父子兄弟竟改稱先生弟子,雖曰本于馬注,而他處絕不經見。”劉沅《四書恒解》:“稱父母為先生,人子于父母前稱弟子,自古無此理。”
應該說清儒的質疑是合理的,從詞源來看,將父母稱呼為先生是不合理的,遑論子弟自稱弟子。劉沅繼續闡發:
此章言敬而不愛,亦不得為孝也。服勞奉養,凡子弟事尊長皆然。事父母則深愛,和氣自心,即有他事,一見父母便欣然藹然,凡憂悶之事都忘卻了,此為色難。
鄭浩《四書集注述要》亦持同樣觀點:
師者道之所在,嚴肅之意較多,事父母更當柔色以溫之。夫子言此,乃弟子事先生之禮不足以為孝也。
清儒于此的疏注使得文脈通暢,并且可以和上文“不敬,何以別乎”相承,因此劉、鄭等人的解釋是合理的。父子、師生關系存在一定相似性,故俗語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之語。但這兩對關系有本質的區別,父子關系的核心是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倫理親情,當此倫理親情遭到破壞時,父子關系緊張,不利于以家庭為基礎的倫理道德的構建;師生關系無這份親情,自可不必受此拘束,師可以嚴,弟子亦可以就所學之理與師進行嚴肅的探討,故韓愈《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因為父子與師生這對關系的本質區別,孟子云:“古者易子而教之。”(《孟子·離婁上》)
言偃問孝,夫子教之以“敬”,卜商問孝,夫子回答則在“敬”的基礎上再加一層,即“色難”,“和顏悅色為難”,克服其難,正如劉沅所言,為“愛”。以侍奉師長的方式去侍奉父母,敬則敬矣,但父母子女之間的脈脈天倫親情不在,亦不足為孝,惟有敬之、愛之,方可稱為孝。當然應當看到,夫子之所以在“敬”的基礎上加之以“愛”,是因為“敬”雖應發自內心之赤誠,但就敬的外在表現形式而言,是可以程式化乃至虛偽化的;但源于倫理親情的“愛”雖其外在表現亦可以作偽,但不可持久。因此由“敬”至“愛”,進一步強調孝之真誠,進一步將外在道德規范內化為真摯的倫理親情。
總括上文,應該說夫子所言的四個方面是由兩個維度構成的,即外在的道德規范和內在道德倫理。外在道德規范,即“無違”從負面約束和“父母唯其疾之憂”正面激勵;內在道德倫理,即“敬”從外在表現與“色難”從內在情感。而這兩個維度又構成由外在事功到內在修為的一個發展,從視野來看,似乎越來越小,但從宋儒所言的工夫而言,卻越來越細密。整體呈現出一種由外至內,由言行到心性,由具體到抽象的轉變。這兩個維度、四個方面具備極大地涵括性,故具有很強的普適性。當然對于我們而言要明了的是,夫子所言非孝之至者,而是孝之根本,只有做到這四者方可以為孝。當然,實事求是講,四者的完全踐行亦非易事。
(作者系文學博士,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