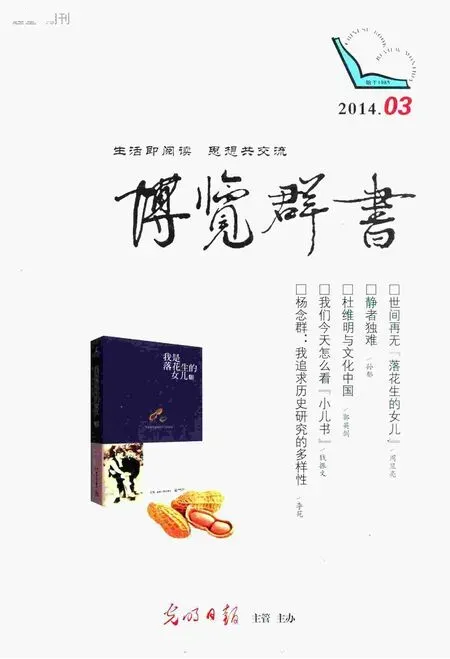“義德”的力量
崔海鷹
義,是中華民族由來已久、生生不息的傳統美德之一。對古往今來的所有中國人而言,義都是一個極為熟悉的字眼兒:它不僅連結著一個個動人的故事,更凝聚著孔孟以來歷代圣賢的諄諄教誨;它不僅意味著一腔熱血,更承載著正義與擔當,有如信念之根,深植于每個人的內心最深處。南宋文天祥就義后,書于衣帶的絕筆贊中有云:“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這位末世丞相,堪稱踐行仁義美德的楷模。也讓我們真切第感受到“義”德的文化光輝。
壹
仁義之道,是中國倫理道德的核心,堪稱立身處世、治國理政的至德要義。董仲舒說:“以仁安人,以義正我。”(《春秋繁露·仁義法》)如果說,“天下歸仁”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社會;那么,“義以為上”則是實現這一理想的大道坦途。因為義德、義行,一個人將更為可敬,也更加可愛;因為義德、義行,一個社會將更為和諧,也更加充滿希望;因為義德、義行,整個國家、社會中的人們,也將生活得更為幸福,更有尊嚴。
孟子曾做過這樣精妙的比喻:“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義,路也;禮,門也。”(《孟子·萬章下》)如果把“仁”看作安身立命的家園,那么,“禮”就是進出的門戶,而“義”則是通向家園的大道正途。對所有人而言,謀生之路固然有千萬條,但惟有“循義而行”,才算真正踏上人生正道,才能真正安身立命。
對個人而言如此,對一個家族,一個企業,乃至整個國家、社會而言也無不如此。人們常看到,大凡興旺長久的家族,無不是講求道義的楷模;大凡優秀、杰出的企業,往往是遵守公德、循義而行的典范;整個國家、社會也只有堅定地遵道行義、維護公平正義,才能真正地實現長治久安、幸福和諧。
義是什么?義,就是我們社會、人生的康莊大道。
自孔子以來,歷代學者皆將“義者,宜也”作為“義”字的通義。據《禮記·中庸》記載,孔子在回答魯哀公詢問時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意思是仁就是愛人,首先要從孝養、愛戴雙親開始;義就是適宜地待人、處事,最重要的就是要尊賢重長。若析而論之,義的內涵大致包含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合理、公平、正義,二是規則、規范、法度,三是應當、責任、擔當,四是常說的恩義、情義等。但最主要的內涵是一、三兩個方面。其中,第一方面是人類社會各種規則、法度、規范的內在依據和靈魂;第三方面是根據公平、正義與合理性的要求,人們應當無條件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等,這是義德實現的關鍵。正是由此二點,構成了義的全德性特征,并對其他德目形成一定的統攝和影響。如孟子常常講義利之辨,實際就是以義代替全德;韓愈明確指出:“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原道》)也是以仁義涵蓋道德。此外,孟子常將仁、義連言,荀子則常將禮、義連言,也有不少人將忠、義連言,信、義連言,均體現了義對其他諸德的規范、制約性。這是義相對于其他德目的一個顯著特征。
貳
古往今來,公平正義最為民心所向往,而百姓也總會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表達對“義”的維護、向往和追求。因此,公平正義,歷來是檢驗、考驗一個政權合法性的最重要依據。證之于歷史,每當一個王朝、一個政權遵守公平正義,施行仁政,必會為百姓所擁戴,從而走向繁榮富強、長治久安。相反,每當一個王朝、一個政權殘暴不仁、違背公平正義,就會迅速失去民心,為百姓所拋棄,被歷史所湮沒。
孔子將公平正義視為政治的本質所在。為此,孔子要求統治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做到“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并明確提出“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正是基于這一立場,對于那些肆意聚斂、危害百姓利益的行為,孔子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鳴鼓而攻之”。(《論語·先進》)
正因如此,孔子尤為看重為政者是否遵行義德,是否具有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自覺,并努力付諸行動。所以,當弟子樊遲請學稼、請學圃時,他卻反復強調:“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論語·子路》)。如果為政者能夠做到“義”,那么四方之民就會自然“襁負其子而至矣”(《論語·子路》)。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孔子進而將義看作執政者與有德君子們的本質要求,期望賢士君子“義以為質”(《論語·衛靈公》),并屢屢告誡“君子喻于義”(《論語·里仁》),“見得思義”(《論語·季氏》),“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其意都是在強調精英階層要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視為自己的本分和職責。
孟子更是高揚“義”的大旗,高度關注社會的公平正義問題。當孟子初到魏國時,就給梁惠王“上了一課”,鄭重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的“仁義治國論”,這正是儒家王道、仁政思想的核心內容。孟子認為,統治者的責任就在于施行王道、仁政,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因此,他強調要“制民之產”,使民眾能夠有起碼的生活保障,然后再施以教化。因此,面對當時的社會不公不義現象,孟子進行了更加猛烈的抨擊:“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
可以說,早在孔子、孟子時代,尚義的價值觀就已形成,并迅速獲得全民族的廣泛認同。兩千多年來,由于先哲的教誨,歷代的教化,中國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士君子們往往會自覺地以尚義為信念,嚴于律己,勇于擔當,既開拓出高尚、光輝的人生境界,也塑造著光明、和諧的國家、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也唯有崇正尚義、先義后利,才能贏得世人的真心敬重。
叁
對為政者而言,利民為公為義,利己為私為不義。利己者,謀小利而招怨;利民者,舍小利而獲大益。“馮諼客孟嘗君”是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特別令人驚嘆的是,馮諼假托孟嘗君之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的“市義”之舉,竟徹底改變了孟嘗君的命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孟嘗君之名)市義者,乃今日見之。”(《戰國策·齊策四》)孟嘗君為了供養自己和家人、臣屬,以放貸而盤剝封邑百姓,屬于典型的不義行為。我們可以想象,之前的薛邑百姓是多么畏懼而痛恨孟嘗君。也可以設想,如果沒有馮諼的“市義”之舉,當孟嘗君落魄而來到薛邑時,老百姓又將如何鄙夷、冷落他。可見,為政者唯有“市義”,唯有一心為公,以義治民,才能獲得人民的真心擁戴。治一邑如此,治一國,治天下又何嘗不是如此?
其理既如此,就對為政者包括國家、社會中的其他杰出人物提出了義以為上的要求。應當看到,在中國文化中,義德是社會教化、士人教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心懷義德,崇正尚義,并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志向和事業的士人君子們,往往就是社會的楷模。我們也可以想見,如果一個人秉持正義,循義而行,那么,其心胸、眼光必超越個人、小團體的利益之上,從而具有更廣泛的價值和意義。這樣的人,也一定會因澤惠他人而受人敬重,最終成長為國家、社會的棟梁之材。
固然,在很多時候,好人未必即得好報,正義也未必立即昭彰,似乎只能無可奈何。但而,作為一種特殊的過濾器,時光無情而公正,如同大浪淘沙,經其反復沖刷檢視,是金子還是砂礫,總會逐漸分明,是非終必有彰顯之日。真正的仁人義士,即便一時遭際不幸,終究將會渡盡劫波,迎來光明和尊敬;而邪僻詭詐之輩,就算一時榮于華袞、氣焰囂張,待真理、道義伸張之日,也必將身敗名裂,受到社會道德的貶斥,遭受國家法律的懲治,可不慎乎!
秉義而行,前途遠大。這一規律,主要是由國家、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所決定的。一個人能自覺認識、踐行其所在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在尊重、維護整個社會的尊嚴和權益,因而也必將贏得整個社會中人的尊敬和信任。正是由于久已確立了崇正尚義的價值觀,遵從道義、義德的,多為社會認可和尊重;而違反、背棄道義、義德的,則往往會遭抨擊和排斥。由此而言,秉義者昌,逆義者亡。一個人是在克己奉公,還是在損人利己,都必將為世人所共見,并由此而導致各自不同的人生結局。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崇正尚義的價值觀有形無形地時時規范著人們的言行,引導人們遵行道義,按社會規范和法度,時時反省自身,改過遷善,以獲得社會、他人更高的認可度,由此而有力地推進了社會文明與進步。
杜甫有詩曰: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范仲淹則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數千年來,這種義德擔當精神代代相傳,沾溉億萬中華兒女。今天,我們也常常看到:當一個人胸懷天下,心系國家、民眾的時候,他的生命格局就將突破自我局限,而具有更廣泛、更永恒的意義,從而成就堂堂君子、慷慨義士。懷抱這樣情懷的義德君子越多,國家、社會就會越文明、和諧,民眾也將更為和睦友善、富足安康。
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要維護國家、社會的穩定繁榮,民眾幸福安康,必須首先弘揚正氣,維護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同樣,在離亂的年代,要“撥亂世,反之正”,也必須從除惡揚善、培育正確的社會核心價值觀入手。義德的首要要素,即是尊崇道義,明辨是非。也就是要從道義、良知出發,明確事情的是非曲直,不可含混,也決不可動搖。面對利益、誘惑,始終堅持“義以為上”,這既是個人良心、品質的呈現,也是對國家、社會所應盡的責任與義務。
英國藝術史家恩·貢布里希曾在他的名作《寫給大家的簡明世界史》中,贊譽孔子為“一個偉大民族的一位偉大導師”,并懇切地指出:“在他的學說的影響下,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學說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關于義德理想及施行途徑的論述。由此而形成的尚義的民族傳統,無疑也是中華民族能夠“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幾千年”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
(作者系歷史學博士,現為中國孔子研究院(曲阜)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