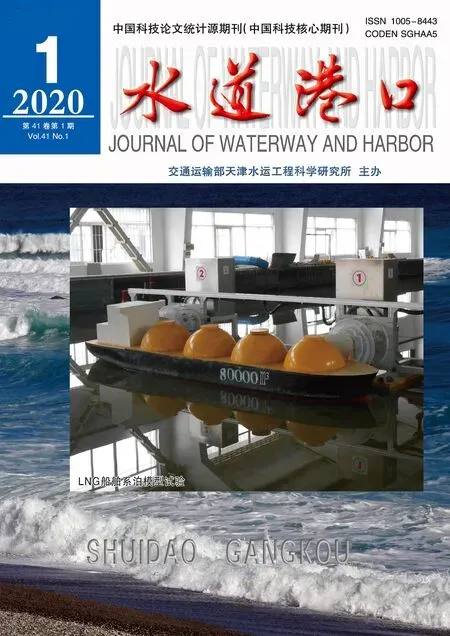基于港口群聯合調度的防臺錨地規模優化研究
彭廣益,鄧夕貴 ,封學軍 ,吳曉婧,3*
(1.河海大學 港口海岸與近海工程學院,南京 210098; 2.中國港灣西部非洲區域公司,科特迪瓦阿比讓 06BP6687;3.廈門大唐房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廈門 361001)
臺風是一種破壞力很強的災害性天氣系統,它對建筑與人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中國是世界上受臺風影響最嚴重國家之一:“十一五”期間,每年大約有8次臺風登陸,造成400余人死亡,逾26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1],隨著防汛防臺風工作水平的提高,“十二五”期間,年平均死亡人數降至近百人[2]。對于沿海港口而言,臺風的襲擊對港口機械、港區船舶和人員安全都構成了嚴重威脅。為了防御臺風對港口帶來的威脅,規劃并建立防臺錨地是港口安全發展的重要保障。
然而在港口貿易不斷拓展、靠港船舶數不斷增加、到港船型趨于大型化與專業化的情況下,我國的防臺錨地卻呈現出規模嚴重短缺、規劃發展滯后的現象。究其原因,是我國海域資源緊張以及缺乏科學合理的建設、管理和維護制度。隨著交通運輸部提出“促進區域航道、錨地和引航等資源共享共用”成為2018年工作重點,合理規劃、優化錨地資源正成為行業發展的熱點問題;同時,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推進與建設也對沿海城市的港口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如何共享、如何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還缺少科學的方法和手段。基于港口群聯合調度的防臺錨地優化研究對豐富我國港口錨地研究、提升港口航運安全以及響應相關政策要求具有深遠意義。
目前國內對于錨地規劃研究主要集中于錨地評價、錨地的規劃、錨泊安全等方面。葉志民[3]、于仁海[4]、張鵬飛[5]、米小亮[6]等利用理論分析、模型構建、指標體系建立、仿真處理等不同方法手段對錨地規劃進行研究。對于防臺錨地,國內學者定性分析多,定量規劃少;對單個港口研究多,對港口群整體需求規劃的少。唐武[7]、吳亞軍[8]分別分析了洋山港與海南錨地基本情況,指出防臺錨地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提出了相關錨地保護政策;孫一艷[9]等進行了單船首尾雙錨錨泊的物理模型試驗驗證了漁港港內錨地允許波高;張亦飛等[10]引入Monte Carle方法建立了漁港避風錨地面積計算的隨機模擬模型,采用不同的概率分布刻劃各相關參數,從而獲得避風錨地面積的概率分布;連石水[11]、沈旭偉[12]等介紹南海臺風特點、我國防臺體制、防臺錨地的選址和防臺錨地的設計要點(包括錨泊方式、錨地主要尺度等),為防臺錨地的設計提供參考。
鑒于此,本文從港口群聯合調度的角度出發,建立防臺錨地的需求和優化模型,基于港口群聯合調度的防臺錨地規模優化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更有很強的理論價值。
1 防臺錨地需求模型構建
1.1 問題描述及模型構建
錨地由于不具備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的能力,所以其重要性往往被忽視,防臺錨地可以在臺風來襲、碼頭發生險情等突發狀況下為船舶提供安全避險的場所。在現今資源緊缺的情況下,應從合理、高效地實現錨地資源利用入手,滿足港口需求。
通常情況下,從經濟最大化的角度,對于錨地需求需要計算最佳錨位數,錨位數過多易造成資源浪費,錨位數過少易導致船舶等待時間過長、港口服務效率降低。但針對防臺錨地,應考慮臺風狀況下最不利的情況,此時安全性取代經濟性成為首位考量因素。故本研究在計算錨地面積需求時將進出港船舶數量與船型列為首要因素。
此外,綜合考慮臺風風力等級、錨地維護情況等因素,構建錨地需求面積函數表達式如下
Ap=F(N(p,t,i),M(p,c,i),D(p,i,c),S(i),K)
(1)
式中:A為錨地面積,km2;N為船舶數量,艘;M為臺風影響函數;D為船舶抗風函數;S為單船錨位面積,km2;K為控制系數;p,t,i,c為港區序號、臺風影響時間、船舶船型和臺風風力等級,即:Ap為規劃所得p港口所需的防臺錨地面積。
1.2 參數標定
(1)船舶數量確定方法。通常情況下,分析船舶的進出港規律需要大量的到港船舶(噸位或艘數)資料。大多數船舶到港規律服從泊松分布,可據此進行推算。本文中對到港船舶數量的確定采用基于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數據的統計法。
AIS數據信息主要包括動態與靜態信息、航次信息、航行安全信息。除了航行狀態可由人工輸入,其他動態信息將由傳感器自動獲取[13]。船舶航行時這些信息每3~10 s記錄一次;船舶錨泊或停泊且移動速度小于3節時,每3 min記錄一次[14]。AIS數據解析后可能有些記錄錯誤,需要對數據進行適當分析與處理,以減少AIS數據誤差、提高后續階段的工作效率[15]。對AIS信息進行數據預處理主要關注其中明顯的數據錯誤并將其刪去,同時對船舶類型進行歸類。利用AIS數據庫的海量數據可以提取目標港區的進出港船舶資料,從而分析確定目標海域的船舶數量。
(2)臺風影響函數。臺風登陸路徑不同,對港區造成的影響也不同。臺風對港區的影響十分復雜。目前對臺風風速半徑的估算停留在人為估算的層面,即根據衛星云圖的臺風云系分布進行風速半徑估算,因此,臺風各級風速半徑因臺風而異,也因人而異,無法獲得準確的結論。在實際運用中,可通過歷年統計資料的分析處理,獲取較為合理的臺風影響系數。
(3)船舶抗風函數。不同船型、不同噸級的船舶的抗風能力不盡相同,導致避臺時間與避臺方式的不同,應分類討論。根據《海船穩性規范》可以計算出距海面10 m高地的風速值V10和船舶最大抗風風速V10max,查詢“我國沿海氣象臺規定風速”的上限值,即可得到船舶的抗風等級或最大抗風等級。
(4)單船錨位面積。《海港總體設計規范》中注明:單錨系泊不適用于防臺錨地,其所需要的水域面積較大,且其系泊力通常難以抵御大風影響,即便增長了錨鏈長度從而增加了錨鏈阻力,仍然難以阻止走錨情況的發生[10],本文不予考慮。錨抓力更大的雙錨泊與多錨泊方式所造成的船身偏蕩較小,但是由于其操作較復雜,走錨時易發生錨鏈交纏,威脅船舶安全。單浮筒系泊是常用的系泊方式,所需水域面積小;雙浮筒系泊則適用于水域較窄的地方,但大型船舶防臺浮筒建造較少。王文淵等[16]根據規范,通過計算機仿真技術計算各噸級集裝箱船舶在不同系泊方式下的所占水域面積,結果顯示在同樣條件下,雙浮筒系泊方式錨位所占水域面積較小,故本研究選擇防臺浮筒系泊方式,在實際中采取加系纜繩等方法增強其安全性。
單浮筒系泊水域的系泊半徑可按式(2)計算
R=L+r+l+e
(2)
式中:R為單浮筒水域系泊半徑,m;r為由潮差引起的浮筒水平偏位,m,每米潮差可按1 m計算;l為系纜的水平投影長度,m,取值見表3;e為船艉與水域邊界的富裕距離,單位為m,取0.1L。
根據《海港總體設計規范》,雙浮筒系泊水域尺度可按式(3)計算
長度S=L+2(r+1)
寬度a=4B
(3)
式中:S為雙浮筒水域系泊長度,m;a為雙浮筒水域系泊寬度,m;B為設計船寬,m。
不同船型不同噸級的船舶,其設計尺度也不同,應根據船舶實際情況進行判斷。
(5)控制系數。在規劃防臺錨地面積時,需要考慮一系列影響因素。通常情況下,除了前文已列出的部分,還應結合實際情況,考慮錨地的維護情況,可以為一定數量船舶提供避臺水域的船舶保證率、船舶在避風拋錨時相互之間的安全距離。控制系數如下表達式
K=f(x1,x2,x3)
(4)
式中:x1為錨地綜合系數;x2為船舶保證率;x3為船舶安全間距系數。
2 港口群聯合調度的防臺錨地優化模型構建
2.1 目標函數
決策變量:
Xp為p港區實際建設錨地比例系數,無量綱;
目標函數:
(5)
式中:Costtotal為綜合費用,萬元;Costcon為單位防臺錨地建設費用,萬元/km2;Costmain為單位防臺錨地維護費用,萬元/km2;A為錨地面積,km2;Costnavi為船舶航行單位路程費用,萬元/km;L′為船舶疏散避臺平均航行路程,km;N為船舶數量,艘;Costothers為其他費用,萬元;p,i為代表港區序號、船舶船型。
在式5中,臺風可能從任意一個港區登陸,將臺風登陸的港區編號設置為q,則有
(6)
(7)
(8)
式中:L′為船舶疏散避臺平均航行路程,km;L為船舶疏散避臺最遠航行路程,km;R為臺風風圈半徑,km;α為實際錨地分布率;Lcoastal為目標省份海岸線長度,km;p,i為代表港區序號、船舶船型。
2.2 約束條件
(1)成本約束。防臺錨地投資成本包括錨地建設成本和錨地維護成本,其費用應控制在一定范圍內。
(9)

(2)航行距離約束。
船舶在疏散避臺的航行過程中,航行距離應滿足以下約束
Lp≥R-Dp,q
(10)
式中:R為臺風風圈半徑,km;Dp,q為p港區與臺風登陸港區q的距離,km。
(3)決策變量約束。
在實際工程中,p港區實際建設錨地比例系數應不大于1,約束如下
0 (11) 福建沿海地區地理位置優越,戰略地位重要,既是省內經濟發達區域也是未來引領全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龍頭和引擎:2017年1~6月,全省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完成25 349.35萬t,同比增長4.3%,集裝箱吞吐量完成735.1萬TEU,同比增長9.7%。同時,福建沿海也是我國受臺風影響最為頻繁的區域之一,年均達到6~8個。其中臺風正面登陸為1~2個,如2010年“鲇魚”,2015年“蘇迪羅”和2016年“尼伯特”均給沿海和全省經濟造成嚴重損失,2017年福建遭遇“納沙”和“海棠”雙臺風襲擊,16萬戶家庭用電中斷,樹木倒伏2 600多棵,海陸空交通全部受阻。但福建沿海存在錨地資源緊張、錨地規劃滯后、商漁矛盾突出、錨地使用不規范、防臺錨地不足和缺乏資源整合等問題。截至 2017 年底,福建全省沿海港口生產性泊位數共 502 個(其中千噸級及以上泊位 386 個,萬噸級以上泊位 171 個),現有錨地已不能滿足進出港船舶和港口生產需要。同時福建省發生臺風頻繁,防臺錨地無法匹配船舶防臺需求,船舶得不到有效的避臺保障,存在安全風險。福建省沿海錨地總體能力緊張,防臺錨地在數量和規模上存在嚴重不足,這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和制約了港口的發展,給港口安全和船舶安全帶來了風險。為了進一步促進沿海港口的可持續發展,保證船舶和港口作業安全,為福建沿海港口規劃防臺錨地十分必要、意義重大。 綜合考慮地址位置和港口吞吐量,將福建沿海港口劃分為五個地區:寧德港區、福州港區、湄洲灣港區、泉州港區和廈門港區,分別編號為1~5;利用IMO(國際海事組織)的船舶AIS數據庫的海量數據直接提取目標港區的進出港、過路及停泊等船舶資料,并利用AIS數據的船舶MMSI編號,通過查詢相關網站獲取船舶基本信息,對目標港區2016年7~9月的AIS數據進行統計,得到第p港區平均船舶數量N:N1=1 341、N2=939、N3=298、N4=787、N5=1 847。 選取7月22日、8月22日與9月22日3 d的AIS數據,每天隨機抽樣500艘船,共計1 500艘船,進行船型統計,獲得有效樣本1 205個。得到各港區船型所占比值,如表1所示。 由于受臺風影響較大的往往是海上貨運船舶,本研究在計算臺風影響狀況下防臺錨地的需求量所考慮的船型中,只考慮貨船、集裝箱船與油輪,分港區各類船舶占比和船舶數量如表2。 表1 分港區各類船舶占比與船舶數量Tab.1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ships and number of ships in different ports 艘 表2 分港區平均船舶尺度Tab.2 Average ship size by port area m 通過AIS數據、中國臺風網歷史臺風登陸資料、《海港總體設計規范》、相關文獻與實際調研結果,確定各參數值,如表3所示。 表3 福建省防臺錨地需求模型參數表Tab.3 Parameter of Fujian anti-typhoon anchorage demand model 表4 福建沿海規劃防臺錨地面積Tab.4 Coastal planning of fujian anti-typhoon anchorage area 經實地調研了解到,雙浮筒系泊方式使用率較低,故防臺錨地面積計算僅計算單浮筒系泊方式所得面積。通過上述所獲得的各參數值展開計算,得到福建省沿海港區防臺錨地面積,具體見表4。 根據上述防臺錨地需求、船舶數量與費用,確定各參數值,如表5所示。 表5 福建省防臺錨地規模優化參數表Tab.5 Optimal parameters of anti-typhoon anchorage in Fujian province 表6 分港區實際建設面積比例系數Tab.6 Proportion coefficient of actual construction area of the port area 利用表5中各參數值,計算福建省分港區防臺錨地面積優化模型,所得結果如表6所示。 計算結果顯示,基于省際聯合調度制度,綜合考慮建設預算與航行成本兩方面因素,防臺錨地面積實際建設規模的比例系數分別為:寧德港區0.60,福州港區0.78,湄洲灣港區0.95,泉州港區0.94,廈門港區0.41。即經過優化,福建省各港區防臺錨地實際建設規模分別為:寧德14.56 km2、福州15.32 km2、湄洲灣8.92 km2、泉州15.50 km2、廈門15.24 km2。 上述錨地規模優化模型是基于福建省取得最大綜合效益的角度,結果的含義是指在港口群聯合調度情況下,福建省所需建設防臺錨地的最小規模。由于未考慮相鄰港口群實際錨地容量,上述結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分析發現,在考慮福建港口群內部及相鄰港口群(浙江沿海和廣東沿海港口群)聯合調度的情況下,優化模型所得分港區防臺錨地實際建設比例系數港區與地理位置相關,總體上呈現出由福建省沿海中部地區分別向兩邊遞減的規律。 本文以防臺錨地為研究對象,在進行實地調研的基礎上,分析借鑒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建立防臺錨地需求模型與基于港口群聯合調度的防臺錨地優化模型,系統整理福建省錨地的基礎資料,結合其自然條件與防臺錨地現狀,對福建防臺錨地進行優化,并基于所得結果提出相應規劃建議。結果表明在港口群聯合調度情況下,福建省所需建設防臺錨地的規模要小于一般錨地建設需求。基于資源共享、聯防聯調角度出發建立高效、完善的防臺錨地,有利于我國加快推進綠色交通發展、推進資源集約節約循環利用,也對提升我國對各種社會突發事件的戰略保障有重要意義。3 案例分析
3.1 數據預處理


3.2 防臺錨地需求確定


3.3 防臺錨地規模優化

4 結果分析

5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