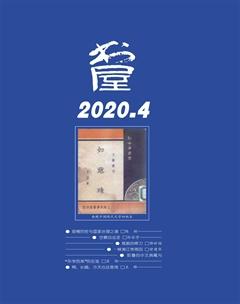中西對話中的自然法思想
康曉蓉
一
當代美國最具世界影響力的法學家之一哈羅德·J.伯爾曼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在其所著的《法律與宗教》一書里,他從廣泛的意義上來談“法律”與“宗教”,并指出,“盡管這兩方面之間存在緊張,但任何一方的繁盛發達都離不開另外的一方。沒有宗教的法律,會退化成一種機械的法條主義。沒有法律的宗教,則會喪失其社會有效性”。
然而中國的法律傳統最初乃執行道德的工具,從某種角度來說可謂附加了刑罰的“禮”,為了禮教而設的實踐性法制,這樣的法律不太關乎信仰,也不要求其神圣性。吳經熊從一開始就站在東、西方文化對話的高度來研究問題,也因其一直懷著對推進中國法制的理想而所致。
1917年春,吳經熊和好友徐志摩同入天津北洋大學法科。時間不長,北洋大學法科被并入北京大學,吳經熊回到上海,準備在上海找個學校繼續讀書。正好這之前的1915年東吳法科成立,掛靠在東吳大學旗下(東吳大學是1900年由美國基督教監理會創建的私立大學,乃中國第一所西制大學)。東吳大學法科其實是一所教會學校,院長蘭金是一名敬虔的基督徒,他想方設法將學生引向基督信仰,宗教課程當時是被作為必修課的,《基督宗教的上主與世界觀》為指定教材。吳經熊在這里第一次讀到了《圣經》就很喜歡,加上蘭金的言傳身教,1917年冬吳經熊成為一名基督徒(該宗派屬循道宗),那年他十八歲。
1920年夏,吳經熊在東吳大學畢業后留學美國,在密歇根大學法學院學習,1921年獲法律博士學位,后赴巴黎大學、柏林大學、哈佛大學訪學。1921年5月,吳經熊在國際和平卡耐基基金的資助下來到了巴黎大學。“我盡可能地多讀多寫,盡量仔細觀察,深入思考,因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要拯救我的國家,啟蒙我的民眾,振奮我的民族,使中華文明跟上時代的步伐”。在此期間,吳經熊與導師霍姆斯繼續通過書信交流。
1922年初,吳經熊來到德國,在柏林大學師從新康德主義法學派首創人施塔姆勒。施氏著重于法律的概念和邏輯,提倡客觀正義法律概念的建構和法律原則的推演。而霍姆斯的法律哲學重實用、洞見、經驗,警醒系統性思維對洞見的遏制。在兩位觀點不一甚至有些較大張力的大師之間,吳經熊努力讓兩者的觀點有更高的綜合而青出于藍。
1923年秋,吳經熊從歐洲回到美國,以研究學者的身份進入哈佛法學院,追隨羅斯科·龐德而得社會學、法學的精要。龐德的法學思想對當代法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了“法”這種現象,給法學研究帶來了不同的思維模式。
1924年5月,吳經熊歸國后執教東吳法科。1927年4月1日,東吳校董會在收回教育權的呼聲高漲的背景下同意法科教務長的辭呈,并改東吳法科為東吳法學院,決定由吳經熊擔任院長,時年他才二十八歲。吳經熊執掌東吳法學院的十年,是東吳法學院的黃金時代——吳經熊作為學術權威撰寫學術論著、參加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帶領師生翻譯西方法學名著,引領法學時代潮流。
1929年,吳經熊任上海特區法院院長,在任期間很多公義、良善、準確等皆備的精判決,讓人拍手稱贊;1933年任國民政府立法院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1945年任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執委;1946年任駐羅馬教廷全權公使、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等。他的司法實踐內容極其豐富——擔任律師,維護了法律的尊嚴,開創了一種可貴的追求公義的社會風氣。他在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擔任推事時,試圖將“中國法律霍姆斯化”,以堅持和維護司法獨立原則;擔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法律顧問時,試圖將工部局的行為納入到中國法制的軌道;擔任聯合國制憲大會中國代表團法律顧問,組織起草《聯合國憲章》的中文文本。
1950年,吳經熊出任美國新澤西州西頓哈爾大學法學教授。1966年,移居臺灣,出任中國文化學院教授。他一生的著作二十多部,涉及法律、哲學、詩歌、宗教、自傳等,《法律的三度論》、《施塔姆勒及其批評者》、《超越東西方》、《法律哲學研究》、《內心悅樂之源泉》、《正義之源泉:自然法研究》、《自然法與基督文明》等。他所全心貫注所翻譯的《圣經》及《圣詠譯義》,文字優美如行云流水,深彰中國文言之美,并蘊《詩經》之風范。
二
縱觀吳經熊的一生,就如他在其自傳《超越東西方》的后記所言:“在我回顧自己五十年的人生歷程時,覺得它就像一支曲子,其中關鍵音是愛。我的一生都為上主之愛所環繞。我人生所有失落的書葉都為祂的愛手所拾起,裝訂成為有序的一冊。實際上,愛的神使一切的事都變得甜美了。”吳經熊十八歲信基督教,初信時很火熱,二十一歲到美國留學后信仰冷淡下來。三十八歲時神奇地峰回路轉,重回基督懷抱,虔誠、篤定,晚年在學術上對中國哲學與文化的研究增多,但對基督信仰至死不渝。那是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上海淪為孤島,吳經熊于他的同學袁家璜家中避難,袁家夫婦均為天主教徒,對其影響頗大。他讀圣女小德蘭的《靈心小史》時,感覺好像句句是經他自己心里發出來的。于是,吳經熊對教理和人生真義恍然有悟。
那時,吳經熊經歷了婚姻、情感、理想、國家等多種迷惘和危機。他一生錢最多的時候大抵是1930年從法官轉做律師的三年期間,他每晚都出去應酬,沉湎于酒色和算命看相。從小兩家父輩就定親的妻子李友悌不識字,和自己差距太大,吳經熊曾一兩次提過離婚,但又感良心不安。就在妻子答應他四十歲可娶妾的誓約快到期的時候,他皈依天主教,娶妾的事自然化掉了。妻子不再因他外出的放蕩而哭泣,孩子們不再因父母吵鬧而冷漠,他的眼光與之前截然不同了:“我更多看到她那美好的內在品德。以前是覺得她配不上我,現在是感到自己配不上她。”“每次我與妻子一道跪在領圣體的圍欄邊時,我都感覺到一陣陣的喜樂和贊嘆涌過我的心里。我們感到我們的婚姻本身好像每天早上都得到更新,而每次更新又加深了我們的愛。”
在個人理想和家國抱負上,吳經熊曾有熱誠的法律救國觀。1924年5月吳經熊回國時寫給霍姆斯的告別信中說道:“去啟蒙,去使卑微者高尚,使無樂者歡樂,使工人獲得基本工資,使無房者有住處,掌握生命并將它引向更純凈的通道——這些問題是我要致力于解決的。”那時他樂觀地相信中國將要步入法律的文藝復興時代,這將改變一個古老的民族。回國后,他在法律踐行中一直標舉正義為法與法學的最高準則,強調“法律以爭訟為發源地,以公道為依歸處”,追求法律圖景是一個統一的規則體、統一的意義體。然而現實的情景是:“紙面上的法律規則與當日中國的社會現實在許多問題上之捍格不入自不待言,欲借助立法而強行改變現實以達成事實與規則的一致,如‘吳氏憲草希望借由立憲而實現權力制衡、民主政制,也同樣非一蹴而就。”當然還有比這些更深層的,吳經熊說自己偏愛平等勝于嚴法,精神勝于文字,仁慈勝于正義,沒有人比他更欣賞羅馬人的格言:“最高的正義也是最大的不義。”
當吳經熊首次讀到《圣經》里圣保羅的話“文字令人死,精義卻叫人活”時,他就知道自己注定了要成為基督徒。法學家的吳經熊對此似乎心有靈犀,他大概是在1937年寫下的一則札記中說:“我當法官時,曾認真地履行我的職責,實際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內心深處,潛伏著這么一種意識:我只是在人生的舞臺上扮演著一個法官的角色。每當我判一個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靈魂祈求,要他原諒我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為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為我的意愿。我覺得像彼拉多一樣,并且希望洗干凈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盡管他也許有罪。唯有完人才有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是,完人是沒有的。”
三
在早期的文章《中國古法典與其他中國法律及法律思想原始資料選輯》中,吳經熊提出中國法律史上有類似于西方不同法學派的論說,“中國發展出一個自然法學派,以老子為鼻祖;一個人本學派,孔子為首,文王為典范;一個實證學派,以商鞅為領導人物;而最后一個歷史學派,代表是班固”,從而提出中國法律思想足以接受近代的社會法理學。他五十六歲時出版的《正義之源泉:自然法的研究》一書中仍念念不忘將中國文化理念以西方法學思想來重新闡釋。比如在《正義之源泉:自然法研究》一書中他寫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一論述如何接近于圣托馬斯之法哲學理論——而在那之中,永恒法、自然法和人法構成一連續之序列。“天命之謂性”實指天意天恩之綢繆——也就是永恒法之代稱;“率性之謂道”合乎于“圣托馬斯所謂之理性造物對于永恒法之參與”,而這一“率”之道或參與之本身,實乃自然法之體現;而于自然律法之精純提煉,實乃文化之功力,它包括了人為法及其之禮儀。這類雖有過度詮釋之嫌,但其初心可鑒,怎樣將西方社會本位論的法律精髓帶給中國、造福中國。
這種建構不止于法學思想理念,也深深植根于吳經熊心之所系的中國法制建設。現實的捍格不通讓他緊緊依靠信仰來反省思索,以期突破。他的兒子吳樹德在為《正義之源泉:自然法研究》在大陸出版時的前言中所寫:“他能一直保持某種客觀中立和不偏不倚,不讓霍姆斯引導他去完全接受主要是霍姆斯主義式的法律命題:一種主要根源于實用主義、實證主義和功利主義的法律體系。父親從功能上又從形而上的角度理解理性。通過這個他分別看到法律科學的演化以及圣靈的造化……他將自己本國傳統資源中的精華部分,帶到他所受洗的宗教以及普遍性道德里。”
怎樣在根與新葉以生命的本源處去理解呢?吳經熊寫道:“永恒法是根基,自然法是樹干,人法之不同部門則是其枝葉。自然法為人法之基礎,還構成了人法最為重要的源頭。”對此,他還在書中專門配了一株大樹的圖畫,似乎用此方式將“法”的生命體生動呈現在人眼前,這是既有別于奧古斯丁、阿奎那的邏輯思維,又符合東方人的直觀思維,同時又暗合了圣父、圣子、圣靈的位格性的一種表述。所以,吳經熊的自然法思想較前輩更帶著一種質樸而活潑的生命性,也從中呼吁唯有敬畏神圣、尊重生命,法律界才可能恢復榮光。
吳經熊在《正義之源泉:自然法之研究》中對自然法從倫理、良心、衡平、公正、真善美等維度,以及心理學、司法哲學與普通法史等角度予以檢驗和論證時,以洋溢著熱情的詩性文筆直呼:“在上帝之中愛與智慧合一。”“普通法,不僅建立于正義之上,也根植于恩典之中。”進而多方論述信仰、理性與法學思想之間的關系,如:“理性中有信仰,信仰之中亦有理性,正如在其他任何地方:斜陽普照,影與影交疊,無以分疏。”“思辨理性處理原因與效果,而實踐理性則主要關系目的與方法,前者目標為真的問題,后者則以善為目的。”“法律所屬之實踐理性,在確定性之問題的定位上有別于思辨理性。”從而不斷提醒人仰望至高者,高舉真正的公平與正義,讓人如同敬畏上帝一樣尊重之:“公平之心正如樹一般,其扎根于大地之中,而一項真的權利則是深植于自然法與正義之中的。”
當落實到具體的法律與道德應用上時,吳經熊顯示出他的高度。如果將之理解為吳經熊的宗教狂熱,那就與之相去甚遠。那種儒家的濟世理想始終在吳經熊的血脈里,即便他在晚年寫的《禪的黃金時代》,也是為著中國傳統哲學文化的精華怎么樣能在當下的時代發揮出來。為此,吳經熊對《中庸》的開篇語“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都可做出天才的法學解讀,但他絕不是也從不局限于某種國家至上或文化主義,吳經熊的心里始終有一種集合東、西方之長而有超越東、西方的世界理想。他說:“將基督宗教稱作西方的,這對它是不公平的。基督宗教是普世的,實際上,在一些事上西方要向東方學習。因為,從整體來說,東方在自然沉思方面走的步子要比西方在超然沉思方面遠……東方太早地進入了沉思階段,西方卻還在推理理性階段拖拖拉拉。東方是小偷,西方卻是天父的不肖之子。但這個兒子應該可以向小偷學習很多東西。”
因此,對自然法在相應的文化處境中的合宜理解與運用,他帶給中國人前所未有的廣闊視角和法律神圣性,并真摯地盼望著自然法能真切而活潑地體現在具體的家國與生活中,“一個偉大國度將給予人類一個寬宏而十分新穎之范例,一個總由高尚正義與仁慈所指引的民族范式”。
(吳經熊著、張薇薇譯:《正義之源泉:自然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