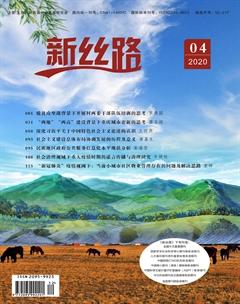建設我國生物安全治理體系的思考
摘 要:隨著世界范圍內頻發嚴重的生物事件,我國面臨的生物安全形勢也非常嚴峻,需從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深刻認識生物安全的重要性,構建新型的生物安全治理體系,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筑牢“防火墻”,意義重大。
關鍵詞:生物安全;生物威脅;治理體系
2020年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一、我國生物安全的現實境遇
1.頂層設計生物安全規劃日趨完善
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已將生物安全納入國家非傳統安全的戰略視野,將大規模傳染病等領域納入關注視角,并制定各種生物安全戰略或規劃,如《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十三五”國家科技創新規劃》、《“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相關部委也提出了《“十三五”生物產業發展規劃》、《“十三五”生物技術創新專項規劃》、《“十三五”衛生與健康科技創新專項規劃》、《“十三五”健康產業科技創新專項規劃》等,為生物安全研發提供了相關技術支撐和平臺建設資源保障。
與此同時,國家先后頒布了與生物安全有關的如下法律和條例:《植物檢疫條例》(1983年,2017年第二次修訂)、《國境衛生檢疫法》(1986年,2018年第三次修正)、《傳染病防治法》(1989年,2013年第二次修正)、《進出境動植物檢疫法》(主席令第53號,1991年,2009年修正)、《動物防疫法》(1997年,2007年修訂)、《生物兩用品及相關設備和技術出口管制條例》(2002年)、《病原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條例》(2004年,2018年修訂)、《生物技術研究開發安全管理辦法》(201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2019年)。《刑法》中涉及生物安全的條文共有17條,對傳染病、生物恐怖、外來生物入侵和生物資源保護等進行了規定,但有關人類遺傳資源管理和生物技術謬用防控的條款尚屬空白。2019年10月23日,我國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2020年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再次強調,要盡快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和制度保障體系。
2.生物安全科技工作有所突破
(1)我國在重大傳染病防控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對新突發病原體的發生、傳播、致病機理、防治和預警方面取得一系列進展,如發現了蝙蝠源冠狀病毒、絲狀病毒等烈性病病原體的起源、中間宿主、病原體與中間宿主的共進化關系以及跨物種傳播感染機制等,并分析了H7N9、H5N6、EAH1N1等新發突發病原體的發生、重組、播散、損傷機制;成功研發鼻噴流感減毒活疫苗。并研究發現了1600多種新病毒,另建立了野生動物疫源疫病數據庫、鳥類遷徙數據庫、野生動物疫病樣本庫及預警示范基地,為未來野生動物源性新發突發傳染病監測預警奠定了基礎。
(2)生物安全實驗室為國家生物安全提供有效裝備支撐。我國現已形成初步覆蓋全國、功能較為齊全、作用發揮較為充分、管理較為規范的生物安全實驗室體系。截至目前,已建成近80個三級生物安全P3(BSL-3)實驗室和3個四級生物安全P4(BSL-4)實驗室,覆蓋2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3)外來物種入侵甄別與防控初步形成體系支撐。在外來生物入侵防控基礎研究及其防治技術與產品方面取得顯著進展,入侵生物學學科框架體系初步形成。建立了上千種外來有害生物的DNA條形碼識別或種特異分子檢測等快速檢測技術與產品,開發了多物種智能圖像識別APP平臺系統,實現了重大入侵物種的遠程在線識別和實時診斷。
(4)生物安全特種資源庫初步建立。我國陸續建成囊括野生動植物種質資源、微生物資源、入侵生物標本資源、人類遺傳資源和生物信息資源等生物安全特種資源庫。如國家重大科學工程“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亞洲最大的醫學昆蟲標本館、入侵生物標本資源庫,以及中國典型培養物保藏中心、中國普通微生物菌種保藏管理中心、中國微生物菌毒種保藏中心、獸醫系統菌毒種保藏中心、中國烈性病毒資源保藏庫等。
3.生物安全防御的短板和弱項
(1)頂層設計針對性不強。雖然我們出臺了各種《綱要》、《規劃》和一些規范標準,但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一部完整的《生物安全法》,《刑法》里面僅有17條涉及生物安全。2004年我們出臺的《傳染病防治法》,在傳染病應急事件和響應管理上規定的不夠完善[1]。另外,相對于美國的盾牌計劃、生物監測計劃、生物傳感計劃和“生物防御曼哈頓工程”,以及《國家生物防御戰略》和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我們國家缺少具有國防和軍事意圖的科技項目。
(2)生物研發投入落后于發達國家。在國際重視生物安全并向大生物安全觀——健康安全觀轉變的趨勢下,全球各國都積極關注生物安全領域的研究。如美國,直到2019年底,美國管理機構共資助與生物安全相關的項目9893項,資助經費高達1592億美元[2]。法國科研署共資助生物安全相關項目31項,累計經費約1060萬歐元。日本自 2015年起,文部科學省撥付特別領域研究補助金資助開展“全球傳染病等生物威脅的新沖突領域研究”項目。
相對于發達國家的研發,我國雖然也對生物安全有關項目進行了立項,但項目數少,資助資金也比較少,以國家社科基金“公共衛生”為主題進行搜索,從1994年到2019年25年間,只有802項項目立項。
(3)生物安全防御聯動機制不健全。在這次舉國“戰役”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國家CDC(疾控中心)、軍隊CDC和地方CDC以及各級床染病醫院,仍存在條塊分割嚴重、隸屬關系復雜、部門機構各自為政、協調機制不暢等問題,面對疫情,還存在短板、漏洞和弱項,遠沒達到對疾病的“可溯、可診、可防、可治、可控方面合力攻關”,不能真正實現資源的有效整合、信息共享和體系的健全完備。
二、對策和建議
1.加強頂層設計,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領域
生物威脅已經從偶發風險向現實持久威脅轉變,威脅來源從單一向多樣化轉變,威脅邊界從局限于少數區域向多區域甚至全球化轉變,突發生物事件影響范圍已經從民眾健康拓展為影響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因此,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們應從戰略上重視生物安全體系的建設。
2.推動科技創新,加強科研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科技不僅是打贏當前這場戰爭“最有力的武器”,而且還是應對重大風險挑戰的“國之重器”。他在3月2日的考察中說,“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領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國之重器。”為了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必須倚仗“國之重器”。我們要完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要健全國家重大疫情監控網絡,要研究建立疫情蔓延進入緊急狀態后的科研攻關等方面指揮、行動、保障體系,平時準備好應急行動指南,緊急情況下迅速啟動。
3.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以“法”的強有力手段恢復秩序、安定人心,處理常規和特殊變通亦大體有章可循,在非常時期、應急情況下從容鎮定,才能戰勝各種困難。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加快生物安全立法工作,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從法律制度上筑牢生物安全的“堅實底線”。
4.健全生物安全的聯動機制
雖然維持一定力度的生物安全公共投入,但在政策協調、組織人事、物資供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生物安全防御體系存在短板,難于有效抵御網絡生物安全等新型生物威脅。因而,在防控突發事件時,應建立央地、軍地聯動機制,解決應急措施短板等瓶頸問題,讓生物安全治理體系真正起到可防、可治的作用。
注釋:
[1]徐緩.美國公共衛生應急法制化建設新動向及啟示.中國應急管理,2009年第3期第50-54頁
[2]李愛花、楊仁科、唐小利.美英法生物安全領域基金資助布局.中華醫學圖書情報雜志,2019年第28卷第1期
作者簡介:
劉龍(1964--)男,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生物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