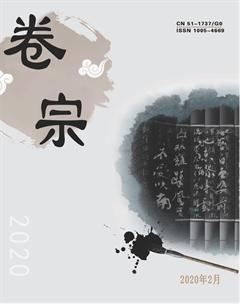夷·城父考
盧鑫
摘 要:《左傳》中“夷”、“城父”二詞混用,“城父”起源久有分歧,眾說紛紜。本文主要論述亳州城父,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夷與城父是否為同一概念;二、“城父”時代起源,三、“城父”地名考證。筆者通過梳理相關概念,對《左傳》等傳世文獻及前人意見進行考辨,認為夷與城父是兩個不同概念,最初城父為一城池,是夷邑的治所,后取代夷為邑名、縣名;城父時代可分為三個階段“夷有城時代”、“夷城父時代”、“城父邑縣時代”;“城父”一詞應源于公元前533年“遷許于夷”歷史事件,且與葉縣城父有極大關聯。
關鍵詞:夷邑;城父;《左傳》
1 夷與城父概念辨析
夷,邑地。夷邑,春秋時期本屬陳國,后為楚地,治所位于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東南。邑,采邑,指古代諸侯分給大夫的封地。夷,作邑地,特指今亳州“夷邑”,最早見于文獻《左傳·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焦,譙縣也。焦、夷并列,此處“夷”,位于亳州市譙城區東南,確定無疑。古代國都、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都以有城垣的都邑為中心。公元前637年楚伐陳,以攻取陳國焦、夷二邑且占領其都邑城池而告終。文中“城頓而還”,說明夷地有城,且城為夷治所都邑。城,指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高墻,泛指城池。《墨子·七患》:“城者,可以自守也”。除此之外,焦、夷并列的記載還有:襄公元年(前572年):“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
《春秋·昭公九年》(前533年):“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只稱夷,不稱城父。說明此時“城父”一詞尚未出現,或僅作城名而非邑名。
城父,筆者認為最初僅指城名,指夷邑治所“城父”城,后取代夷成為邑縣名。城父一詞,最早出現在《左傳·昭公九年》,且“夷”與“城父”同時出現。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于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于許。”
文中“遷許于夷,實城父”與《漢書·晁錯傳》“徙民實邊”記載,都反映了古代徙民戍邊的統治政策,可知“實”的意思是“使加強,充實”。有人把“實城父”中“實”字在理解為“實際上,事實上”,用于解釋說明“夷就是城父,在昭公九年之前夷已經改名為城父”,此種觀點忽視了當時的社會背景,未免牽強,也就此產生了“夷與城父同概念混用”和“時代先后”的問題。
昭公三十年(前512年):“吳子使徐人執掩余……取于城父與胡田以與之……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與“城父”又同出現。哀公六年(前489年):“吳伐陳……乃救陳,師于城父。”“城父”又單獨出現。
筆者認為,“夷”與“城父”同時出現或交替出現,并非混用,實因此時城父是夷邑的治所,不存在一定時期內夷與城父同概念混用和時代先后的問題。城父與夷的關系,不是“廢夷改稱城父”單純地更換地名,而是城父由治所城名逐漸取代“夷”成為邑縣名的歷史演變過程。
2 城父時代起源
城父起源的時代,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夷有城時代”,夷邑有治所城,城名不詳。第二階段為“夷城父時代”,城父系城名,作為夷邑治所。第三階段為“城父邑縣時代”,城父取代夷,成為邑、縣名,并沿用后世。
公元前637年楚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自此夷為楚國轄地,夷邑有城池,城名不詳。公元前572年“晉師侵楚焦、夷及陳”,是為佐證。“城父”一詞首次明確記載于《左傳·昭公九年》“遷許于夷,實城父”,說明在公元前533年或之前,“城父”一名已經出現,且城已具規模。
昭公三十年(前512年):“吳子使徐人執掩余……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古代筑城,有不同稱謂。據《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可知,城池的營建有不同稱謂,建造邑叫做“筑”,建造都叫做“城”。可知昭公三十年“遂城夷”,城作動詞,為營建之意。且“遂城夷”是指在夷地建城池,并非一定指城父城。為徐子營建城池,用“城”字表示完全說的通。
“夷”在《左傳》中最后一次出現是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哀公六年(前489年):“吳伐陳……乃救陳,師于城父。”其后相關典籍均用稱“城父”,不稱“夷”。
綜上可知,第一階段“夷有城時代”的下限不晚于公元前637年。第二階段“夷城父時代”至少跨半個世紀,其上限不晚于公元前533年,下限應不晚于公元前489年。第三階段“城父邑縣時代”自公元前五世紀末至漢唐后世。
3 城父地名考
城父地名起源,一說“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杜注曰:“此時改城父為夷”。一說楚平王“大城城父”,改夷為城父。昭公十九年(前523年):“楚子為舟師以伐濮……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故太子建居于城父。”。前者杜預認為城父為當時舊名,夷為新名。只要了解春秋時陳、楚的歷史,便知道此說顛倒了夷與城父出現的先后順序。后者楚平王“大城城父”,且不論此處城父是否指亳州城父,單就“大城城父”發生在“遷許于夷,實城父”十年之后,在時間順序上就不合邏輯。那么城父緣何稱“城父”呢?筆者以“遷許于夷,實城父”這一歷史事件為主線,探究許國遷徙前后相關地理地名的關聯性,追溯城父地名的由來。
“遷許于夷”是“徙民實邊”政策的產物,源于春秋時期楚武王(公元前741年—公元前690年在位)設縣而治的管理思想。莊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斗緡尹之。”滅權國設權縣是思想付諸實踐的開始。楚武王創造的這一套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和國家機器,為楚國成為春秋時期數百年不衰的強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自此,開疆設縣成為楚國成例,每滅一國,便將該國異地遷移安置,嚴加監管,對該國的故地通常設縣管理。這是“遷許于夷”的社會和政治背景。
公元前576年,許靈公被遷到了“葉”(今河南葉縣西南)。公元前534年陳國第二次滅國,次年,許國再次被遷到陳地夷邑。關于“遷許于夷”,參照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上述昭公九年“楚公子……遷方城外人于許”這段話的意思是,楚國公子棄疾把許國從葉(今河南葉縣)東遷到夷邑,充實邊城“城父”,再把州來、淮河以北的土田劃歸許國。伍舉把田地授給許國主。鄭然丹把城父城百姓西遷到陳地,再把夷地濮水(今沙水)以西的田地補給陳。把方城(楚國北界邊城,鄰近葉地)邊界以外的人遷到原許國故地。
春秋同名異地者多,城父亦有二。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根據史事并配合州郡沿革,對亳州城父和葉縣城父(又稱襄城城父)的歷代政區歸屬作了疏理。城父城(亳州東南),春秋時本屬陳邑。父城(葉縣東北)春秋時楚邑,亦曰城父。漢初鑒于二地同名,把后者改為“父城縣”,以避免混淆。
可知,歷史上兩個城父,即亳州城父和葉縣城父,均與許國有關,或者說“遷許于夷”前后,二城父都曾是許國屬地,想必這不是巧合,而是存在內在聯系。
筆者認為,“城父”源于“徙民實邊”政策,因“遷許于夷”而改都邑治所名為“城父”。公元前533年遷許于夷時,改夷都邑城名為“城父”,作為許國都。公元前529年,楚平王繼位,復封陳國,遷許國回葉。可以說,在陳第二次滅國的五年時間里,許國定都于亳州城父。城父人隨許國遷回葉后,因懷念城父城,故稱聚居地為城父,是為葉縣城父。遷許回葉后,夷地仍稱夷,治所城池沿用“城父”一名。自公元前五世紀末,多用城父指代夷,“城父”逐為邑、縣名。
4 結語
本文主要圍繞三方面內容展開考證,“夷與城父是否為同一概念”、“城父時代起源”、“城父地名考證”,并得出結論。
一是城父是夷邑的治所,一定時期內兩者并非同概念,不存在文獻混用和時代先后的問題。城父與夷的關系,不是直接單純地更換地名,而是城父由城池名逐漸取代夷成為邑縣名的歷史發展演變過程。
二是城父起源的時代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夷有城時代”,夷邑有治所城,城名不詳。第二階段為“夷城父時代”,城父系城名,作為夷邑治所。其上限不晚于公元前533年,下限應不晚于公元前489年。第三階段為“城父邑縣時代”,城父取代夷,成為邑縣名。
三是“城父”一名源于“徙民實邊”政策,因“遷許于夷”而改都邑治所名為“城父”。歷史上兩個城父,即亳州城父和葉縣城父,均與許國有關,且兩者存在承襲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