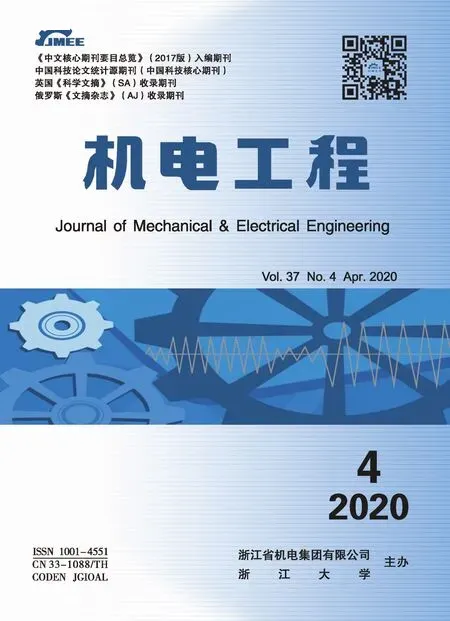驅動橋錐齒輪錯位量的有限元建模和分析*
李旭偉,田 程,張林濤
(中國汽車技術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天津 300300)
0 引 言
驅動橋是汽車的重要動力總成,而錐齒輪副又是驅動橋中最主要的零件,其性能的優劣將直接影響整個傳動系統的性能,因此,對錐齒輪副的設計和分析具有重要的工程意義。
在實際工作時,錐齒輪副的載荷作用會導致支撐齒輪的軸系發生變形,使得齒輪副的相對位置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可通過錯位量來表示。錯位量對錐齒輪的嚙合性能有著重要的影響[1],是錐齒輪設計和分析時的重要參數。工程上獲得錯位量的常用方法是通過試驗來進行測量[2],這種方法雖然接近于實際情況,但需要制造樣件,大大增加了設計成本,加長了設計周期;此外,受到傳動系統結構和實際測量條件的限制,要準確測得計算錯位量所需的齒輪的位移和轉角非常困難。若采用仿真計算方法獲得錐齒輪的錯位量,則需要建立整個驅動橋傳動系統的分析模型,并計算系統在載荷作用下的變形。其中,軸承的剛度和位置對齒輪錯位量影響較大[3],是計算過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其難點之一是在計算支撐軸系的系統變形時,如何考慮軸承剛度在各方向上的耦合性和非線性的特點。
筆者采用文獻中提出的一種多支撐軸系有限元建模方法,通過建立一種特殊的軸承單元來解決軸承的模擬[4]。此外,由于驅動橋結構復雜、零件眾多,模擬計算的另一個難點是如何對驅動橋內部結構進行合理的簡化和建模,并考慮外部橋殼和主減速器殼體等對系統變形的影響。目前,尚未見學者針對驅動橋錐齒輪錯位量的仿真計算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針對這一問題,本文提出一種驅動橋有限元模型建模方法,在考慮軸承剛度耦合性和非線性的情況下,建立包括傳動軸、軸承、錐齒輪、差速器等部件的驅動橋傳動系統的完整有限元模型,并在此基礎上考慮殼體剛度的影響;通過求解該模型的系統變形,得到錐齒輪設計時所需的錯位量;最后通過試驗對該建模方法進行驗證。
1 傳動軸與軸承模型的建立
主減速器是驅動橋的主要組成部件之一,其主要零件包括軸、軸承和齒輪。其中,主、從動齒輪均采用跨式支撐方式,其傳動軸由多個軸承進行支撐。由于在本文的建模分析中,筆者更關心的是傳動系統內各個位置(尤其是齒輪處)的變形情況,而非某個零部件局部的受力及應力分布,因此,在建模時,可在保證其宏觀剛度盡量真實的情況下,對各零件的有限元模型進行適當的簡化,以提高系統模型的計算效率。
多軸承支撐的軸系模型是傳動系統建模的基礎。由于軸承剛度在各個方向上存在耦合性和非線性特點,在不確定其變形的情況下,無法通過簡單的定剛度彈簧進行精確的模擬;而采用實體單元模型,又會增加龐大的計算量[5-6]。
筆者采用文獻[4]中提出的一種考慮軸承剛度耦合性和非線性的軸承單元來模擬軸承,可有效地模擬軸承剛度的特點,并且計算規模小,易于編程實現。
軸承單元可以看作是一個具有5個方向剛度的非線性彈簧,具有2個節點,分別表示軸承的內外圈。軸承單元的剛度矩陣可根據軸承內部載荷與位移之間的關系推導得到;在HARRIS[7]和LIM[8]等人的基礎上,筆者進一步考慮了滾子錐角的影響。
這里以滾子軸承為例,給出軸承各方向的載荷和位移關系表達式,即:
(1)
式中:Fx,Fy,Fz—軸承在各個軸向的受力;Mx,My,Mz—軸承在各個軸向所受的力矩;Kn—綜合剛度系數;Z—軸承滾子數;α—滾子接觸角;Ψj—第j個滾子的方位角;γp—滾子節圓半徑;ns—切片數;tk—第k個切片的軸向坐標;δj,k—第j個滾子的第k個切片的法向位移量。
軸承局部坐標系如圖1所示。

圖1 軸承局部坐標系
滾子切片示意圖如圖2所示。

圖2 滾子切片示意圖
軸承單元兩個節點之間的剛度矩陣,可通過對式(1)求偏導,或采用差分法計算得到。
為了考慮滾子修緣的影響,筆者沿滾子軸線方向將滾子劃分為多個等厚度的切片。單個滾子中,每個切片的法向位移量的計算公式如下:

(2)
式中:δx,δy,δz—軸承內外圈之間沿3個坐標軸方向的位移;θx,θy—繞x軸和y軸的轉角;sα—軸承的初始軸向預緊量;β—滾子錐角;P(tk)—滾子修緣量。
對于圓柱滾子軸承,可看作是圓錐滾子軸承的特例,取式(2)中的接觸角α和滾子錐角β為0,即可得到圓柱滾子軸承的載荷位移關系式。由于滾子與滾道間沒有拉力,法向位移量小于0時取0。
對于傳動軸,可采用考慮剪切變形的歐拉梁單元來模擬,將傳動軸根據不同的截面尺寸分成若干軸段,分別建立梁單元,并賦予不同的截面屬性;并在軸上安裝軸承的位置設置節點,與軸承單元對應節點相連,將軸承單元的剛度矩陣組集到模擬軸的梁單元剛度矩陣中,即可得到單根軸系統的剛度矩陣。
軸承單元的另一個節點與殼體模型或其他與之裝配的軸相連,殼體模型的處理在下文介紹。
2 錐齒輪模型的建立
在建立了傳動軸與軸承的有限元模型后,進一步需要建立齒輪模型,用于連接各個傳動軸,并傳遞載荷。由于驅動橋主減速器中的弧齒錐齒輪或準雙曲面齒輪采用了局部共軛理論,在傳動時可看作是點接觸。
錐齒輪簡化模型如圖3所示。

圖3 錐齒輪簡化模型P,P′—齒輪副節點處主、從動齒輪的嚙合點;G—主動齒輪中心點;W—從動齒輪中心點;M,N—齒輪副的軸交錯點;O—齒輪坐標系原點;x,y,z—齒輪坐標系坐標軸;ε,η—主、從動齒輪的偏置角
圖3中,忽略傳動過程中嚙合點位置的變化的影響,認為主從動齒輪始終在齒輪副的節點處嚙合,在齒輪副節點處過嚙合點P和P′分別作與兩根傳動軸軸線垂直的交線,交點即為主從動齒輪在軸線上的中點。
筆者在嚙合點與齒輪中點(G和W)之間分別建立剛性梁單元,用于模擬兩個齒輪,其中,GP為主動輪,WP′為從動輪。兩嚙合點P和P′之間通過等效嚙合剛度矩陣進行耦合,其嚙合力的方向向量如下:
(3)
式中:F—嚙合力;Fxi,Fyi,Fzi—嚙合力在空間坐標系下的分量。
由式(3)可知,錐齒輪的等效嚙合剛度矩陣只包含3個平動方向的分量,嚙合力可通過給定的錐齒輪幾何參數及傳遞的轉矩計算得到。
根據嚙合力方向向量公式,可得到等效嚙合剛度矩陣表達式如下:
(4)
式中:km—錐齒輪接觸的等效嚙合剛度。
要建立主減速器部分的有限元模型,只要將式(4)加入錐齒輪模型即可,在該模型下即可對錐齒輪錯位量進行定義,并給出相應的計算方法。
錐齒輪錯位量是用來表示發生變形后主從動齒輪之間的相對位移,這一位移是定義在錐齒輪副的軸交錯點M和N之間,而非齒輪的中點G和W。
錐齒輪錯位量定義如圖4所示。

圖4 錐齒輪錯位量定義ΔP—齒輪副沿小輪軸向的相對位移;ΔW—沿大輪軸向的相對位移;ΔE—沿偏置距方向的相對位移;Δ∑—沿軸交角方向的相對角位移
圖4中,要對錐齒輪的錯位量進行分析,需要使用4個位移量及對應的方向來表示。
由于系統模型中并沒有建立M和N這兩個點,錯位量需要通過G和W點的位移計算得到。因此,在圖3所示的全局坐標系中,主動輪和從動輪的錯位量可以表示為:
(5)
(6)

將主從動齒輪各自的錯位量相加,即可得到齒輪副的錯位量,如下所示:
(7)
在實際結構中,由于不存在圖3中所示的M和N點,通過試驗方式獲得錯位量時,除了需要測量齒輪在各方向的位移外,還需要測量其轉角,才可以根據式(5~7)計算出錯位量,這也大大增加了試驗測量的難度。
3 差速器模型的建立
差速器是驅動橋中另一個重要部件,它一般與主減速器錐齒輪的從動輪固聯,將從動輪上的轉矩分配并傳遞到兩個半軸。本文不討論兩側車輪存在差速的情況,但是由于差速器結構的存在會影響傳動系統的整體剛度,且不同的差速器殼體模型對齒輪錯位量影響也不同[9],在驅動橋傳動系統模型中需要對其進行建模。
對于差速器殼體有兩種建模方法:(1)先建立其實體有限元模型,然后采用Guyan縮減法提取其剛度(具體處理參見第4節內容),該方法適用于殼體結構復雜且可以獲得其幾何模型的情況;(2)將差速器殼體簡化成一個對稱的回轉體,采用模擬傳動軸的方式用梁單元進行建模,該方法適用于殼體結構相對簡單,或缺少其精確幾何模型的情況。
差速器內部主要包括行星齒輪軸(十字軸)、行星輪、半軸齒輪等部件。由于不考慮差速情況,齒輪只傳遞載荷,不發生轉動,可將行星輪和十字軸看作一個整體,將半軸齒輪與半軸看作一個整體,分別用梁單元進行模擬,齒輪嚙合的處理同第2節所述方法。
差速器內部零件建模如圖5所示。

圖5 差速器內部零件建模1—半軸齒輪;2—行星輪;3—剛性梁;4—梁單元;5—十字軸;6—半軸
圖5中,將十字軸簡化成一個十字型的空間梁,在實際結構中,十字軸4根銷軸的外端與差速器殼體上對應的銷孔相連。當采用梁單元模擬差速器殼體時,模型在銷孔位置只在軸線上有一個節點,無法直接與十字軸4根梁上的節點相連。因此,需要在模擬差殼的梁單元上分別建立4個空間剛性梁單元,梁端部的4個節點分別位于銷孔的實際位置;將十字軸模型端部對應節點分別與這4個節點耦合,來實現十字軸與差殼的連接。這些剛性梁單元并不對應真實結構,僅作為一種連接關系。
由此,可通過建立起差速器部分的有限元模型,將其與前面建立主減速器部分的模型組合,再采用同樣的多支撐軸系建模方法,建立輪邊部分剩余結構的模型,即可建立起包含全部主要部件的驅動橋傳動系統的有限元分析模型。
4 殼體剛度的影響及系統模型求解
除了內部的傳動系統外,驅動橋外部還包裹有橋殼和主減速器殼,這些殼體起到了重要的承載和支撐的作用。傳動系統所受到的載荷會通過軸承傳遞到殼體上,使殼體發生變形;而殼體的變形也會影響到相應軸承連接處的位移,進而影響到傳動系統。因此,在驅動橋傳動系統建模時,有必要考慮殼體剛度的影響。
由于橋殼和主減速器殼的結構一般都比較復雜,為了準確獲得其剛度,有必要采用實體單元建立其有限元模型。在進行驅動橋齒輪嚙合分析過程中,有學者對驅動橋以及主減殼體進行了實體建模[10],但是若將該模型直接與之前建立的傳動系統模型相連,會大大增加計算規模。為此,在對驅動橋進行模態綜合動力學建模分析時,又有學者采用對有限元模型進行縮維的方法,生成關鍵節點之間的質量和剛度矩陣,用于系統模型計算,大大縮短了系統的仿真計算周期[11]。
在計算錐齒輪錯位量時,由于并不需要關心殼體上的應力分布,只關注各軸承支撐處之間的剛度,筆者也采用Guyan縮減法,對殼體有限元模型的剛度進行縮減,其基本公式如下:
(8)
式中:Kh—殼體有限元模型整體剛度矩陣;k—整體剛度矩陣中的分塊剛度矩陣;下標o—凝聚節點所對應的自由度;下標i—殼體有限元模型內部節點所對應的自由度;kh—縮減后的殼體剛度矩陣。
根據式(8),采用Guyan縮減法的具體方法是在殼體有限元模型中,在各軸承中心所對應的位置設置凝聚節點,并將其與殼體上各軸承安裝位置所對應的節點剛性連接,以凝聚節點為外部節點,將殼體的剛度矩陣縮減成各凝聚節點之間的剛度矩陣。
將剛度縮減后的殼體有限元模型的凝聚節點與傳動系統模型中軸承單元的對應節點相連,即可將殼體的縮減剛度矩陣組集到傳動系統模型的總體剛度矩陣中,這樣就可在不增加傳動系統模型維度的情況下,準確地考慮殼體剛度的影響。
除了殼體外,對于傳動系統中一些結構復雜的異型軸,如差速器殼體、輪轂和制動鼓等,也可以采用類似的方法處理,以獲得更為準確的剛度。其中,采用該方法模擬差速器殼體時,除在與軸承連接處設置凝聚節點外,還需要在十字軸的銷孔處建立凝聚節點,用于和十字軸模型相連。
至此,筆者建立起了驅動橋傳動系統完整的有限元模型。該系統的剛度方程如下:
P=Kδ
(9)
式中:K—系統剛度矩陣;P—外載荷向量;δ—節點位移向量。
該模型考慮了影響系統變形的各主要部件及影響因素。在主錐主動輪輸入端節點施加輸入轉矩,約束兩個輪邊處輸出端節點的軸向轉動自由度,采用NR迭代法,即可對上述方程進行求解,得到輸入載荷下軸系各處的變形及各零件上的載荷;并可以根據所得結果,計算得到主減速器錐齒輪的錯位量。
5 試驗及結果分析
采用試驗方法測量錐齒輪錯位量時,一般參照法規QC/T533—1999中5.3節驅動橋支撐剛性試驗方法,但該法規僅涉及對主從動齒輪位移的測量,并未測量齒輪的轉角。實際試驗時,受驅動橋結構的限制,齒輪中心繞其徑向方向的轉角難以測量,因此,這里僅以齒輪中心的位移測量結果來對上述建模方法進行驗證。
筆者以某型號驅動橋為研究對象,根據實際驅動橋結構布置測點,測量主減速器主被動錐齒輪各自沿3個垂直方向上的位移。
支撐剛性試驗臺架如圖6所示。

圖6 支撐剛性試驗臺架1—驅動橋右輸出端;2—齒輪位移測點;3—千分表支架;4—驅動橋左輸出端;5—驅動橋輸入端
試驗中,筆者采用電子千分表來測量變形。測點位置盡量靠近齒輪中心,并借助光電觸發器保證各測點同時采樣。試驗載荷為額定載荷,輸出扭矩為30 000 Nm。最終各測點試驗數據,均通過多次采樣后,再取平均值來獲得。
由于在現有的商用有限元軟件中,無法建立本文所采用的考慮剛度耦合性和非線性的軸承單元,筆者依據上述方法在Matlab環境下進行編程,根據試驗所用驅動橋的參數,建立了其完整的傳動系統有限元模型,在試驗測點對應位置建立了節點以輸出測點處的位移結果。
在商用有限元軟件中,筆者分別建立了驅動橋橋殼和主減速器殼的實體有限元模型,并依據試驗中驅動橋橋殼和主減速器殼體上測量孔的開孔情況,對模型進行了修正;此外,為了獲得更準確的結果,也建立了輪轂、制動鼓和差速器殼體的實體有限元模型。同時,在實體有限元模型中軸承等部件的安裝位置建立了凝聚節點,分別計算得到殼體等部件的縮減剛度矩陣,并加入到傳動系統模型中。
在所建立的驅動橋模型中,筆者施加與試驗中相同的載荷,進行迭代計算。該模型計算速度快,在目前常見配置的電腦下,計算時間在10 s以內。
測點位移計算與試驗結果對比如表1所示。

表1 測點位移計算與試驗結果對比
從表1可以看出,計算結果與實測結果的位移趨勢是相同的,各方向位移大小的相對關系也是吻合的;其次,主動輪的計算結果與試驗的吻合程度要好于被動輪,誤差的絕對值在0.006 mm以內;被動輪向位移誤差較小,x向和z向誤差相對較大。
造成誤差的主要原因可能是:(1)受測點位置表面粗糙度、油污或其他雜質、以及測量框架變形等影響,造成測量值本身存在一定誤差;(2)試驗中的驅動橋結構與所建立的模型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別,除安裝誤差等難以確定的因素外,為了方便建模對于螺栓、花鍵等一些裝配關系也作了簡化,處理為固聯。
總體上來說,仿真計算的結果與試驗吻合較好,驗證了該建模方法的正確性,其計算結果的精度可以滿足工程應用的需要。
錐齒輪錯位量計算值如表2所示。

表2 錐齒輪錯位量計算值
表2中,由該模型的系統變形結果,依據式(5~7)計算得到了錐齒輪的錯位量,該結果可直接作為錐齒輪設計軟件(如格里森公司的CAGE軟件)的輸入參數,用于進行齒輪的加載接觸分析和設計。
6 結束語
為了解決現有驅動橋錐齒輪錯位量難以獲得這一問題,筆者提出了一種驅動橋有限元建模方法,通過計算系統變形,得到了錐齒輪的錯位量。該研究的主要結論及說明如下:
(1)該驅動橋傳動系統有限元模型包含了傳動軸、軸承、錐齒輪和差速器等主要部件,并考慮了軸承剛度耦合性和非線性的特點,以及殼體剛度的影響;
(2)經過與驅動橋支撐剛性試驗結果的對比,該模型計算的齒輪位移與試驗結果吻合較好,驗證了該方法的正確性,并得到了可用于錐齒輪設計所需的錯位量結果;
(3)該方法易于編程實現、計算效率高、結果可靠,為錐齒輪錯位量的計算提供了一種行之有效的途徑,對驅動橋傳動系統其他部件的設計和分析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下一階段,筆者將進一步考慮溫度變化對齒輪錯位量的影響,使用仿真方法計算傳動系統實際工作過程中,由于升溫帶來的錯位量變化,為系統的優化改進提供技術支持。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蘇進展,方宗德.弧齒錐齒輪印痕穩定性優化設計與試驗[J].航空動力學報,2012,27(11):2622-2628.
[2] QC-T 533-1999.汽車驅動橋臺架試驗方法[S].北京:中國標準出版社,1999.
[3] 倪小波.后橋主減速器齒輪錯位量影響因素研究[J].汽車科技,2016(3):13-17.
[4] 田 程.考慮軸承剛度耦合性和非線性的多支撐軸系有限元分析方法[J].機械工程學報,2015,50(17):90-95.
[5] 劉顯軍.多支承軸系軸承受力與剛度的有限元迭代計算方法[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2010,44(11):41-45.
[6] DEMIRHAN N, KANBER B. Stress and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s on cylindrical roller bearing rings using FEM[J]. Mechanics Based Design of Structures and Machines,2008,36(1):86-102.
[7] HARRIS T A, KOTZALAS M N.滾動軸承分析(原書第五版)第2卷軸承技術的高等概念[M].羅繼偉,李濟順,楊咸啟,等,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0.
[8] LIM T C, SINGH R. Vibration transmission through rolling element bearings, part I: bearing stiffness formulation[J].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1990,139(2):179-199.
[9] 晏 敏,李文強,劉海云.不同差速器殼體模型對主減速齒輪嚙合錯位量的影響[J].江西化工,2018,34(6):160-163.
[10] 劉 程,史文庫,何 偉.基于整體驅動橋模型的準雙曲面齒輪嚙合分析[J].汽車工程,2016,38(9):1153-1157.
[11] 周 馳,丁煒琦,桂良進.汽車驅動橋系統模態綜合動力學建模分析[J].振動與沖擊,2017,36(9):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