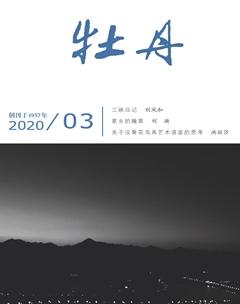劉玉棟鄉土小說研究綜述
張露
劉玉棟作為“70后”代表作家之一,新世紀以來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眾多學者對劉玉棟小說進行了不同層面的研究和分析。本文主要從整體的宏觀把握和單部作品的微觀分析來對劉玉棟鄉土小說的研究成果進行歸納、梳理,總結既有研究中的得與失,以拓展劉玉棟鄉土小說研究的新局面。
一、劉玉棟鄉土小說創作的整體研究
思想內容與主題的挖掘、審美風格的形成、敘事藝術的偏好等因素都是整體研究的重要內容。
(一)思想內容與創作主題
對劉玉棟鄉土小說內容與主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對鄉村道德的關注、對現代化進程的思考以及對城鄉關系的探討方面。
劉玉棟對土地、現實和人生的道德化審視,賦予了小說道德關懷和倫理關懷的力量,使小說具有歷史批判和現實批判的意味。吳義勤在《“道德化”的鄉土世界——劉玉棟小說論》中提出,“鄉土的道德化”是劉玉棟小說的價值支撐,也是他的敘事策略。韓存遠、韓德信在《現代化·現代性·鄉土文學——以劉玉棟作品為例》中,從現代性的角度分析了劉玉棟小說創作中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各種社會問題的思考以及對普通人的生存和精神世界的關注。
隨著城市化進程地不斷加快,城鄉關系呈現出既緊張又聯結的狀態。有評論者從城鄉關系入手,解讀劉玉棟的小說創作。劉瑩、黃發有的《鄉村與都市的雙向凝眸——劉玉棟小說論》從土地的溫情之殤、浮萍的虛妄之嘆、此地與彼地間的游移三個方面分析了劉玉棟鄉土與都市題材的小說,指出無論是面對鄉村還是都市,劉玉棟的文本中始終貫穿一種矛盾的情緒,土地危機重重,都市又冰冷寂寞,無法尋覓到心靈的安置之處。
(二)審美風格與敘事藝術
溫暖詩意與痛苦哀傷是劉玉棟小說特有的審美風格。洪治綱在《苦難背后的溫暖——劉玉棟小說論》中,認為劉玉棟的小說充滿溫暖的情感之力,以一種溫情式的話語基調、樸實平和地敘述著社會底層人群的生存故事。施戰軍在《體恤與知情之間的傷懷——劉玉棟小說讀想》中,提出劉玉棟的小說里奇跡般地融注了鮮活的感性與溫柔的情懷。還有的評論家積極嘗試運用敘事學理論解讀劉玉棟小說的敘事藝術。汪政、曉華在《暗夜的溫暖——劉玉棟中短篇小說閱讀札記》一文中,分析了劉玉棟中短篇的作品,提出其在敘事上選定一個視角或敘事人,以時間或人物為單元,全方位地展現出了生活的場景。
總體而言,上述文章對于整體理解和把握劉玉棟小說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值得注意的是,評論者們力圖全面總結劉玉棟鄉土小說時,往往會偏離“整體”的特點,而更傾向于某一特定主題的分析。究其原因,一是因為整體研究相較于其他研究,涵蓋范圍廣容量大;二是因為劉玉棟的創作生涯仍在繼續,學者也難以對劉玉棟的所有創作給出一個定性的評價。
二、劉玉棟鄉土小說的單篇評論
“70后”作家們普遍是以中短篇小說見長,在長篇小說創作方面還是較為缺失的。劉玉棟的《年日如草》在2010年出版后,對于劉玉棟自身以及整個“70后”作家群體而言,都具有突破性的意義。因此,學術界對劉玉棟單篇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長篇小說《年日如草》。張麗軍、房偉等的《一個農民·一座城市·一部心靈成長史——劉玉棟長篇新作<年日如草>研討》采用學術對話的形式,全方位地探討了這部作品的審美閱讀體驗、人物形象、語言、結構與敘事空間等。
劉傳霞、石萬鵬的《鄉村逃亡者的城市敘事——論劉玉棟的長篇小說<年日如草>》將主人公曹大屯放置在成長小說視域與“鄉下人進城”文學譜系中進行考察,20年間曹大屯已經從一個懵懂鄉村少年變身為適應城市生活的中年市民。在與祥子、五龍、孫少平的對比中,評論者認為曹大屯以他的善良、誠摯參與并維持了城市的良序公德,為“鄉下人進城”文學譜系提供了嶄新形象。郭念文的《行走在理想與現實的邊緣——評劉玉棟<年日如草>的人物塑造》剖析了曹大屯、曹父、曹奶奶這三個具有不同時代特征的典型人物,揭示出“農村人”在融入城市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人格上的懦弱、文化上的迷茫和精神上的妥協。
周文、田冰的《金與草的城鄉辯證法——<年日如草>符號矩陣解讀》運用格雷馬斯的符號矩陣理論,從城鄉敘事的矩陣結構、城鄉的人為對立、城鄉的商業融合三個方面對小說進行文本分析,指出了金錢與道德、城市與鄉村這四項之間橫向的矛盾與對立關系,闡明城市化應該更加注重文化道德觀念的重建。王海濤的《論<年日如草>的敘事倫理》通過審視城鄉兩種文化的差異,分析城市化進程中進城農民的精神境遇,揭示城市身份只是無用的外殼,現實的生存壓力和內心困惑是進城農民面臨的普遍困境,揮之不去的漂泊感,是進城農民的典型心理。
這些單篇評論文章從人物形象、敘事結構、城鄉差異等多方面對《年日如草》進行了解讀與評析,雖然角度各異,但都作出了較為透徹的闡釋。
三、劉玉棟鄉土小說研究的問題及發展空間
從對上述文章的梳理中,可以發現劉玉棟鄉土小說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但同時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其一,研究的角度局限于主題、敘事風格等方面,而帶有突破性的觀點匱乏。其二,學術界對劉玉棟單篇作品的評論主要針對長篇小說《年日如草》,占據劉玉棟小說創作半壁江山的中短篇鄉土小說卻很少有人關注。其三,關于作家作品比較研究方面,研究者缺少將劉玉棟鄉土小說創作與同為“70”后其他作家創作的鄉土小說的橫向比較,更缺少貫穿現當代作家作品的縱向比較研究。
既有的局限則預示著未來的發展空間。在今后劉玉棟小說研究中,學界除了要及時地跟進對劉玉棟小說的評論外,還應該在以下幾方面加以努力:第一,尋求新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當今,生態批評成為熱點,可以嘗試用生態批評理論分析劉玉棟的小說。第二,加強對中短篇小說的研究。《給馬蘭姑姑押車》《火色馬》《幸福的一天》等都是非常優秀的鄉土小說作品,評論者應當多加以研究。第三,開闊研究視野,將劉玉棟鄉土小說放置在文化視野和現代性視野中進行研究,尋找最合適的劉玉棟坐標點,從而把握其獨特性。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