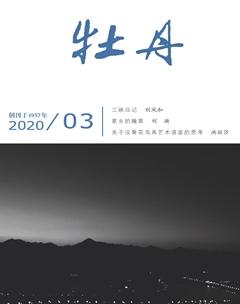金華北山:黃溍詩歌中的文學空間
如今文學地理學正蓬勃興起,婺州(今浙江省金華市)的金華北山作為一個有意味的文學空間,從古至今有無數文人曾暢游其中。本文選取黃溍這一典型,立足于金華北山這一空間,從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上考察黃溍心理情感的變遷。
從時間維度上來說,黃溍不同時期游覽金華北山所表露出的情感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從空間維度上來說,將游覽時間很接近的“金華北山”空間和“扈從上京”空間進行對比,可見空間轉換對其詩風的影響。
查洪德在《元代詩學通論》中指出元人具有隱逸、游歷、雅集、題畫之風。金華北山集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于一身,成為一個有意味的文學空間。婺州文人在其中詩酒雅集、游山玩水,滿目清景訴諸筆端,化為具有審美意味的詩文作品,讀者從中可以領略到不同時期不同文人多樣的心理感受,也可以從山水詩文這一視角窺見婺州文人的獨特風貌。
一、有意味的文學空間:金華北山
學者楊鐮在其《元詩史》中提到,同題集詠是元代一個顯著的文學現象。金華北山進入研究者視野正是從金華北山同題集詠開始的。黃溍寫有《金華北山紀游》八首,分詠靈源、草堂、三洞、鹿田、寶峰、潛岳、山橋、寶石八景。后有吳師道《追和黃晉卿北山紀游八首》、胡助《和黃晉卿北山紀游八首》。但審視比較吳師道《北山游卷跋》和宋濂《題北山紀游卷后》,可知這一現象不是同題集詠可以涵蓋的。
《北山游卷跋》曰:右《北山紀游》詩文一卷,金華葉謹翁審言、烏傷黃溍晉卿、蘭溪吳師道正傳、東陽張樞子長、釋無一之所作也。自至大庚戌距至順癸酉,二十有四年間,凡屢游,五人者雖不必俱,而游必有作。
《題北山紀游卷后》曰: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游》卷示濂,請題識其后。卷間諸詩,皆鄉賢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修撰張公之作,禮部《紀》《游》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為檢其遺稿……侍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于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迨今五十余年。
比較吳師道和宋濂對《北山紀游》卷題跋之異同,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信息。
第一,《北山紀游》由游歷北山活動后編成。根據元代著名文學家柳貫的《草堂琳藏主得往年黃晉卿、吳正傳、張子長北山紀游八詩裝演成卷,要予繼作,因追敘舊游,為次其韻增諸卷軸》,可知《北山紀游》的收集整理者為智者寺草堂的琳和尚。
第二,游歷北山活動的參與人士地域性明顯,皆是婺州人士,也就是宋濂筆下的“鄉賢達”。活動的發起人是宋濂的老師,烏傷(現浙江義烏)人士黃溍。
第三,游歷北山活動持續時間很長。學者歐陽光的《論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傳承現象》和學者徐永明的《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將婺州的作家群分為四代,其中吳師道與黃溍、柳貫同屬于第二代文人,宋濂則屬于第三代文人。宋濂“自庚戌迨今五十余年”句,表明從黃溍至大庚戌年(1310年)首作《北山紀游》詩以來,到宋濂為《北山紀游》作題已是1360年之后的事了。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參與人數也由吳師道跋中所稱的五人,擴展為宋濂題中數人。
如果僅僅將此次游歷當作同題集詠來處理,那么所能涵蓋的僅僅是黃溍《北山紀游》八首,以及相關追和之作,研究視域便隨著研究對象數量的減少而縮小了。何況同題集詠主要指詩,而正如宋濂在《題北山紀游卷后》所指明的那樣,這其中還包括吳師道的《金華北山游記》和《北山后游記》兩篇散文。
與此同時,在這里需要補充的是,本文所說的“金華北山”是一個泛概念,泛指整個金華山。吳師道在《金華北山游記》中按游蹤的順序寫到芙蓉峰、上方境界、三洞、鹿田、第一軒、山橋、赤松山、煉丹山、二皇君祠、小桃源、寶積觀、安期生石室、劉孝標讀書巖等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并且說:“金華為天下名山,環亙數百里,巖洞泉石之勝,顓在山北。”金華北山風景佳處很多,是數百里金華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綿延于婺州境內,橫貫《元史地理志》所載的婺州路一領司、六縣、一州中的大部分地區。
翻檢婺州文人文學作品,黃溍除了《金華北山紀游》八首所詠八景外,還作有《金華山贈同游者三十韻》《送覺上人游金華山》等;吳師道除了追和黃詩外,還有《金華觀分得琴字》《答黃晉卿約游金華三洞不果》《和吳存吾題金華山鹿田寺》等;宋濂還有《登北山上方境界亭》《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婺州第一代文人方鳳也曾寫過長文《金華洞天行紀》。僅僅看這些題目就可以發現,集聚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金華北山(泛指金華山,下皆稱金華北山)在婺州文人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既是游山玩水的好去處,也是文人雅集賦詩唱和的理想場所,其中更蘊含著文人的情感起伏、生命律動。
正如學者朱萬曙在《空間維度的中華文學史研究》中所說:“空間有大有小,大到一個行政區域,中到一處山水景觀,小到一方斗室……注重從‘空間維度開展研究,能夠回歸到更為豐富和立體化的文學史現場,重現更為具體的文學史原貌,甚至能夠促使文學史研究和思想史、心靈史、生活史、情感史更好地銜接,生發出諸多富有文化意味和生命趣味的學術命題,從而使文學史研究更加富有學術張力和學術生氣。”因此金華北山于婺州文人,有同題集詠的成分,但更是同題集詠的擴展與延伸,毋寧說金華北山于婺州文人是一個有意味的文學空間。
二、時間變化中的情感變遷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曰:“作詩之妙,實與景遇,則語意自別”。正如學者廖可斌所說:“文學的基本功能是反映生活、描述心靈,它在展示人類社會生活和思想情感的豐富性、生動性方面,與歷史學和思想史研究相比,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黃溍作為“儒林四杰”之一,以南人身份官至翰林院國史編修,一生至少三次游金華北山,以其為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黃溍有詩題為《予與子長以庚戌之春、癸酉之夏,兩至赤松,今年秋復來,則子長已倦游,而予亦老矣,同游者汪生元明、許生存仁,既又得龍丘余子方俱行,由小桃源登煉丹山,謁二皇君祠,回宿寶積觀,感歲時之代謝,念交朋之離合,輒成短句奉簡子長》,由“庚戌之春、癸酉之夏,兩至赤松”可知黃溍兩次游金華北山的時間。
庚戌年,即1310年,黃溍34歲。這一年正月黃溍客杭,與鄧文原、松瀑真人等交游,作《同儒上人謁黃尊師于龍翔上方修撰鄧公適至輒成小詩用紀盛集》一詩,詩曰:“坐陪三老盡文雄,政爾衣冠不茍同。談笑流傳成故事,畫圖想像見高風。”可謂快意與憂思交織,欣然與惆悵并行。這是南人在交游之樂的同時自然流露出的愁懷意緒,何況是在遺民聚集的南宋古都杭州,又時逢正月寒風。吳師道《和黃晉卿客杭見寄》曰:“一從江客江城去,詩思凄涼酒盞空。天末倚樓孤岫雨,春深閉戶落花風。”此等意味更為明顯。
與此不同的是,在這一年萬物復蘇、百花爭艷的春季,黃溍回到家鄉婺州與友人葉謹翁等游金華北山時所作的《金華山贈同游者三十韻》,詩歌基調明快,筆法上采用賦法。其詩寫三洞,有詩句云:“罅幽穴險徑沮洳,膝行匍匐不得奔。剨觀崖廣架寥泬,雙龍繞霤蟠蜿蜿。”則洞穴空間的狹小、路徑的崎嶇、巖石的怪奇、光線的昏暗、地勢的起伏躍然紙上。而寫不知名狹路則有云:“山翁顧之笑引臂,前牽后接猴與猿。馳坑跨谷攲側過,背汗喘息逾炰燔。”寫過不知名的危險小路,舉步維艱之時得一山翁幫助,最后側身而過、脊背冒汗的情形。不管是游三洞還是過小路,不難體會黃溍在庚戌之春游金華北山時對美景的沉迷。此時對金華北山重在“游”,而癸酉之歲作金華北山詩則更多人生況味。
癸酉年,即1333年,黃溍已57歲。自延祐初年黃溍一振而起中進士以來,歷仕臺州路寧海縣丞、石堰鹽場監運、諸暨州判官。1330年因馬祖常之薦,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林郎。次年夏秋時節得以扈從上都,這是黃溍“浮沉州縣,十又六年”后的頂峰。然而就在晚通朝籍、意氣風發的黃溍從上都還后,他的父親便去世了,“其夏,扈從北都,秋還。及冬十二月望,訃至京,溍即日解索居官,匍匐北歸。”因此,57歲的黃溍不僅處于服喪期間,而且才將顯耀,便要還鄉,加上垂垂老矣還要受顛簸之苦,此時的他心境與24年庚戌之歲大為不同,《癸酉四月,同子長至赤松,子長先去,遂獨宿智者之草堂,已而子長與正傳俱來,同一上人宿鹿田,游三洞,還過山橋,至潛岳謁故中書舍人潘公祠堂,復回智者而別》即作于此時,其詩云:“昔與張公子,翩翩訪赤松。重來逾兩紀,獨宿去孤峰……急景真流電,浮生尚轉蓬。后期觀歲晏,來往意憧憧。”與庚戌詩的明朗相比,這首癸酉詩顯得衰颯得多,沒有了庚戌詩用大量賦筆對在洞里探險的歷程、行路時的細微感受的描寫,探洞不過“探奇洞有龍”五字而已,而更有“一切景語皆情語”之感,這時的詩,反映更多的是身世之感:友人之離合、身體之年邁、世事之無常。
金華北山是一個固定的文學空間,但對于黃溍來說,由于時間流逝而帶來的經歷轉變,促使他在面對同一座金華北山時而產生不同的心理感受。比較他前后期游覽金華北山的詩歌,人們可以清晰感知到他的情感變遷。
三、空間轉換下的詩風差異
以金華北山這單一的空間為研究對象,并考察黃溍相關詩作,可以在縱向上考察詩人的情感變遷。但如果立足于金華北山這一空間,并另外引入“扈從上京”空間,同時分析比較在這兩個迥異空間中的黃溍詩作,會發現空間的轉換也會造成詩人詩風的差異。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這里對空間與詩風關系的研究仍然是建立在雍容和緩、平易正大的時代主導的文壇風氣下的。
元代文學家蘇天爵《題黃文獻公紀行詩后》云:“至順二年,予與晉卿為太史。屬行,上覽山川之形勢,宮闕之壯麗,云煙草木之變化,輒低徊顧念,若有沉思者,余因知其賦矣,既而果得其紀行詩若干篇。”可知,黃溍的上京紀行詩與眾多寫作上京紀行詩的文人一樣,也多有描寫山川的。同時,至順二年(1331年),與黃溍1333年游金華北山僅相差兩年,對比黃溍的一生,其上京紀行詩與1333年游金華北山詩可以視為同一時期在不同空間中的作品,然而詩風卻呈現出一定的差異。
在“扈從上京”這個空間中,黃溍跟著皇家的隊伍,與蘇天爵等百官一起,可以說處于一個“嚴肅”的空間中,其作《上京道中雜詩》十二首就表現出更多的理學色彩。而金華北山既是熟悉的家鄉的山川,與之游覽的又是張樞、吳師道等多年的友人,這時的他處在一個相對閑適的空間,因而其詩作就更多指向自己的內心。兩者相比較來說,顯示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同許多身處這種空間的文人一樣,上京紀行詩作有明顯的頌圣傾向。黃溍的《榆林》寫到長城窟:“崇崇道傍土,云是古長城。……儒臣忝載筆,帝力猗難名。”漢代樂府古題中有《飲馬長城窟行》,《文選》李善注說:“長城,蒙恬所筑也。言征戍之客,至于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從古至今令無數人傷神流淚的長城窟,現在連水都變得甘甜起來。這樣的感受自然是由于大元的疆域廣闊,由殺伐之音轉為牛羊之聲。詩中說道,這應該歸功于人主的圣明,而人主的圣明又是小小儒臣的筆所不能名狀的。而金華北山詩則顯然不存在此類傾向。
二是黃溍處于“扈從上京”這樣嚴肅的空間中,而他又深諳理學,博通經史,因此詩作多呈現出理學意味的思考,蘇天爵就說他的紀行詩“緒密而思清”。例如黃溍的《居庸關》:“連山東北趨,中斷忽如鑿。萬古爭一門,天險不可薄。圣人大無外,善閉非鍵鑰。”由形勢險峻、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的居庸關,提到“閉”與“不閉”的問題,認為圣人應該是“無外的”。而在癸酉年所作的金華北山詩中,則更多的是在記錄游蹤的基礎上,指向自己的內心,與好友的情誼,自己身體的年邁。
學界認為,黃溍的詩學思想是矛盾的。學者陳博涵認為,黃溍的詩學思想有“以史論詩”和“以情論詩”兩面,并且援引查洪德論黃溍文論的觀點,認為矛盾的雙方最后折中于“理”。其主要是對黃溍詩文思想進行直接整合,進而分析,但如果還原到黃溍詩文創作的實際,立足于上京紀行詩和金華北山詩所呈現出來的差異,也可以說是空間的轉換帶來了黃溍對自己身份認識的改變,進而暗合了他的詩學思想。
四、結語
婺州文人與金華北山這個有意味的文學空間密不可分,黃溍可以作為其典型代表。立足于金華北山這一空間,看黃溍庚戌年和癸酉年游覽金華北山之作,可以看出他的心理感受由庚戌年更注重“游”的歡欣向癸酉年歷經人世百態后重“志”的轉變。而選取時間上相近的“扈從上京”和癸酉“金華北山”兩個不同的空間,則可以發現空間的轉換對其詩風的影響。當他在“扈從上京”這一嚴肅的空間中時,詩風具有理學色彩,而在金華北山這一閑適的空間中,作詩更指向自己的內心,詩風則顯得更加自然。
(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蘇省研究生科研創新計劃項目“元代詩詞曲互滲現象研究”(項目編號:KYCX18_203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嚴楚喬(1996—),男,江蘇淮安人,碩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