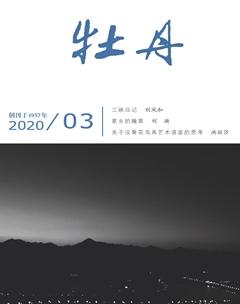韓國小說《殺人者的記憶法》及其電影改編的對比研究
凌悠軒
《殺人者的記憶法》是韓國當代作家金英夏創作的小說作品,2013年出版即成為文學類暢銷書。2017年,元信延執導的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殺人者的記憶法》于韓國上映。兩者在敘述形式上均可視為主人公自傳形式,但在人物塑造、表現手法、情節等方面均存在不同之處。本文將主要從敘事角度與文學角度對兩者進行分析比較。
小說《殺人者的記憶法》主要講述了患上阿爾茨海默癥的連環殺手重新記憶起曾經忘卻的殺人行為的故事。導演元信延通讀了此小說后,下定決心要改編為電影。電影《殺人者的記憶法》刻畫了失去記憶的殺人者金炳秀的形象,金炳秀除了殺人和犯罪意識,還突出表現了強烈的父愛。從敘事角度與文學角度探索小說與電影的區別,人們可以感受到兩者之間不同的魅力。
一、人物塑造
原著小說的特點就在于敘述形式為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連續殺人犯在老年的自白,即主人公自傳式,通過反轉的要素與自我指示性的藝術手法傳達了哲學性的深意與遺忘的恐怖。患上阿爾茨海默癥的主人公如何重組散落的記憶碎片是作品的魅力所在。電影改編與原著的大體框架相同,亦從金炳秀的立場展開敘述,但是為了創作驚悚恐怖片的電影體裁,發生了以閔泰柱(原著為樸柱泰)與恩熙(原著為金恩熙)為主的人物塑造變化。
原著中樸柱泰并不是真正的殺人兇手,只是一名普通警察。根據金炳秀的記憶,自己所做的所有犯罪行為都是樸柱泰所做,樸柱泰只是金炳秀的疑心對象。小說通過金炳秀的視角與扣人心弦的情節最大化反轉,使讀者在醒悟到樸柱泰不是真正的兇手的同時,還感受到了記憶深處被遺忘的恐懼。電影為了渲染恐怖氣氛,將樸柱泰設定為了真正的殺人兇手,通過最后與金炳秀的對決表現出急劇的緊張感。
電影雖然沒有小說通過自述口吻刻畫的主人公形象引人入勝,但是作為殺人者中的一人,閔泰柱的形象塑造是電影的成功之處。除此之外,小說中的恩熙是金炳秀的錯覺、想象中的人物。小說中,由于恩熙是金炳秀妻子的私生女,恩熙早在很久之前就被父親殺害并埋葬在院子里,但是金炳秀早已忘卻了女兒被自己殺害的事實。小說中金炳秀呼喚的金恩熙實際上是來到金炳秀家的社會福利人員,但金炳秀一直錯以為是自己的女兒。所以小說中并沒有像電影一樣刻畫恩熙與金炳秀的家人親近關系,而是將她設定為金炳秀錯覺中守護的對象,最后通過無論是想要守護的女兒還是社會福利人員均被金炳秀殺害的情節,使小說再次被恐怖的氣氛所籠罩。與小說不同,電影中恩熙是金炳秀所養的女兒且是真心想要守護著的對象,從最后去對決的途中還在記憶著自己要守護女兒的錄音內容,可以看出他強烈的父愛。
小說中,金炳秀是70歲手無縛雞之力的老人,而電影為了保持對峙的緊張感,將金炳秀的年齡設定在了50歲,從電影中金炳秀為了與閔泰柱對決而鍛煉身體的情節,可以看出金炳秀也已年老的事實。小說中的安刑警實際上也是金炳秀想象中的人物,時而也被金炳秀錯認為樸柱泰;而電影中的安炳萬是真實存在的,作為金炳秀的好朋友,也是派出所的所長。安炳萬對于之前的連環殺人案的受害者們有著深深的負罪感,所以有著一定要抓到兇手的強烈愿望。電影中金炳秀認為閔泰柱是真兇,所以安炳萬也推動了后期追查的情節發展。
二、表現手法
小說與電影的最大的區別在于,小說中金炳秀帶著“下次會做得更好”的想法進行殺人,可以看出他是為了更加完美的快感而殺人。小說中還有金炳秀為了寫出精巧的日記,曾去文化中心學習詩歌創作的情節。對于殺人,金炳秀認為“殺人是比想象中更加繁瑣而又骯臟的職業”。
與小說相反,電影中金炳秀以殺害家暴的父親為契機,懷揣著“一定要清除掉像垃圾一樣的人”的目標和想法進行殺人,他認為這樣會有更多的人被救活,但實際上只是讓自己殺害父親的事實變得合理化。電影中金炳秀的形象反而與小說中樸柱泰的形象塑造有異曲同工之妙。電影利用金炳秀與閔泰柱的差異展現了戲劇性的效果。
電影中閔泰柱穿著蛇皮圖案的衣服隱喻了閔泰柱的形象,閔泰柱隱藏著自己的本性裝作善良的警察,在恩熙耳邊低聲細語道:“我也不愿相信,但是的確是你爸爸做的事,并且監視之后才會知道,你媽媽的失蹤也……”為了使恩熙失去了對父親的信任,閔泰柱像一條奸詐的蛇一樣蠱惑著恩熙。
小說與電影中錄音機、竹林以及閔泰柱與金炳秀的相遇情節等均相同。由于金炳秀喪失記憶,錄音機記錄著自己做過的行為以及將來要怎么做,是一個代替金炳秀記憶的裝置;竹林是金炳秀殺害的尸體的埋藏之處,也是金炳秀心靈獲得安寧的場所;金炳秀與閔泰柱的輕微交通事故,使兩個殺人者相遇,從此展開新的敘事。
作家金英夏擅長以冷靜的視角、嘶啞的嗓音表達新生代對于都市的全新感受,他的小說大多表現對人與人性的探索與追求。《殺人者的記憶法》通過一位罹患老年癡呆的老人的日記,領人們走進時間、人性與記憶的漩渦,帶人們領略最可怖的臆想空間。表面看似是意外,但內在卻涉及更加深層的關于存在與記憶、生命和意義的討論,“開放性”結局的戛然而止,在驚悚之余更留給了讀者一片遐想的空間,相對比傳統思維上殺人犯本身帶來的“惡意”,更多的是由于“破碎”和“喪失”的無奈縈繞心頭。故事中的情節似真似假,通過一處處的伏筆與情節的吻合,在紛繁復雜的碎片化信息中,貌似可以尋找出最有邏輯的“真相”。但是對于作品的解讀,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見解。小說與電影通過不同的人物塑造與表現手法,也帶給了讀者和觀眾不同的感受。
(延邊大學朝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