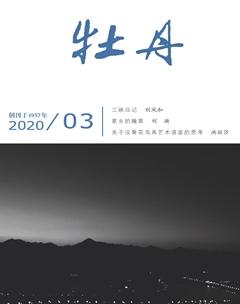從傳播學視角淺析福克納與《喧嘩與騷動》的成功之路
劉暢
福克納在從備受爭論到享譽國際的過程中,除了其出眾的文學才能,作品傳播的成功也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促成福克納成功的傳播學因素包括發表作品期刊自身的影響力、作品的電影改編、作品發表后不斷引發的論爭,以及作品在海外的譯介并不斷獲獎等。考察福克納作品成功傳播的因素,對于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的傳播與跨文化傳播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傳播,即社會信息的傳遞或社會信息系統的運行。傳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傳受雙方必須要有共同的意義空間,它是一種行為、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系統。人類傳播經歷了口語傳播時代、文字傳播時代、印刷傳播時代、電子傳播時代四個階段。《喧嘩與騷動》能在時空中流動、共享、互動,最終滿載盛譽,一定程度上就是搭乘了大眾傳播時代的快車,從而在國際產生了廣泛影響。
一、福克納與《喧嘩與騷動》在美國的研究與傳播
(一)文本傳播中的學界論爭
文字傳播是印刷時代的主要傳播方式,而文字作為載體記錄著每一個時期的現象和觀點,批評家和研究者的評點使《喧嘩與騷動》成為了一個日久彌新的話題,被注入著不同時代的思維與智慧。
20世紀70年代之前,文學界對福克納的評論褒貶不一,部分美國學者僅僅肯定福克納小說形式的創新,卻忽視了作品中深刻的主題思想與歷史意識。而另一部分批評家則不遺余力地抨擊著福克納作品中的恐怖與暴力,美國學界對福克納作品的評述呈現出了兩極分化的顯著特征。
1945年,馬爾科姆·考利編輯出版了《袖珍本福克納文集》,將福克納與他的作品首次作為一個整體擺上了價值和聲譽的天平,為人們的正確認識提供了些許引導。隨后羅伯特·潘·沃倫評點的論文發表在《新共和》上,在肯定考利的基礎上提出福克納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我們這個現代世界所共同的問題……”還強調了注重福克納“每一部作品里的結構情況”,以及他筆下的自然、黑人、幽默等主題。此后,對福克納的贊美在學界逐漸流行起來,也仍然不乏有貶斥的聲音。直到1950年福克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這極大地肯定了福克納在文學創作上的付出,令福克納作品的探討與論爭持續升溫,人們的偏見亦逐步緩和。
20世紀60年代伊始,在俄國形式主義與英美新批評流派的推波助瀾之下,對福克納及其作品的正面評價成為了主力。西方的文藝理論在20世紀70年代迎來了繁榮時期,對福克納的研究領域也得到了開拓:人們不再用極端的角度看待他的作品,而是將其置于社會、歷史、文化中客觀看待,得到理性的新啟示。經久不衰的批評賦予了《喧嘩與騷動》長久的生命活力,推動著福學向前發展,使它在文本傳播的學者論爭之中得以流傳和延續。
(二)電子傳播中的文本電影化
《喧嘩與騷動》曾被兩次改編為電影,雖然尚未得到熱烈的反響,但這種改編本身就是雙贏的嘗試。對于作家作品而言,電影的改編首先就是對作家和作品的一種肯定;其次,電影語言是一種直觀的感官語言,它的流通性也大于印刷傳播,一定程度上來說更有利于打開海外市場,擴大影響力。而導演對經典作品的選用與改編不僅為作品賦予新的生命,也是對導演專業素養的考察,只有在失敗和批評聲中尋找經驗和思考,才能提高自身水平,然后在媒介助推下實現本土文化的文化輸出,從而實現跨文化傳播。
1959年,導演馬丁·利特首次嘗試將文本電影化,他的改編完全打碎了原著的敘事框架,以小昆丁與演員私奔作為主線來串聯家族往事。雖然這次不太成功的電影化過多地依賴于舞臺藝術的營造,忽視了電影語言,卻出乎意料地表達著與原文文本相似的氣質與味道。
2015年詹姆斯·弗蘭科將《喧嘩與騷動》再次搬上銀幕,該片還作為展映片參加威尼斯電影節。作為弗蘭克最崇拜的偶像,福克納的創作深深吸引和影響著同樣內向的弗蘭科,性格的相似使他們在對世界的感知與表述上不謀而合。《喧嘩與騷動》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無法電影化的作品,意識流的表述如果不能把握好分寸,找到一條合適的表述途徑,很容易變成故作玄虛、使人難以理解。雖然弗蘭科未能找到有力的電影手段將其轉化為能夠打動觀眾的故事,但他使用大量的閃回蒙太奇來表達班吉無理性的思維跳躍,并將故事的主線闡述得清晰明朗,再現了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他的大膽改編體現了他的自信與智慧,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求新精神。
二、《喧嘩與騷動》的跨文化傳播
(一)在中國新時期背景下的譯介
改革開放新時期,為了拓寬學術視野,我國對美國文化及美國文學藝術的翻譯和研究熱情空前高漲。而實現文本的跨文化傳播,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譯介。《喧嘩與騷動》在新時期中國的翻譯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
我國學者對《喧嘩與騷動》的評介最早要追溯到1981年7月出版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福克納研究專家李文俊翻譯了《喧嘩與騷動》第二章,并作了簡要評析,第一次較為全面地向國人介紹了福克納這位在美國被廣泛研究且褒貶不一的作家。1980年至1984年,李文俊完成了對《喧嘩與騷動》的漢譯,并于同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該書出版后反響熱烈,涌現出大量的高質量評述,掀起了20世紀80年代研究外國文學尤其是英語意識流小說的熱潮。
部分學者開始從事對福克納的研究工作、撰寫專著。這一時期發表的與福克納相關的研究論文近300篇,其中分析《喧嘩與騷動》的論文高達100篇,主題囊括了人物、藝術結構、寫作手法、主題思想、創作動機等多個角度。綜上,人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譯介外來作品、考察其藝術特征與主題思想能為本土文學的發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動力。毫無疑問,《喧嘩與騷動》對新時期學界的影響是空前絕后的。
(二)《喧嘩與騷動》對中國作家的影響
譯介加速了英語意識流小說在中國傳播的深度與廣度,同時影響著新時期以后許多作家如王濛、王安憶、莫言等人的思維方式和寫作手法,一些模仿意識流的作品也應運而生。
在閱讀《喧嘩與騷動》之后,莫言感嘆道:“感到如夢初醒,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地胡說八道,原來農村里發生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成小說。”題材的廣闊使莫言備受啟發,受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啟示,莫言大膽地將他的家鄉寫到了稿紙上,從此東北高密鄉成為了莫言創作中的一個典型標志,生動又鮮活。
作家蘇童亦認可自己的創作受到了福克納的影響,“我也覺得自己似乎也可以有一個郵票大的一塊地方”,于是“楓楊樹村”成為了他的筆下農村的大多數場景,“香椿樹街”則是城市的象征,一系列以此發散的中短篇小說如《少年血》《城北地帶》《刺青時代》等被創作出來。
余華在離開家鄉海鹽多年后在自傳中無不感慨,“如今雖然我人離開了海鹽,但我的寫作不會離開那里。我在海鹽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長的時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長、河流的成長。那里的每個角落我都能在腦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語時會脫口而出。我過去的靈感都來自于那里,今后的靈感也會從那里產生”,亦肯定了地域及地域文化對他創作的深刻影響。
意識流小說寫作手法的滲入為當時的小說寫作開辟了一種新模式,也為作者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通過譯介與傳播,中國作家和研究者們開始受到意識流小說的影響,從而生成了一系列的研究評介行為。福克納的意識流小說《喧嘩與騷動》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傳播過程,完成了文化輸出,實現了在中國的跨文化傳播。
三、結語
廣義上的文學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但外來文化的侵入與接受必然會受到受體民族文化的阻抗,所以如何實現中國文學的國際化,怎樣與受體獲得文化身份的認同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媒介貫穿于當今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建構著一個與人們物質、文化生存環境息息相關的信息化時代,研究者們的人際傳播、媒介作用下的大眾傳播為福克納打開了知名度,圍繞作家及其作品的論爭使其更有影響力,而期刊推介及電影改編擴大了知名度,最后獲獎與海外譯介是其成功的重要推力。毫無疑問,傳播對于福克納的成功具有重大意義。傳播對福克納及其作品的助推作用,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與進步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啟示。
(長沙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