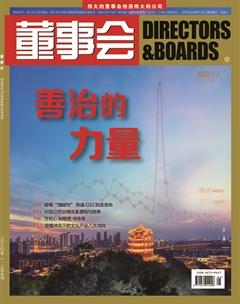容百科技扯出信披“重大”難題
羅培新 王余幸怡

因信息披露等問題,去年11月容百科技(688005)成科創板第一家收到監管函的上市企業。監管部門對其的關注點,是一筆2.06億元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到期無法兌付——超過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的凈利潤。容百科技2020年1月16日公告稱,公司已按照40%比例對比克電池應收款項單項計提壞賬準備。投資者感覺被蒙在鼓里,巨款不能收回一定早在上市前就有跡象,容百科技知情不報,沒有做到完整披露,存在欺詐上市a之嫌;容百科技頻頻“喊冤”,商票不能兌付,自己也是到期才發現,巨虧,還背上信息披露不到位之“罪”。
這個案例事關科創板企業信息披露的“重大性”標準,尚是待解難題。
容百案是否“重大”
信息披露的完整性,要求所有應當披露的信息,不得有重大遺漏。完整披露不等同于事無巨細地披露。一方面,向公眾披露信息需要符合一定的形式和要求,若要求證券發行人、上市公司對掌握的任何信息都詳細編制并發布出來,會對其施加過重負累,影響公司運營;另一方面,對投資者來說,淹沒在大量與投資決策無關的信息中反而會帶來困擾、不必要的成本,亂花漸欲迷人眼,反倒無益于了解證券的真實情況,從而作出合理決策。鑒于此,產生了事關信息披露的“重大性”標準。
上交所舉辦的首期科創板董事長、總經理專題培訓會上,上交所副總經理盧文道指出,信息披露有很多具體要求,專業性、實務性很強,而就“重大性”標準而言,披露的信息、事項可能特別多,要掌握對公司生產經營可能產生重大影響、進而對投資者的決策有重大影響的重大性事項。的確如此,科創板面向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上市的財務要求較為寬松。由是,就需要更加嚴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予以保障,從而審出一家“真公司”,避免名不符實的企業欺詐上市。2018年起,比克電池的經營業績出現下滑。容百科技的公告稱,前期根據公司銷售內控制度,因比克電池應收賬款余額較大,公司為降低內控風險,2019年起開始控制了對比克電池的供貨量,銷售額有大幅減少。或許,容百科技在上市前就已經知曉了該筆應收賬款存在一定的“爆雷”風險,但在招股說明書和上市后的信息披露中對此未置一詞。這似乎有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義務。容百科技應收賬款可能“爆雷”,屬于應予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誰來界定“重大”
科創板上市企業的特殊性使得其更為強調“重大性”標準,也帶來了適用的難題。“重大性”并非一個純客觀的信息披露標準,而是同時包含著對信息進行價值判斷的主客觀相結合的標準。客觀標準可以采用指數化或定量化的方式來約束,但就主觀而言,至少涉及上市公司、投資者、監管機構和法院等各方不同的利益衡量。究竟誰來界定這個“重大”,成了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科創板信息披露的相關管理辦法就“重大”有如下規定:首次公開發行披露階段,《科創板首次公開發行股票注冊管理辦法(試行)》規定“中國證監會制定的信息披露規則是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不論上述規則是否有明確規定,凡是對投資者作出價值判斷和投資決策有重大影響的信息,發行人均應當予以披露”;持續性披露階段,《科創板上市公司持續監管辦法(試行)》規定“科創公司和相關信息披露義務人應當及時、公平地披露所有可能對證券交易價格或者投資決策有較大影響的事項,保證所披露信息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相較《上海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規則》“上市公司和相關義務披露人應當在本規則規定的期限內披露所有對上市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種交易價格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的規定,科創板首次將投資決策影響作為重大性判斷標準之一,更加有利于投資者的保護,為上市公司判斷相關信息是否為重大應披露事項,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標準,也為交易所后續采取監管措施或紀律處分提供了規則依據。
對于重大性的判斷,存在兩種不同的認定標準。其一為“投資決策標準”,指以是否對投資者的投資決策產生重大影響,作為判斷重大性的標準;其二為“證券價格標準”,指以是否對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產生重大影響,作為判斷重大性的標準。這兩者并不存在本質沖突,類似一體兩面。歸根究底,證券信息傳導反映到證券價格上,要通過投資者這個中介。因而,從更好保護投資者角度來說,主采“投資決策標準”兼采“證券價格標準”是比較適合當前科創板的方法。
借力“理性投資者”
美國聯邦證券法規定禁止對重大事項作出虛假、誤導性陳述或遺漏重大事項,何謂“重大事項”法律并無解釋。1976年的一個案件中,美國最高法院第一次闡述了信息披露“重大性”的判斷問題:“如果理性投資者在決定如何投票時會有實質的可能性重視被遺漏事項,換言之,如果理性投資者有實質的可能性認為被遺漏事項一旦披露,將會對其己掌握的全部信息的整體含義產生顯著的影響,那么,該被遺漏事項就是重大事項。”
“理性投資者”并非全然從原告角度考量,而是一個法官假定的對于證券市場上已公開信息有所知悉,具備理性人的思維,能夠理性地認知、推理、判斷的投資者。由于具體案件的復雜性,不可能將“重大性”限定在一個剛性的公式上,判斷一個信息是否屬于重大信息取決于實際情況、針對個案進行分析。美國有關信息披露“重大性”之規則經驗,對科創板適用“投資決策標準”判斷信息是否構成重大時有啟發意義。
雖然科創板對于投資者的準入門檻作了一定限制,但投資者的水平參差不齊,不同的投資者對同一信息很有可能作出不同的價值判斷。若個案中完全依賴原告投資者角度,司法會帶來極大不穩定性和不可預期性,這與信息披露重大性標準的初衷背道而馳。因而,在適用投資決策標準判斷信息是否具有重大性時,不應完全主觀化,可借助“理性投資者”這一假定的客觀化主體進行判斷。
當然,現階段,科創板企業、投資者、執法機構等都會有自己心目中的“理性投資者”,對此的差異化理解會帶來對“重大性”的不一判斷,這不利于科創板信息披露工作的統一展開。而在科創板相關配套制度的保障下,市場更向理論上的有效市場趨近,證券價格的變動,可作為一個有力的客觀參照物來輔助衡量某一信息是否“重大”:主采“投資決策標準”兼采“證券價格標準”。要特別指出的是,合理構建科創板之信息披露重大性標準,關鍵在于回到“以信息披露為中心”這一初心。披露充分、市場透明,才會帶來理性投資,“賣者盡責,買者自負”,健康資本市場得以形成,成熟商業社會得以運轉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