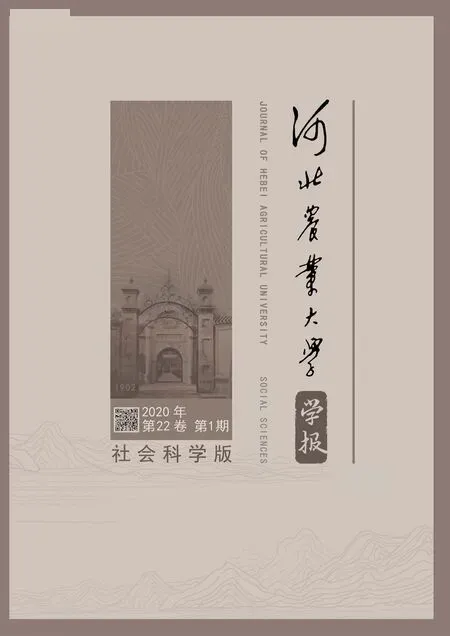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司法確認研究
——基于山西省230份裁判文書的分析
張旭光
(山西農業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山西 太谷 030801)
“農經組織”是基于地域、血緣等紐帶發展起來的具有法人資格的特殊經濟組織[1]。當事人獲得成員身份是享有“農經組織”各項成員權益的前提條件。因此,成員身份的有無得失對于維護“農經組織”成員合法權益意義深遠。基于此,在集體成員權益糾紛案件中,當事人是否具有本“農經組織”的成員身份往往成為當事人的爭議焦點。由于中國現行法律沒有規定確認成員身份的明確標準,法院在是否認定當事人具有集體成員身份問題上呈現矛盾的司法態度。尤其困惑的是,面對實踐中層出不窮的集體成員身份確認糾紛,司法救濟功能卻顯得力不從心,甚至有的糾紛連訴訟領域都無法進入。上述困境直接影響了“農經組織”成員資格糾紛的有效解決。鑒于此,本文收集整理了230份裁判文書作為樣本進行案例分析,以期探索研究出一條對“農經組織”成員身份科學判定的司法推動路徑。
本文以“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相關案例為檢索對象,截止到2019年4月4日,一共搜索到涉及山西省“農經組織”成員身份確認的裁判文書共計302份。考慮到有些案件并未涉及成員身份的實際確認,部分案件的裁判文書僅涉及程序問題,最終選取230份裁判文書作為本文的分析樣本。本文運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從樣本案例統計分析中總結山西省該類案件的總體樣態,進而發現山西省審判機關在裁判“農經組織”成員身份糾紛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構建司法機關如何有效地防范、化解該類糾紛的對策。
一、山西省“農經組織”成員身份司法確認案件總體狀況
(一)案件分布呈現不均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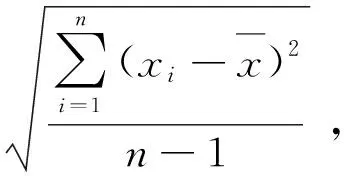
(二)糾紛起因呈現趨同性
按照直接導致身份確認糾紛發生的外部因素為標準,筆者將引發糾紛的原因分為征地補償、地質災害移民搬遷、資源開發土地流轉、福利分配、土地確權以及其他原因等6個類別,并在此基礎上做了糾紛起因數據統計。
根據統計,土地補償是引發糾紛的最主要因素,230個裁判文書中,明確表明是由土地補償糾紛所引發的訴訟竟然高達210份,其數量占到樣本總量的91.31%。土地補償糾紛的具體原因主要有征地補償、地質災害移民搬遷、資源開發等。其中,僅因征地補償費用分配引發的糾紛共發生136起,占樣本案例總數的59.13%;因地質災害、移民搬遷引發糾紛發生43起,占樣本案例總數的18.7%;因資源開發、土地流轉引發的糾紛發生31起,占樣本案例總數的13.48%;其它糾紛起因中;由村民福利分配引發的案件占6.52%;土地確權引發的案件占1.74%;其它原因,諸如因房屋買賣合同糾紛、繼承糾紛等引發的案件占到樣本總量的0.43%。可見,現階段農村集體成員身份確認案件的糾紛起因百分之九十以上同土地補償費用分配有關,山西省此類案件的發案起因呈現出高度的趨同性。
(三)司法態度呈現沖突性
裁判結果直接反映法院處理此類案件的司法態度。本文以案件裁判結果為分類標準,將230個樣本裁判結果分為“確認資格”(53.91%)、“否認資格”(20.87%)、“無權受理”(13.91%)、“二審裁定受理”(2.61%)等類型。這組數據直接反映出山西省各地各級法院對這一問題在裁判立場上的對立和沖突,具體沖突可以總結為以下兩方面:
第一,法院是否受理之沖突。從樣本案例來看,山西省司法實踐中仍有為數不少的裁判文書對成員身份確認糾紛持有不予受理的司法態度,尤其是在2014年以前,此類案件基本無法進入訴訟領域;自2014年以后,法院不受理此類案件的比例逐漸由80%下降至2018年的5.77%,呈現出明顯下降的總體趨勢,反映出法院逐漸以更開放的態度接納此類案件。
第二,同類案件不同裁判之沖突。在對樣本案例分析比對發現,山西省法院系統對涉及成員身份確認的案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對立沖突。如,在原告楊某訴某村委會要求支付征地補償款糾紛一案中,法院就以缺乏明確法律解釋導致人民法院不具備此類糾紛的必要條件為由,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然而同類案件卻在有的法院存在不同的審理結果。比如高談全訴交口縣回龍鄉田莊村民委員會下桃花村民小組的類似案件上,交口法院則以高談全在被告處有房有地為由而確認其具有被告組織成員的身份,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予以了支持。可見,不同法院在同類案件上秉持截然相反的裁判邏輯,而更令人困惑的是,這種沖突在230份案例樣本中絕不是偶然現象,同級法院之間、上下級法院之間都存在這種現象。
(四)確認標準多元化
通過樣本案例研究,山西省法院內部遵循單一標準和綜合標準兩種裁判思路,而兩種裁判思路下又存在諸多判斷標準。單一標準裁判思路總體上有戶口說、基本生活保障說和固定生產生活關系說。例如,周某訴左云縣小京莊鄉向陽寨村民委員會一案中,左云縣人民法院認為“原告的戶籍于2014年8月11日已遷居至向陽寨村,從該日起即具有向陽寨村村民資格”,可見左云縣法院在認定成員身份時堅持的是戶口原則,只要具有本村戶口就認定為集體成員;然而本案上訴后,大同市中院則認為“被上訴人的戶籍雖于2014年8月11日遷入向陽寨村,但在該村未取得承包地及宅基地,長期在外工作,未盡過村民義務,不具有該‘農經組織’成員身份”,大同市中院在認定資格身份問題上并不唯戶口論。
而在綜合標準裁判思路下,各個法院堅持的認定標準更是五花八門。根據各要素地位的不同,有的法院“堅持生產生活為基本原則,酌情考慮戶籍、權利義務等因素”,有的法院堅持“戶籍為基本因素,酌情考慮生產生活、土地承包、土地生活保障、服從管理等因素”,還有的法院堅持“戶口等形式要件+土地生活保障的實質要件”的標準。
(五)糾紛主體呈現特定性
“農經組織”成員身份糾紛往往發生在特定的當事人之間,這種特定性體現在以下方面,第一,一審原告往往集中于鄉村社會的弱勢群體,綜合樣本裁判文書,一審的原告主要有出嫁女、女兒戶、招贅女婿、外遷戶等;第二,被告基本固定是村民委員會、村民小組,個別情況還可能涉及到征占土地的公司、企業等經濟組織。
二、山西省“農經組織”成員身份司法確認現狀原因分析
(一)土地調整政策價值導向: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如上所述,90%以上的成員身份糾紛是由于對集體土地的補償費用分配所引發,探究此類糾紛深層次的原因,離不開對“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土地調整政策的剖析。農地調整的真正目的在于保障每個集體組織成員有地種、有飯吃,其追求的價值應當是土地在集體成員之間實現公平分配。但是由于頻繁調整土地,往往帶來大量的糾紛甚至違法亂紀現象。為了提高鄉村社會治理效率,實現鄉村社會穩定,國家政策法律堅持“大穩定,小調整”的原則,即犧牲土地分配的局部公正換取鄉村社會治理的效率與秩序[2]。不可否認,這種政策不僅穩定了農民對土地的投資預期、提升了土地生產效率,也防止了土地細碎化和利用調地權力尋租等頻繁調整土地帶來的社會問題。但是追求穩定往往會帶來滯后于社會現實需要的結果,由于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等因素,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會經常發生變動,在堅持“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調整政策下,新加入的集體成員事實上成為無地、少地的人口,一旦集體經濟組織土地被征收或流轉,這些人往往由于沒有土地而在土地補償費用分配上被“另眼相待”。為爭取自己的權益,集體成員往往以侵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為由與村委會、村民小組對簿公堂,由此引發的訴訟中,確認當事人是否具有成員資格往往就成為案件審理的焦點之一。
(二)身份確認糾紛司法監督缺位:司法不作為
法院司法不作為的原因如下:第一,誤解集體成員身份司法確認的性質。 部分法院認為,集體成員身份司法確認目前沒有立法依據,法院處理案件缺乏必要條件;第二,割裂集體成員身份司法確認與村民自治的關系。有法院把村民自治與司法審查絕對對立起來,認為集體成員身份確認問題屬于村民自治范疇,因此不屬于法院受案范圍,法院無權受理;第三,部分法院認為“農經組織”成員身份糾紛不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爭議,不屬于人民法院民事主管范圍。例如崔曉君訴澤州縣金村鎮湛家村村民委員會一案中,原告請求確認其具有被告成員身份,而法院則以不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糾紛為由拒絕受理此案,據此一審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訟請求。
(三)司法救濟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司法裁量權過大
關于“農經組織”成員身份問題,目前還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對此作出明確規定。而根據我國《立法法》規定,有權解釋“農經組織”成員資格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未就此作出任何明確解釋。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法院對身份確認糾紛在是否立案受理、是否認定資格等方面存在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在立案階段,有的審判機關堅持糾紛屬于村民自治范疇的思維,因此審判機關不應插手干預;而有的審判機關則認為村民自治不是絕對不受司法監督的領域,為了防止出現“多數人的暴政”,司法審查應當有限度地介入村民自治范疇。在審理階段,由于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導致各級法院、各地區法院在裁判思路、司法確認標準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標準的多元化等于沒有標準,由此導致實踐中上下級法院、同級法院之間常常會出現同案不同判、案結事不了的尷尬局面。
(四)鄉土邏輯與國家邏輯的博弈:價值與標準的差異
中國農村在經過城鎮化快速發展等重大歷史變革后,農村富余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由此現代性因素逐漸滲透進入傳統封閉村莊,沖擊原有的鄉村倫理價值[3],傳統鄉土性特征開始發生變化,傳統“鄉土社會”逐漸向“后鄉土社會”過渡,村民的主體意識強化,要求鄉土社會的生活秩序更多體現出規則性和公正性。“后鄉土社會”的治理中,同時兼具有現代法治文明和鄉土文化習俗的因素。成員身份的確認往往交織著鄉土社會傳統習俗與國家政策法規的價值博弈。在農民的鄉土邏輯中,集體成員身份的確認主要考察當事人是否是原始農業人口以及是否具有特定的血緣、婚姻、輩分關系[4]。可見,鄉土邏輯的身份確認標準中往往滲透著強烈的地域、血緣色彩。基于此,在中國農村社會的傳統觀念中,出嫁女、女兒戶、招贅女婿、外遷戶是農村社會這個封閉系統的異物,融入集體經濟組織往往面臨著觀念、經濟、情感、心理等多因素的阻礙,每當因征地補償等重大經濟利益分配時,在上述因素驅使下,這些外來戶的利益往往首當其沖受到沖擊。而從國家邏輯的層面來看,其追求的是公平價值目標,往往以戶籍、權利義務關系、固定的生產生活關系等因素為認定基礎,保證“人人有份,機會均等”,確保每一位組織成員均享有成員資格以及相應的成員權益。司法機關認定集體成員身份屬于國家邏輯層面上的法律介入,其確認標準和追求價值均與鄉土邏輯存在差異,勢必造成成員身份確認糾紛日益多發和日趨復雜。
三、農經組織成員身份確認的司法推動
(一)堅持尊重村民自治和合法性審查相結合的原則
村民自治是我國農村社會治理的基本原則,是我國憲法規定的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群眾民主自治原則。但是,村民自治并不意味著可以隨心所欲,村民自治行為必須在國家政策法規范圍內實施,村民自治行為與接受人民法院的司法監督并不矛盾。所以,法院在審理“農經組織”成員身份糾紛時既要尊重“農經組織”基于自治權制定的認定規則,同時也有必要對村民自治行為的合法性依法進行司法審查。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和農村社會的深刻變化,集體成員身份確認糾紛越來越復雜多樣,社會關注度、敏感度也愈發增強,這種變化呼喚更專業、更權威、更客觀中立的裁判機關的介入;另一方面,在村民自治活動中,多數村民利用村民大會決議、村規民約等自治形式實施侵害少數村民利益的情況并不鮮見,因此司法機關的介入有利于防止村民自治中侵害個別人合法利益的多數人暴政現象。正如約翰.羅爾斯所說:任何一個人的生命都是唯一的生命,不能由于外界的壓力強迫任何人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我們無權強迫他人犧牲自己提升自己的幸福指數[5]。
(二)裁判理念上要注重“軟硬結合”
法治的優勢就在于其可以超越血緣共同體,維系社會秩序,并為每個成員提供一種需要普遍遵守的行為模式,保證社會的公平穩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在當今中國鄉土社會可以否定天理人情等軟法的治理作用[6]。“當鄉土社會秩序由‘熟人社會’的‘自生自發秩序’變遷到‘半熟人社會’的‘混合秩序’”時[7],這就要求司法機關在解決身份確認糾紛中,要將理性基礎上的“硬法”和情理基礎上的“軟法”相結合。鄉土社會生活中交織著國家邏輯和鄉土邏輯的博弈,而后鄉土社會下現代觀念與傳統習俗的劇烈沖突,導致雙方博弈更加激烈。依法治國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戰略保障。然而,宗族家訓、民情習俗等中國農村的特殊性使得在集體成員身份的確認過程中有必要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予以適度融合[8]。司法機關解決糾紛不僅要追求好的法律效果,也要實現良好的社會效果,司法機關確認成員身份時要防止單純走“硬法”的片面路線,必須循著兩條邏輯進行“軟硬結合”:一是基于國家法律規范的“硬法”邏輯;一是基于鄉土社區文化的“軟法”邏輯。尤其是在司法確認標準中,不僅要堅持國家硬法邏輯的剛性要素,還要吸收軟法邏輯的柔性要素。“軟硬結合”的裁判理念不僅有利于緩和硬法要素的“普遍性”可能導致的個體不公正,而且有利于避免硬法要素“滯后性”帶來的對新問題的司法不作為,也能避免硬法要素“強制性”導致的對人權的損害。
(三)完善民事案由規定,賦予司法機關確認成員身份的正當性
民事案由概括體現了民事訴訟糾紛涉及到的民事法律關系[9]。人民法院在決定是否受理案件時,不僅要考慮糾紛的法律關系內容,還要確定該糾紛是否屬于法院民事主管范圍、本院是否對該糾紛具有管轄權等。可見,通過確定民事糾紛是否屬于法定案由,有利于人民法院準確判斷是否應當予以民事立案受理。構建科學完善的民事案由不僅有助于在民事訴訟中準確確定糾紛法律關系內容,而且直接影響糾紛是否屬于人民法院的主管范圍、糾紛案件是否能進入訴訟領域得到救濟等問題的解決。我國現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設置了4個層級共424個具體民事案由,而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直接相關的案由只有1個具體案由,遠遠不能適應農村法治建設和農民權益保障的現實需要。由于我國民事案由并沒有針對集體成員身份確認糾紛直接做出的規定,當事人如果單獨就確認集體成員身份提起訴訟,法院往往以不屬于法定案由為由拒絕受理此類糾紛。筆者認為,可以仿照“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案由,由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規定》第八部分中增加1個二級案由“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關的糾紛”,該二級案由下設2個三級案由,其一是“侵害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益糾紛”,其二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確認糾紛”。明確規定法院受理此類糾紛的案由根據,徹底解決法院在直接受理此類糾紛時缺乏案由依據的尷尬境地。
(四)司法機關應當確立“以戶籍為形式要件,以權利義務為實質要件”的統一裁判標準
司法機關確認成員身份離不開對農經組織身份確認的初衷和“三權分置”土地流轉制度的考察。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將成員身份確認工作置于影響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的樞紐地位。“農經組織”成員身份確認的本質就是明確誰有權享有組織成員身份帶來的財產權益,進而實現農民“離土離鄉不離權”,真正實現農民由“土地人”向“社會人”的轉變。而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明確以立法的形式確認了“三權分置”的土地政策要求,即承包方承包土地后,可以自己經營,也可以流轉其承包地的土地經營權由他人經營。
基于此,司法機關解決糾紛應當堅持“以戶籍為形式要件,權利義務為實質要件”的綜合確認標準,即確認集體成員身份時首先要審查當事人與該集體經濟組織之間是否形成固定的生產生活權利義務關系,同時還要兼顧考察當事人的戶籍情況等形式因素。理由如下:
第一,“權利義務為基本原則”還原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經濟組織與其組織成員之間法律關系的本來面目。在認定成員身份時,應當首先考察當事人是否在農經組織享有宅基地資格權和使用權、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以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等,是否履行集體成員的義務等等,來綜合確定當事人是否具有成員身份[10]。
第二,農經組織作為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經濟實體,其組織成員的判斷標準中應當剔除戶籍等行政管理要素,但基于我國農經組織形成發展的地域性、血緣性等特殊邏輯,目前還不具備完全不考慮戶籍因素的條件,可以把戶籍作為酌情考慮的形式因素。在此思路下,戶籍非認定成員身份的充分條件,如果只具有戶籍而不符合權利義務實質要件的不能認定為集體成員。
第三,認定成員身份必須充分考慮“三權分置”土地流轉制度和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趨勢。隨著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對于流轉土地的農戶來說,他們可能不在農村生活,也可能根本不從事農業生產。司法機關在認定集體成員身份時如果不考慮這種社會現狀,機械單純地考察是否存在固定的生產生活關系或者基本生活保障等因素,必然會與土地三權分置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馳,也與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社會趨勢格格不入,以此為主要判斷標準容易喪失個案正義。
四、結語
對集體成員身份扎實精準地進行司法確認,不僅有利于加強對農民基本民事權益的保護,更是推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成功改革的關鍵。本文通過230份裁判文書的整理,對山西省集體成員身份司法確認狀況進行了系統的案例研究和數據統計,在此基礎上對集體成員身份司法確認的科學路徑做了深入研究。研究表明:第一,山西省部分法院對集體成員身份確認糾紛基于種種理由仍堅持不予受理的司法態度,筆者認為法院在解決此類糾紛時應當堅持尊重村民自治和合法性審查相結合的原則;第二,山西省法院對成員身份的確認存在多元化的確認標準,并且各標準考察因素以及各因素地位更是五花八門,為防止出現“同案不同判”消解司法權威的現象發生,在現階段統一確立“以戶籍為形式要件,以權利義務為實質要件”的確認標準比較適宜;第三,法院在確認成員身份是要避免單純在國家邏輯層面思考,還應結合鄉土社會特有的邏輯,統籌考慮戶籍、土地承包、對集體的貢獻、村規民約、民情習俗等因素進行身份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