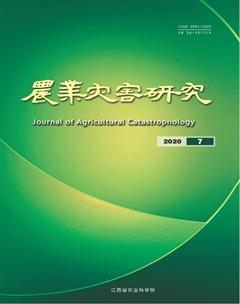云南歷史農業災害及其文化
施磊



摘要 據歷史記載云南省在元、明朝代的農業災害主要有旱災、洪災、澇災、地震等;至元、明時期,由于當地冶煉業的發展以及山地農業的開發,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農業災害頻繁;至清代后歷史記錄逐步豐富,云南省農業災害又增加了冰雹、雪災、蟲害、霜凍、風災、火災等。20世紀后,云南省農業災害的發生率更高,尤其是建國以來,我國各項事業飛速發展,人們的生產活動對整個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影響,由此引發了更高頻次、更為嚴峻的農業災害。云南省的農業災害具有分布廣泛、連年頻發、災情嚴重等特點,造成的農業經濟損失在整體上呈現出增長趨勢,成為限制云南地區農業與經濟發展的重要負面影響因素。研究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及其相關文化,對云南省現代化農業發展中的防災抗災活動具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歷史;農業災害;文化
中圖分類號:G27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305(2020)07–0–05
DOI:10.19383/j.cnki.nyzhyj.2020.07.047
Yunnan Historical Agricultural Disaster and Culture
SHI Lei (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Kunming, Yunnan 650034)
Abstrac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agricultural disasters in Yunnan Province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mainly included droughts, floods, waterlogging, earthquakes, etc.; to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melting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agriculture, landslides, landslides, mudslides, and ground collapses Such agricultural disasters are frequent; after the Qing Dynasty, the historical record gradually enriched, and the agricultural disasters in Yunnan Province increased hail, snow, insect damage, frost, wind and fire. After the 20th century, the incidence of agricultural disasters in Yunnan Province was even higher. Especiall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y country, various undertakings in our country have developed rapidly. People's production activities have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the entir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vere agricultural disaster. The agricultural disasters in Yunnan Province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frequent occurrence in successive years, and serious disasters.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 losses caused by them have shown an increasing trend as a whole,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negative factor restricting the agri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Yunna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gricultural disasters and related culture in Yunnan Province has positiv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lief activ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Yunnan Province.
Key words Yunnan Province; Historical Agricultural Disaster; Culture
伴隨全球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人類更為頻繁的活動使得農業自然災害情況逐步加劇,并成為影響全球發展的重要問題之一。由于農業生產活動的特點,絕大多數農作物具有不可轉移性,在農業災害來臨時采取的預防和補救措施較為有限,而一旦發生農業災害,會嚴重破壞農業生產。2019年,云南省主要發生了干旱、地震、山體滑坡、泥石流、洪水等農業災害,農作物受災面積1 659.8hm2,絕收125.8hm2,受災農作物的絕收面積占比為7.6%,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損失,此次農作物受災面積達到了21世紀以來的較高水平。因此,本文對云南省農業歷史災害及文化進行研究,從歷史出發對云南省的農業災害進行過程性、系統性研究分析,做到以史為鑒,希望對未來云南省農業自然災害的預防和治理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
在全國范圍內,云南省可以說是農業災害發生最為頻繁、種類最為繁多、受災影響最為嚴重的省份之一。根據相關史料記載,我國歷史上所出現過的農業災害類型幾乎都在云南省發生過,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云南省地理情況復雜,地質特征多樣,許多地理單元在整體上較為封閉,因此許多農業災害的影響范圍較小,并不波及云南大部分地區,其影響程度有限,因此在元、明兩朝之前,云南省農業災害的記錄較為簡單;在元、明兩朝之后,隨著農業史料記載的逐步發展,云南省農業災害記錄更為詳細、完整,文獻記錄逐漸豐富了起來;到近代以后,由于交通、通訊、文字載體的發展,云南省歷史自然災害的記錄更為全面、詳盡,且具有一定的關聯性,相關史料更為系統。
近年來,云南省農業災害仍舊頻繁,且在科學技術的支持下對農業災害的治理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但仍呈現出難以有效防治的特點,對于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的研究意義在于以史料揭示云南省各歷史時期的農業災害情況,雖然史料記載不可能涉及云南省歷史的所有時間、所有地區,但也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能夠為現代農業制定防災、減災、救災策略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鑒。
1 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的種類與其特征
1.1 云南歷史農業災害主要種類
1.1.1 旱災 無論是古代還是近代,在云南省農業災害中,旱災發生較為頻繁,對農業生產造成了嚴重影響。例如,元代至治二年(1322年),臨安路河西縣出現了春夏之旱“春夏不雨,種不入土”,即此地春夏兩季雨水甚少,天氣大旱,地表干裂,種子無法埋入土壤中;明景泰四年(1453年),昆明、姚安兩地出現了旱情,幾乎是顆粒無收,“民多餓死”;清嘉慶二年(1797年),楚雄發生大旱,民“大饑”,無可充饑。
1.1.2 澇災 澇災是因為雨水過度而導致地表及土壤中大量積水,抑制農作物的呼吸或者破壞農作物的結構,從而造成農作物減產,甚至是絕收。例如,名景泰元年(1450年),玉溪澄江地區受“淫雨害稼,斗米四錢”,澇害使得農作物減產,米價上升;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秋季,姚安地區淫雨連綿,“民多饑”;光緒三十三年(1907)秋天,羅次縣(今祿豐地區東北)發生了澇災,“秋熟未獲……禾稼被傷者殊多”。
1.1.3 洪災 洪災為多發的農業災害,多發于春、夏兩季。由于降雨量增多而導致江河漲水,或者地下水難以存儲大量水資源導致洪水大漲,淹沒農田,沖毀、泡爛莊稼,由此造成嚴重的農業損失。例如,明正統五年(1440年),順寧府(今臨滄市鳳慶縣一帶)出現將近20 d的大雨,引發了洪水“沖沒田廬,不可勝計”;明正德七年(1512年),滇池地區發生洪災,滇池漲滿,“滇池水溢傷禾稼,街市行舟”;清道光三十四年(1908年),降雨10余日,昭通利濟河水位大漲,“沖去豆麥無數”,造成了嚴重的絕收。
1.1.4 雪災 雖然云南地處南方,但是由于海拔較高,某些地區氣候寒冷,降雪在云南東北部、西北部較為常見,屬于正常天氣。例如,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2月,昆明大雪,“雪深七尺,人畜多斃”;明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10月,云南永昌府(現保山市區域)秋季10月降雪,“雨雪黑,傷谷”,其中的“雨雪黑”說明大氣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劍川雨雪,秋不熟”,即劍川7月出現雨雪,導致秋收時節莊稼仍未成熟[1]。
1.1.5 冰雹 在農業方面,冰雹會對家禽、畜類、農作物造成嚴重的傷害。例如,明嘉靖元年(1533年)10月,左衛(玉溪市左衛一帶)冰雹降落,大如雞蛋,“禾苗房屋被傷者無算”,即冰雹傷害禾苗無數;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晉寧地區3月下冰雹,如拳頭般大小,“傷菽麥,歲饑”;至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6月初,羅次所降冰雹如雞蛋大小,冰雹砸死一牛、一人,且導致“田禾多損壞”。從中可以看出,云南地區的冰雹多發于春秋時節,對作物、牲畜、家禽的危害極大。
1.1.6 霜凍 一般而言,霜凍屬于正常的天氣現象。但是若霜凍出現在幼苗生長時期,則會凍傷、凍死苗、花,導致作物減產甚至是絕收,且絕收率較高。例如,明正德八年(1505年)4月,武定縣地區發生霜凍,“隕霜殺麥,寒如冬”,麥子皆被凍死;明天啟二年(1622年)8月,曲靖師宗縣地區降霜,“隕霜殺禾”;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8月,羅次發生大范圍霜降,“禾苗被其肅殺”,當年作物收成極少。
1.1.7 風災 云南省屬于我國內陸地區,非沿海省份,雖然免受臺風之患,但也存在大風天氣,給農業生產活動造成嚴重影響。例如,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6月初,臨安府(今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縣)風雨交加,天寒,凍死數十人,大片作物、畜禽明,“鳥雀僵死無計”;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玉溪市通海縣一代發生大風,“大風拔木數百株”,果樹禾苗倒伏眾多。
1.1.8 蟲害 蟲害是大規模存在危害農作物的害蟲,對農作物的損害巨大。例如,西晉永寧元年(301年),永昌府發生螟蟲之災,范圍及危害甚廣;明成化元年(1465年),陸豐地區發生蝗災,“無秋”,即秋獲絕收。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定遠地區(今牟定)發生蝻蟲(蝗蟲的幼蟲)大量毀壞作物,有“蝻蟲食苗”的記載;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秋季,“楚雄蠡,饑”;光緒九年(1883年),太和地區(今屬大理區域的一部分)發生螟蟲之患,導致莊稼嚴重減產,“禾生螟,歲歉”。
1.1.9 地震 云南省處于地震活躍帶上,因此歷史地震記錄較多,較大級別地震不但造成人、畜傷亡及房屋建筑倒塌,還會引發山崩或其他地質活動,給農業生產活動帶來影響。例如,西漢時期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犍為郡(今部分屬四川,部分屬云南,位于兩省交界區域)發生了大地震,地震引發了山崩,山崩“壅江水,水逆流”,導致農作物被淹沒毀壞;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云南祥云縣、澄江、大理等地發生了大規模地震,且余震不斷,如大理“屋宇盡壞、死數萬人”,導致作物毀壞,農戶減少;道光十三年(1833年)7月,坤寧、嵩明等十余州縣發生了大范圍地震,及至同年9月,羅次、富民、昆陽、易民等地也頻發地震。在現有史料中,云南省自漢代至今共記載地震400多次,其中四分之一的地震導致了人、畜傷亡。
1.1.10 瘟疫 云南省處于亞熱帶地區,區域內山巒起伏、叢林茂密,嶺下多瘴,容易出現傳染性疾病,并可能由此引發大規模的瘟疫,進而造成人畜死亡,給農業帶來巨大危害。例如,在明正德九年(1514年),麗江發生了大規模的瘟疫,“死者不可勝計”;清康熙18年(1679年),廣西府(今云南瀘西縣)發生了瘟疫,“人畜皆災”;尤其是光緒十八年(1892年),鄧川發生了嚴重的鼠疫,且人畜之間出現嚴重傳染,數年未得到有效救治,“鄉疫為墟”,病死率“十之八九”,農作物無人管理,家禽、牲畜更是染疫死亡。
2 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的特點
在封建時代,災害代表著社會穩定及民心所在,而農業災害直接關系著農民的生活水平及社會是否繁榮,如唐杜甫以“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之句展現開元盛世的物阜民豐。根據前文所言,在元、明以前,云南農業災害相關的記載在正史中極少,正史多注重以人物列傳;到了元、明時期,由于社會各行業得到了更為體系化的發展,由此關于云南省農業災害記錄的史料開始增多,尤其是當時修撰“地方志”“家族志”等蔚然成風,地方志中對于當地災情的災害及其他事件的記錄較多。根據相關史料的分析研究與總結歸納可知,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
2.1 地震災害的發生頻次最高
自西漢至清代,云南省史料中關于地震災害的記錄459次(表1),其中重大的地震災害超過了100次,對農業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例如,唐光啟二年(886年),南詔地區發生地震,“龍首龍尾二關,三陽城皆崩”;還有弘治十二年出現了云南歷史記載中最為嚴重的地震災害。清代的地方志記錄則更為詳細:順治九年(1652年)6月,大理蒙化縣域發生地震,地震之勢猶如萬馬奔騰,天空中霧瘴彌漫,大多數民居坍塌,“震時河水懼干,年余乃止”,地震造成河水斷流,且影響持續了一年以上,給當地農業生產活動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在光緒年間(具體年份不詳),云南地區發生大地震,官衙、民居多被損壞,地下水位暴漲,地下出水“壓死人畜無數”。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中地震的記載甚多,且內容較為豐富,其中地震發生頻次最高,對農業造成的危害巨大。
2.2 洪澇災害、旱災是歷史上出現最多的農業氣象災害
在云南各民族發展與地理遷徙之中,水災是人們從生命、物質及精神上所付出代價最為慘重的災害,這一結論可以在云南省多個古老少數民族的故事、傳說、記載中窺見。同樣,在元、明以前,對于洪澇災害的記載甚少,而在元代以后才逐漸多了起來。例如,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秋天,騰沖地區因連續陰雨引發洪水,“壞民廬人舍,人畜死者以百計”,即人畜被淹死者眾多,作物更是難以保全;明正德七年(1512年),數日大雨導致滇池水位上升,“溢傷禾稼”;明天啟五年(1625年)6月,云南全境遭遇大雨,河水暴漲沖過堤壩,淹沒城池,昆明街市的水面平均高度為“六七尺”(約200~233.3 cm),“附近十余州縣亦成澤國”,一直從6—10月,大雨不絕,洪水難退,“迤東、西二三千里,同時被災”,由此可見洪水范圍之廣、時間之長、影響之大。
清代以后對于農業災害的記錄更多,且記錄載體多元化,如奏折、檔案、地方志等,清代也是歷史上對云南農業災害記錄最詳細、最全面、最多樣的時期。例如,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秋,安寧州(今安寧市)淫雨不斷,洪水沖入城內,淹沒民居,“兩岸田禾盡毀,秋成無收”;乾隆三十年(1748年)6月,云南多發大雨,徵江府(今澄江縣)、廣西府(瀘西縣)等地房屋田地皆被淹沒。同時,昆明縣“災田二百一十一頃九十七畝”,景東府(今云南景東彝族自治縣)“災田三頃一十三畝”,給農業生產造成了巨大損失。
此外,從歷史史料中可以看出,云南境內旱災發生較為頻繁,是影響范圍較廣的農業災害。自元、明以后,關于云南旱災的記錄逐漸增多。云南地區清代的地方志內,幾乎每一年都有關于旱災的相關記錄。例如,康熙元年(1662年),彌勒縣大旱,“斗米銀價二兩”,反映出旱災導致農作物減產的信息;嘉慶二十二年,云龍縣的旱災導致了饑荒,百姓“掘草木以食”。由此可見,旱災在云南歷史農業災害中屬于發生頻次較高的農業災害。
2.3 低溫冷凍、霜災、冰雹是云南歷史常見的農業災害
一般而言,雪災主要多發于云南省西北部海拔較高的山區地帶,該地區的降雪較為頻繁,且屬于正常的天氣現象。而云南中部、南部的氣候整體較為溫和,降雪次數相對較少,因此中南部一旦降雪,則容易引起農業災害。例如,元至正二十七年2月大雪,昆明多地人畜深受其害;明天啟四年(1624年)七月,武定地區大雪,“損禾”。
霜凍也是云南省歷史上較為普遍與常見的農業災害之一,霜凍的出現對農作物的幼苗、花葉等有嚴重的毀壞作用,這在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中也具有詳細記錄。例如,武定地區在正德元年(1506)4月,小麥皆盡被凍死,“武定隕落霜殺麥,寒如冬”;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8月,羅次大霜,“禾苗被其肅殺”,導致當年收成減產。
冰雹農業災害在云南省大部分地區都有發生,且分布較為廣泛,在前文已有文獻敘述。同時,蟲害、風災也是云南較為常見的農業災害,但是在歷史記錄中較少,且記錄的內容比較簡單。
2.4 云南歷史農業災害空間與時間上的特點
從空間上而言,根據相關史料,發現距離當今時間越是久遠,農業歷史災害的種類及發生頻率越少,而距今越近,則農業災害越多。從分析中可以看出,從元代開始,尤其是明、清,史料中記載的歷史農業災害開始大量增加,且記載更為詳實、全面[2]。原因是自元代以后全社會對于地域性歷史的記載、農業方面及更為普遍和重視,同時也因為農業災害對當地造成的影響越來越大,因此人們越來越關注農業災害;還有一個原因是隨著社會發展,人口增多,使得農業災害發生更為嚴重,導致作物減產和絕收,餓殍眾多,成了愈發具有影響力的社會問題,故而農業歷史災害在歷史記載中逐漸凸顯。例如,根據表1可知,明代關于云南省歷史自然災害的記載多于331次,而清代則超過了657次,清代比明代多一倍;同時,從明清兩代關于云南省農業災害的記錄中可以看出,云南幾乎年年都發生多次農業災害,有的災害甚至是持續數月、數年。
從空間上而言,歷史上云南省各地都遭受多種形式的自然災害,且由于各區域地理、氣象環境不同,導致歷史農業自然災害的分布不平衡,某些自然災害多發于某些季節、某些區域中。例如,在史料中可考的洪災有102次,其中發生于農歷五月到八月的洪災共76次,占比74.5%;記載了相關地域的洪災共計超過200次,主要集中于南盤江、瀾滄江、金沙江、元江等流域中,史料記載的各洪災集中發生地點及頻次(表2)。
而從前文分析可看出,冰雹災害在云南歷史發生時間多集中于農歷3、4月,而淫雨連綿,澇災頻起的時間大約為農歷7、8月,且其中大多在秋季發生;而地震災害主要集中于云南西部、中部,這兩個區域內的地殼運動較為頻繁,并且地震多發于秋季,一般伴有降水及其他惡劣天氣。
云南省農業自然災害具有一定的聯系,可以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根據史料記載,在云南省歷史上洪澇災害多發時,往往由于山體、山基受到沖擊而產生山崩;而持續時間較長的大風天氣可能會引起大雪、冰雹等農業災害,不僅給農業生產活動帶來嚴重的影響,導致莊稼減產或絕收,家禽和牲畜死亡,并且還會造成大量的房屋毀壞、人員傷亡,故本文研究的農業自然災害不僅是農業方面的,還屬于自然災害。例如,前文所說的明弘治十四年、清光緒二年的洪災,云南騰沖、嵩明等地發生的嚴重地震,造成當地經濟大幅下滑。此外,農業自然災害造成的大面積饑荒會引起社會動蕩。例如,西晉光熙元年(306年)發生了嚴重的饑荒,“頻歲饑疫”,因疫情與饑荒而歿之人超過10萬;明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昆明府發生大規模、長時期的干旱,“夏秋不雨,民盡饑”;在光緒十九年(1893),昭通地區因糧食歉收造成饑荒,官府及社會組織“三楚會館”開棚施粥,但效果甚微,繼而發生疫情,“死者甚眾,一匣(棺槨)輒裝數人”西晉至清代云南省因農業災害引發的饑荒次數(表3)。
3 云南歷史農業災害的成因
3.1 自然原因
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的自然原因包括氣象、地質、環境等相關因素。云南省主要遭受自西伯利亞南下寒流與印度洋北上的熱氣流影響,如果西伯利亞干燥的寒冷氣流占據優勢在云南區域內停留,則寒流覆蓋區域內多旱;如果來自于南方的印度洋暖流占據優勢,則其覆蓋區域就會多雨。而印度洋距云南較近,且全省南部地勢較低,地方地勢較高,因此,印度洋北上的暖流幾乎無任何阻擋就能傳至云南省,故而夏天云南省夏季多雨、冬季多旱。一般而言,云南省在農歷5—10月為雨季,11月—次年4月為旱季。同時,由于全省境內復雜多變的溝壑、河谷、山川等地理構造分布不均勻,全省各部氣候也各存差異。結合大氣氣流,造成了云南西、南部多旱,中、北部則多雨。此外,云南省的河流、盆地、河谷眾多,長久以來逐漸形成豐富的水資源與肥沃的土地,有利于農作物栽培,但是也會農作物更容易深受其害。再者,云南省全境90%以上都處于地震活躍帶上,地震頻發,加之各類氣象活動對云南的氣候、環境造成直接而又明顯的影響,由此會引發洪水、澇災、大雪、大風、冰雹、霜凍、地震等農業災害[3]。
3.2 社會原因
在歷史中,人類活動對于自然環境的影響逐漸凸顯,并由此導致農業自然災害更為頻繁地發生。自秦代后,封建王朝對于農民的剝削與壓迫極為嚴重,大多數農民生活艱難,在很多情況下面臨缺糧、疾病、災害等,因此沒有條件去研究農業災害的成因及其防范措施。封建官府不作為、農民的防災、抗災能力不足,加之人們的活動逐漸對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導致云南省歷史上農業災害頻繁且災害的防治力度與效果甚微。但其中最為重要的原因是人類在活動中不斷改造自然、影響自然,使得生態環境逐漸惡化。隨著人口增長,勢必要開荒墾田,由此對生態環境造成惡劣影響,并引發了許多負面后果,農業災害就是其中之一。
自西漢起,封建王朝就開始較大規模地向云南某些地區移民,并令其開荒墾地,在自謀生計的同時向朝廷繳納賦稅。至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兩代,如明朝經歷戰爭后南方人口急劇衰減,“屋無人住,田無人耕”,故統治者展開了浩大的移民行動。云南省的移民規模及頻次逐漸增大。元兵南下云南后,“以屯田守之”,即通過軍隊與百姓大力發展農業生產活動守城,到元代末期,共開墾出農田超過了22 000 hm2;在明代,大量其他省份居民被迫遷至云南,尤其是在洪武十五年至二十一年(1382—1388年),云南省通過軍隊開荒墾田的面積超過了43萬畝,到了明正德五年(1510年)底,軍墾共開辟田地172萬畝,官民開墾田地超過172萬畝。再到天啟年間(1621—1627年),官民開墾田地為699萬畝,軍墾田地118萬畝。到了清朝,云南的開荒墾田活動更為深入,只要是能夠開荒之地,多被開墾,甚至是泄光湖水來開墾田地。從順治元年(1644年)到道光末年(1850年),共開墾田地931余萬畝。清雍正五年(1727年),為了開墾農田,官府組織河流改道,開辟出了1萬多畝田地。大規模的田地開墾不僅破壞了生態環境,也使得大片農田成為農業災害頻發的區域,導致歷史農業災害頻發。
此外,云南礦產資源豐富,自漢代采礦業、冶煉業就開始發展,到了元天歷元年(1328年),云南省的金、銀開采居全國之首;同時云南采鹽業也較為發達,至清中期年產鹽超過500萬 kg。另外,云南省燒炭較晚,燒樹木者甚多,逐漸破壞了生態環境,且破壞程度越來越大,增加了農業災害的發生概率。
4 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的文化及近現代的發展趨勢
4.1 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文化
從諸多相關史料中可以看出,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的語言用句遣詞較為簡單、凝練,如發生干旱就是“旱”、連綿的雨就是“淫雨”,瘟疫的記錄只提及地點、后果等,如上述“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造成這種歷史文化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文言文本身較為簡練;古人對于農業自然災害的記載意識較為籠統,不像人物傳記一樣講明詳細經歷,而只有只言片語;封建時代對于歷史農業災害的文本并不重視,認為農業自然災害只需要提及幾句即可,即使敘述了全部過程也沒有什么較高的歷史人文價值[4]。
(1)伴隨著農業災害對社會的影響范圍、影響程度逐漸增大,史料中對于農業自然災害發生的相關數量的記載越來越多,如“云南48縣被水旱蟲疫等災”,其中尤其注明了農業災害的主要影響范圍為“48縣”。同時,對于疫情的記載大多都不說明疫情的原因與種類,只是用“疫”“大疫”等詞提及。
(2)云南歷史農業災害中災害發生地點是基本的記載內容,而對于災害的延續也多有記載。例如,弘治十二年(1499年),宜良發生地震,“民居盡圮,壓死以萬計,旬月常震,越四年始寧”,即地震頻發的時間連續了四年,地震多發期才逐漸結束。而明、清以后,對于農業災害的種類、內容等記錄才逐步詳細起來。
(3)伴隨著文本史料的發展與地方志修訂得更為頻繁,清代以奏折、題本、地方志等史料載體,其中對農業災害的記載更為詳細,且描述與相關數據呈現得更多,如清順治九年6月初八(1652年),大理蒙化發生地震,“地中若萬馬奔馳,塵霧障天。夜復大雨,雷電交作,民舍盡塌,壓死三千余人。地裂涌出黑水,鰍鱔結聚,不知何來。震時河水俱干,年余乃止”[5]。由此,以“萬馬奔馳”比喻地震浩大的聲勢,并講明了伴隨地震而發的雷電、大雨等天氣,并說明了地震中的死亡人數及地震頻發階段所持續的時間。
(4)對于農業自然災害引起的糧食漲價也在云南農業災害的史料中多有記載,如清嘉慶二十二年(1797年),楚雄地區發生旱災,“旱,大饑,斗米二千四百文”,導致一斗米的價格漲到了2 400文。
4.2 云南省近現代自然災害的發展趨勢
在20世紀前半葉,我國主要處于清末及民國時期,云南歷史農業災害連年頻發,且災害的種類多樣。同時,社會發展對于礦產及鹽類、森林的開采更為頻繁,云南省整體生態環境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由此導致農業災害更為嚴重。例如,姚安縣由于植物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水旱等農業災害更是頻發,“村用騰貴,樵采為艱……征諸近年水旱偏災之發生”,其中“騰貴”即物價飛漲之意[6]。
此外,在這一時期,云南省其他農業災害的發生也明顯加劇,加上20世紀前半葉云南地區氣溫整體較低,導致雪災、風災、霜凍等農業災害多有發生,如1925年(民國時期)3月16日,大理地區發生地震,導致“平地、田壩、湖濱出現裂縫,縫冒沙浮,地涌黑水”,并且造成了4 000漁戶受災,上萬人傷亡,牲畜死亡之數達數千;而在同年的3月23—25日,云南中、東地區有37個縣遭遇了嚴酷的霜凍災害,“霜雹兩災共摧豆麥131萬余千畝”,霜凍災害持續數年,導致人們無所充饑、餓殍遍野,這一時期云南的農業災害及其影響可想而知[7-10]。
1949年至今,新中國成立后開始大力發展民生經濟。生產資料的更高、更多需求以及科技發展,加劇了云南省的生態破壞,農業災害的發生率更高,影響范圍更廣,可以說這是歷史發展規律的必然。伴隨著交通、通訊甚至是當今信息網絡技術、農業的發展,我國對于農業災害的記錄更為完善。而1949年至今,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主要有以下趨勢。
首先,由于生態破壞嚴重,云南省地質災害發生次數最多,并由此引發了更多的農業災害。但隨著農業技術的發展與抗災減災體系的完善,農業災害所造成的人畜傷亡減小,但由于農業的規模化,導致農業經濟損失越來越大。
其次,洪澇災害在小程度上減少,而旱災的發生率有所提高。生態環境的破壞使得云南地區的降水逐漸減少。例如,就曲靖市而言,在20世紀50年代的平均降水天數為270 d,而近年來則為150 d。
最后,進入新世紀以來,云南省旱災更為頻繁,且低溫及冰雹是云南的主要農業災害。2008年年初,中國南方出現了大面積的低溫天氣,給農業帶來了嚴重的損失。再如,2013年5月22日,云南諸多地區發生冰雹,其中石林縣的冰雹瞬間堆積達到6 cm左右,使得當年該地區大量作物絕收。
5 結語
在我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豐富的文本資料,這些文本資料是研究我國歷史,做到以史為鑒的根本所在。從本文的研究中,既能夠得到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頻發且負面影響巨大的事實,也能夠從中梳理出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在史料中的文化記錄化特點。無論是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史料記載,還是云南省歷史農業災害發生的具體情況,都是推動云南省農業災害研究和防治的重要文獻,也是發展歷史記載方式的重要參考。
參考文獻
[1] 郭優來,王羽堅,馬強.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分析農業發展中的問題——以云南邊疆民族地區為例[J].祖國,2017(18):148.
[2] 王振.清代云南移民與農業開發的歷史考察[J].蘭臺世界,2015(9):9–10.
[3] 周瓊.云南歷史災害及其記錄特點[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46(6):17–30.
[4] 劉黎.民族地區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考察——以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為例[J].湖北第二師范學院學報,2014,31(10):34–37.
[5] 吳微微.西南省域地震災害耦合因素分析[J].地震地磁觀測與研究,2014,35(z1):92–96.
[6] 李紅云.1905-1907云南大旱災研究[J].社科縱橫(新理論版),2012,27(4):54–55.
[7] 王明東.清代云南賦稅蠲免初探[J].思想戰線,2010,36(3):131–132.
[8] 楊煜達.清代云南(1711–1911年)的季風氣候與天氣災害[D].上海:復旦大學,2005.
[9] 古永繼.歷史上的云南自然災害考析[J].農業考古,2004(1):233–238.
[10] 陳國生.試論清前期云南農業區域[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6(3):158–172.
責任編輯:黃艷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