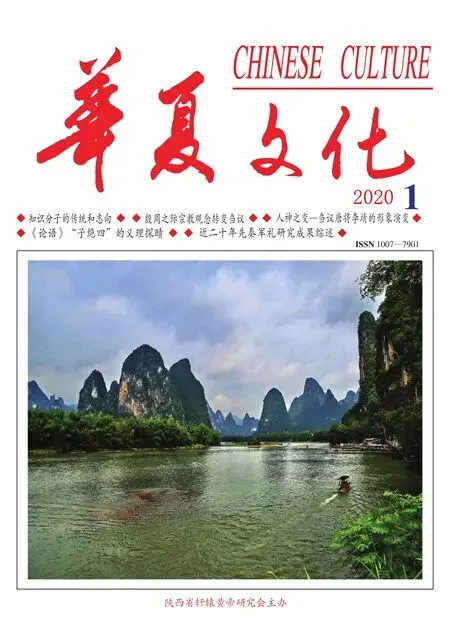《周易》經傳合并體例的取舍及其原因淺探程頤、朱熹為論述重點
——以王弼、
□吳 瑤

《周易》作為六經之首,歷代注書不輟。自秦漢以降,學者泥于象辭,專于術數,至王弼《周易注》,一掃前代繁冗拘迫之風,開創以義理解讀《周易》的先河,并影響此后數千年的《易》學歷史。除了《周易注》本身的內容與解《易》之法,王弼《周易注》本身經傳合并的編排體例亦成為后世主流的《周易》本體例。對此,程頤的《周易程氏傳》與朱熹的《周易本義》卻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前者沿用了《周易注》的四卷本經傳合并體例,而朱熹則力圖恢復十二卷的經傳相分古《易》本。本文著眼于程頤與朱熹對王弼《周易注》經傳合并體例的取舍差異,探究其原由,圍繞三人對《周易》經傳關系的不同理解展開論述。
據考證,最早解釋《易經》的《易傳》大致成書于戰國時期,被漢代經師稱作“十翼”,因此《周易》最初為經、傳相分的十二卷(上經、下經、十翼)體例。宋儒晁說之曾敘述《周易》體例的流變,“《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在漢代以前,《周易》都是以十二篇的體例示人。然而從費直開始,其“長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自此開始專注于以十翼解說《易經》。其后,鄭玄、王弼皆沿襲這種做法,直接將傳的內容并入經文以解釋經義。因此,晁說之認為“古經始變于費氏,而卒大亂于王弼,惜哉!”至孔穎達作《周易正義》,又本于王弼的《周易注》,其大行于唐代,古《易》的體例更不復為人知曉。到宋代,朱熹以呂祖謙所定古《易》本作《周易本義》,以希恢復《周易》古本的體例。然而,朱熹再傳弟子董楷將程頤的《周易程氏傳》與朱熹的《周易本義》合并為一書,但采用的卻是前者的編排體例。及明代永樂年間,胡廣等人編纂《周易大全》,又依循此編排,再次使得古《易》的本來面貌不為人知。
經傳合并或經傳相分的取舍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對經與傳關系的理解。《易傳》是最早詮釋《易經》的著作,又因為出自孔子之手,因此最為學者重視。王弼在其《周易略例·明彖》中言 :“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也……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認為“十翼”之一的《彖》對于理解《易經》有重大的作用,具有觀而思過半之效。對于《乾》卦卦辭,王弼只注“《文言》備矣”,表明其認為《文言》已經全部地解釋了《乾》卦卦辭,自己不必贅言。在《周易略例·略例下》,王弼又言 :“凡《彖》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象》者,各辯一爻之義者也”。認為《彖辭》是言一卦之體,而《象》則各論一爻之義。而王弼的《周易注》正是將《彖辭》拆分放至經文每一卦之后,而將《象辭》分別置于經文每一爻之后。可見,王弼《周易注》的編排正體現出其借用傳文來解釋經文的用心,因此湯用彤先生指出“其注《易》時用傳解經之精神實甚顯著”。由此可見,王弼主要是通過對《彖》《象》《文言》等“十翼”的內容和方法的詮釋去解釋《易經》,這樣的經傳關系的理解影響了他對于《周易》編排體例的完成。
程頤是宋代以義理解讀《周易》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周易程氏傳》在解《易》方法與編排次序上都基本依循王弼,只是在王弼以老莊解《易》上有所批評。程頤在《程氏經說》中言;“圣人有作,則《易》道明矣”,這句話是對孔子“五十以學《易》”的解釋,因此這里的“圣人”是指孔子;程頤認為直至孔子贊《易》,《易》所言之道才得以彰明。可見,在其看來,“十翼”對于闡明《易經》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在對《乾》卦的注解中,程頤有“元亨利貞謂之四德”這樣的表述。“元亨利貞”本是斷一卦之吉兇的占辭,而程頤將其解讀為四德,這實則來源于《文言》的說法“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乾》,元亨利貞”。由是可見,在經傳關系的認識上,程頤同樣認為《易傳》對于理解《易經》有著重要作用,并借助《易傳》來解釋經文。
淳熙九年,朱熹在為呂祖謙《古文周易》所作的跋里提到:
“某嘗以為《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兇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后,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于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
《易》本為卜筮之書的說法,在《朱子語類》中多次出現。朱熹以為,當時治《易》之人,皆諱言《易》為卜筮之書,而以義理為本,這是不識《易》之本義。在《周易本義》乾卦的注釋中,朱熹注六畫為“伏羲所畫之卦也”,“元亨利貞”為“文王所系之辭”,“潛龍勿用”為“周公所系之辭”,“孔子所作之傳十篇”。朱熹認為,《周易》的成書,經過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之作,其所作內容,原自有別。《周易》原本就是卜筮之書,只是孔子贊《易》以后,不再止于卜筮之書,學者不可將其牽合籠統作一并觀,即不可將經、傳混同而觀。
朱熹認為,在分經合傳之后,學者只是根據《傳》來理解經文,只是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而沒有把握經文的全部含義。對于“元亨利貞”,朱熹認為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于守正。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某常疑如此等類,皆是別立說以發明一意。”他認為“元亨利貞”本為占辭,而《易傳》解為四德,并非《易經》本義,而是在此基礎上的發明推說。由此,他批評王弼 :“自晉以來,解經者卻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舍經而自作文。”漢儒雖泥于象術而不通,但尚且依經之本義而演說,王弼則舍棄經文,而自作己說。在此意義上,他也同樣批評程頤說 :“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盡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在經傳關系上,朱熹認為 :“圣經字若個主人,解者猶若奴仆。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仆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經為主人,傳為仆人,因此要以經為主,以傳為輔,他主張“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爻,則自見本旨矣。”,“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系辭》來解”。
由此可見,王弼與程頤因為肯定《易傳》的價值,以及推崇“以傳解經”的詮釋方式,從而采用了經傳合并體例。而朱熹則認為《易傳》所言只是《易經》的面向之一,過分強調“以傳解經”會不識《易》的本義,因此在體例選擇上主張恢復古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