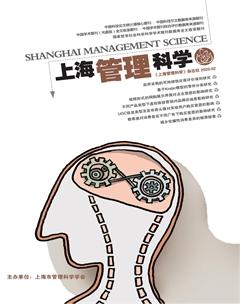新任領(lǐng)導(dǎo)者的消極體驗(yàn)反思與學(xué)習(xí)行為:基于內(nèi)容分析的實(shí)證研究
孔祥年



摘?要:?檢驗(yàn)了個(gè)體反思在新任領(lǐng)導(dǎo)者學(xué)習(xí)過(guò)程中扮演的角色。構(gòu)建以角色認(rèn)同為中介、以培訓(xùn)時(shí)間為調(diào)節(jié)的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同時(shí)控制了個(gè)體主動(dòng)行為作為學(xué)習(xí)的另一種渠道。根據(jù)內(nèi)容分析的方法,對(duì)3322份文本材料進(jìn)行計(jì)算機(jī)自動(dòng)編碼。研究結(jié)果表明:內(nèi)外部消極體驗(yàn)對(duì)個(gè)體反思、個(gè)體主動(dòng)性的影響方向相反,并且強(qiáng)度隨著培訓(xùn)時(shí)間的增加而加強(qiáng);個(gè)體反思、個(gè)體主動(dòng)性與角色認(rèn)同成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角色認(rèn)同對(duì)個(gè)體反思與學(xué)習(xí)行為的關(guān)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內(nèi)部消極體驗(yàn)通過(guò)反思與角色認(rèn)同正向影響學(xué)習(xí)行為。研究結(jié)果闡述了不同性質(zhì)的工作經(jīng)驗(yàn)對(duì)個(gè)體學(xué)習(xí)影響的差異,強(qiáng)調(diào)了個(gè)體反思對(duì)學(xué)習(xí)行為的影響,識(shí)別了角色認(rèn)同在新任領(lǐng)導(dǎo)者學(xué)習(xí)中的作用。
關(guān)鍵詞:?消極體驗(yàn);個(gè)體反思;角色認(rèn)同;學(xué)習(xí)行為
中圖分類號(hào):?F 272.9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Leaders?Reflection upon Negative Experience and Active Learning Behavior
KONG Xiangnian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examines the role of individual reflection in new leaders learning process. We construct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ith the role identity as the mediator and the training time as the moderator ,and treat individual initiative as another source of gathering information. The research collects data from 3322 text material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computer automatic co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negative experience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on individual reflection, and that the influence intensit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raining time. Role identity plays a partial mediate role between individual reflection and learning behavior. Internal negative experience exerts positive effect on learning behavior via reflection and ident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llustrat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field experience on individual learning processes, emphasize the role of individual reflection in learning experience.
Key words: negative experience; individual reflection; role identity; learning behavior
經(jīng)濟(jì)與技術(shù)的發(fā)展在給企業(yè)帶來(lái)變革機(jī)會(huì)的同時(shí),對(duì)企業(yè)領(lǐng)導(dǎo)者提出了新的技能需求。在職工作經(jīng)驗(yàn)相對(duì)于正式培訓(xùn)項(xiàng)目,是領(lǐng)導(dǎo)者開發(fā)個(gè)人技能、獲取領(lǐng)導(dǎo)力提升最重要的來(lái)源(Seibert等,2017)。
挑戰(zhàn)性經(jīng)歷會(huì)促進(jìn)領(lǐng)導(dǎo)者彌補(bǔ)知識(shí)儲(chǔ)備中缺少的適用于新情景的信息(曹春輝等,2012)。領(lǐng)導(dǎo)者的經(jīng)歷是判斷他對(duì)未來(lái)角色的準(zhǔn)備情況的重要因素。Ashford和DeRuhe(2012)認(rèn)為反思是實(shí)踐的集合,可以幫助領(lǐng)導(dǎo)者關(guān)注他們的能力發(fā)展與任務(wù)的完成,并從經(jīng)歷中學(xué)到更多。已有研究回答了反思是從經(jīng)驗(yàn)中學(xué)習(xí)知識(shí)的渠道,本研究提出第一個(gè)問題,不同性質(zhì)的工作經(jīng)驗(yàn)與反思的關(guān)系是否存在差異,新任領(lǐng)導(dǎo)者的學(xué)習(xí)過(guò)程是否存在不同。
從經(jīng)驗(yàn)向?qū)W習(xí)轉(zhuǎn)化的機(jī)制的研究仍停留在理論層面。Mann等(2009)在回顧這方面研究時(shí)指出:“關(guān)于反思的一個(gè)關(guān)鍵假設(shè)就是它可以提升能力……但至今我們并沒有證據(jù)支持或拒絕該假設(shè)。”本研究提出第二個(gè)問題,個(gè)體是否可以通過(guò)反思促進(jìn)自己的學(xué)習(xí)行為?
數(shù)據(jù)獲取是以上研究面臨的一個(gè)主要困難,因?yàn)閭€(gè)體反思往往發(fā)生在工作情景中消極事件的應(yīng)對(duì)過(guò)程中,問卷調(diào)查很難事后反映出當(dāng)時(shí)的事件場(chǎng)景和情緒體驗(yàn)。為此,我們采取情景導(dǎo)向內(nèi)容分析方法。我們的研究情景是王品集團(tuán)的“幼獅計(jì)劃”,“幼獅”是企業(yè)從大學(xué)招聘的應(yīng)屆生,通過(guò)6個(gè)月的在職培訓(xùn)將成為企業(yè)旗下餐飲門店(副)店長(zhǎng)。
1?文獻(xiàn)綜述與研究假設(shè)
1.1?消極體驗(yàn)與個(gè)體反思
個(gè)體反思是一種認(rèn)知過(guò)程,通過(guò)對(duì)自己想法、感覺與行為的檢查與評(píng)價(jià),個(gè)體嘗試增加他們對(duì)具體經(jīng)驗(yàn)的理解(Stein和Grant,2014)。反思開始于挑戰(zhàn)性經(jīng)歷的刺激,挑戰(zhàn)會(huì)帶來(lái)處理問題時(shí)的困惑,個(gè)體接收到的反饋與預(yù)期不符時(shí)會(huì)促進(jìn)反思(Daudelin,1996)。工作挑戰(zhàn)會(huì)激發(fā)學(xué)習(xí)動(dòng)力與興趣,但也會(huì)產(chǎn)生與任務(wù)不確定性和失敗有關(guān)的消極情緒。消極情緒反應(yīng)會(huì)影響反思的過(guò)程,情緒反應(yīng)是短暫但又相對(duì)強(qiáng)烈的,會(huì)限制個(gè)體對(duì)反思的投入,有可能打斷思考過(guò)程(Inzlicht等,2014)。
認(rèn)知心理學(xué)認(rèn)為個(gè)體存在雙系統(tǒng)認(rèn)知加工系統(tǒng):直覺加工與反思加工。直覺是一種自發(fā)、無(wú)意識(shí)、幾乎獨(dú)立于認(rèn)知資源的認(rèn)知加工,該種加工占優(yōu)時(shí),個(gè)體不依賴于邏輯思考,根據(jù)過(guò)往經(jīng)驗(yàn)形成的認(rèn)知框架進(jìn)行決策。反思加工需要投入認(rèn)知資源,進(jìn)行理性思考,去克制或者推翻根據(jù)直覺做出的反應(yīng)(Beevers,2005)。直覺加工是默認(rèn)的認(rèn)知加工系統(tǒng),只有當(dāng)個(gè)體的認(rèn)知框架無(wú)法解釋工作中的反常事件時(shí)反思才會(huì)出現(xiàn),這與挑戰(zhàn)性經(jīng)歷促進(jìn)個(gè)體反思的結(jié)論是一致的。個(gè)體面臨挑戰(zhàn)與壓力時(shí)會(huì)激活消極情緒,分散認(rèn)知資源,將認(rèn)知資源用于關(guān)注業(yè)績(jī)與評(píng)價(jià)的不利后果而產(chǎn)生的消極情緒中,挑戰(zhàn)性經(jīng)歷引起的認(rèn)知沖突與消極情緒之間會(huì)產(chǎn)生認(rèn)知資源的競(jìng)爭(zhēng)(Lavric等,2003)。
具體經(jīng)歷喚起反思需要個(gè)體感知到挑戰(zhàn)性刺激并且擁有足夠可用的認(rèn)知資源,因此挑戰(zhàn)性經(jīng)歷對(duì)反思的影響不是單一的促進(jìn)或削弱。一方面,它可以幫助個(gè)體反思,獲取新的認(rèn)知框架;另一方面,挑戰(zhàn)性的環(huán)境線索會(huì)激活個(gè)體的消極情緒、占用認(rèn)知資源、壓制反思的發(fā)生。為了分析不同的挑戰(zhàn)性經(jīng)歷是否存在著特異性作用,Dragoni等(2011)從四十種領(lǐng)導(dǎo)者活動(dòng)中抽象出貢獻(xiàn)者、管理者與戰(zhàn)略領(lǐng)導(dǎo)者等三個(gè)角色反映領(lǐng)導(dǎo)者的涉入度。三個(gè)角色領(lǐng)導(dǎo)者的涉入度依次增加,涉入程度越高,領(lǐng)導(dǎo)者積累的經(jīng)驗(yàn)就越豐富。我們參照Dragoni(2011)等的方法,對(duì)“幼獅”培訓(xùn)期間涉及的工作崗位(比如道長(zhǎng)、區(qū)控、值班)與職責(zé)進(jìn)行分析,將“幼獅”的工作挑戰(zhàn)分為兩方面:一方面他們需要在與餐飲顧客的接觸中成長(zhǎng)起來(lái)(在本文中稱為“外部挑戰(zhàn)”),另一方面他們要學(xué)會(huì)如何更好地與店鋪其他角色的同人有效共事(稱為“內(nèi)部挑戰(zhàn)”)。前者只涉及貢獻(xiàn)者這一個(gè)角色,后者涉及貢獻(xiàn)者、管理者、戰(zhàn)略領(lǐng)導(dǎo)者等多種角色。內(nèi)部挑戰(zhàn)所涉及角色與責(zé)任的廣度和深度均高于外部挑戰(zhàn)。
在餐飲服務(wù)企業(yè),顧客的不公平行為、口頭攻擊、超出服務(wù)范圍的要求等是誘發(fā)服務(wù)人員消極情緒的主要工作事件(張秀娟等,2008)。對(duì)于顧客的不公平行為,服務(wù)人員不能直接應(yīng)對(duì),只能壓抑自己的真實(shí)情緒。他們不僅關(guān)注內(nèi)心感受,而且消耗認(rèn)知資源用于遵守外部情緒表達(dá)規(guī)則。相比較于和上下級(jí)、同事的公平交往問題,顧客的不公平行為引發(fā)的消極情緒反應(yīng)更加強(qiáng)烈(Grandey等,2004)。
為了研究挑戰(zhàn)性經(jīng)歷對(duì)個(gè)體反思正反兩方面的效應(yīng),我們考慮了挑戰(zhàn)經(jīng)歷激活的個(gè)體消極情緒,本研究將出現(xiàn)消極情緒的外部或內(nèi)部挑戰(zhàn)經(jīng)歷稱為外部或內(nèi)部消極體驗(yàn)。反思需要的認(rèn)知資源與輸入信息的強(qiáng)度和關(guān)注度正相關(guān),因此內(nèi)部挑戰(zhàn)帶來(lái)的認(rèn)知沖突刺激相較于外部挑戰(zhàn)需要更多的認(rèn)知資源,對(duì)工作投入度更高,更可能在與消極情緒的認(rèn)知資源競(jìng)爭(zhēng)中占優(yōu)。
H1:內(nèi)部消極體驗(yàn)與個(gè)體反思成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外部消極體驗(yàn)與個(gè)體反思成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
1.2?培訓(xùn)時(shí)間的調(diào)節(jié)作用
個(gè)體面臨新的或未識(shí)別的復(fù)雜問題時(shí)會(huì)感到驚奇,驚奇感與個(gè)體反思正相關(guān),對(duì)特定領(lǐng)域的驚奇感會(huì)隨著經(jīng)驗(yàn)的增加而減弱(Mamede,2004)。驚奇感使得個(gè)體對(duì)自己的表現(xiàn)產(chǎn)生懷疑,進(jìn)而尋求反饋。當(dāng)環(huán)境中引起關(guān)注的刺激無(wú)法被已有的認(rèn)知框架解釋時(shí),個(gè)體進(jìn)行反思并嘗試更新認(rèn)知框架;當(dāng)從經(jīng)驗(yàn)發(fā)展而來(lái)的認(rèn)知框架可以被重新利用時(shí),惰性產(chǎn)生,即基本上滿足于當(dāng)前做事方式的結(jié)果,傾向于缺乏對(duì)新框架的關(guān)注(Huff等,1992)。
外部經(jīng)歷主要發(fā)生在日常性的場(chǎng)景,工作的復(fù)雜度不會(huì)隨著時(shí)間發(fā)生變化。多次面對(duì)重復(fù)的任務(wù)增加了實(shí)踐次數(shù),提高了掌握關(guān)鍵技能的可能性,最終形成可用于直覺加工的認(rèn)知框架。同時(shí)在外部挑戰(zhàn)性情景中,認(rèn)知資源更可能被分配于消極情緒而非反思顧客抱怨反映出的問題。比如“幼獅”在培訓(xùn)過(guò)半時(shí)記錄的顧客抱怨場(chǎng)景,“大家都認(rèn)為做得還不錯(cuò)的一天卻收到了門店一年來(lái)首通投訴,其實(shí)那桌客人晚上已經(jīng)有人專門處理過(guò)客戶抱怨”。內(nèi)部經(jīng)歷帶來(lái)的刺激體驗(yàn)會(huì)隨著培訓(xùn)進(jìn)行而增加,培訓(xùn)過(guò)程中輪崗擴(kuò)展了陌生領(lǐng)域的范圍,并且“幼獅”逐漸扮演管理者與領(lǐng)導(dǎo)者的角色,承擔(dān)的責(zé)任程度在逐漸增加;“幼獅”與不同角色的同人共事,對(duì)工作中的非標(biāo)準(zhǔn)行為的形成與影響了解也會(huì)更加全面。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shè):
H2:時(shí)間會(huì)加強(qiáng)消極體驗(yàn)與個(gè)體反思的相關(guān)關(guān)系,即隨著培訓(xùn)的進(jìn)行,外部(內(nèi)部)消極體驗(yàn)與個(gè)體反思的負(fù)(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越來(lái)越強(qiáng)。
1.3?個(gè)體主動(dòng)性與個(gè)體反思
個(gè)體主動(dòng)性是指?jìng)€(gè)體積極地、自我驅(qū)動(dòng)地,為完成任務(wù)、達(dá)成目標(biāo)、克服困難而持續(xù)地實(shí)施前攝行為(Ellis等,1997)。個(gè)體通過(guò)反思獲取反饋可以促進(jìn)自我學(xué)習(xí),頓悟不同工作情景下的合適行為。在這個(gè)角度,個(gè)體反思可以被概念化為產(chǎn)生知識(shí)的內(nèi)部導(dǎo)向策略(Ashford等,2016),與從其他人處獲取信息、尋求反饋的外部導(dǎo)向的信息收集策略,即個(gè)體主動(dòng)性相對(duì)。無(wú)論是內(nèi)部還是外部導(dǎo)向的信息獲取策略,個(gè)體的目的都是更好地理解所處的情景。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shè):
H3:內(nèi)(外)部消極體驗(yàn)與個(gè)體主動(dòng)性成正(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并隨培訓(xùn)時(shí)間而增加。
1.4?個(gè)體反思與學(xué)習(xí)行為
學(xué)習(xí)行為是指?jìng)€(gè)人不斷獲取知識(shí)、改善行為,以在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中使自己保持良好生存和健康和諧發(fā)展(陳國(guó)權(quán),2008)。該概念包括學(xué)習(xí)的行動(dòng)與內(nèi)容兩方面內(nèi)容,目的在于個(gè)體能力的持久改變。“幼獅”每周培訓(xùn)的目的是將獲取的認(rèn)知框架自動(dòng)化或發(fā)展新的認(rèn)知框架,前者是通過(guò)相同職責(zé)的重復(fù)形成的,后者則是通過(guò)接觸新任務(wù)或相同任務(wù)的不同層次角色與責(zé)任獲取的。個(gè)體對(duì)挑戰(zhàn)性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反思時(shí),通過(guò)提取與已有認(rèn)知框架矛盾的信息,會(huì)促進(jìn)知識(shí)結(jié)構(gòu)的成長(zhǎng),完善認(rèn)知框架(Handy和Polimeni,2017)。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shè):
H4:個(gè)體反思與學(xué)習(xí)行為成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
1.5?角色認(rèn)同的中介效應(yīng)
角色認(rèn)同是個(gè)體根據(jù)其在組織、社會(huì)中的位置或者通過(guò)社會(huì)互動(dòng),對(duì)擁有的角色所具備特質(zhì)的描述(Brown,2015),它主要回答“我是誰(shuí)”“我應(yīng)該怎么做”等問題。新任領(lǐng)導(dǎo)者進(jìn)入組織后往往角色不清晰,反思能夠有助于其產(chǎn)生自我頓悟,幫助領(lǐng)導(dǎo)者完成角色認(rèn)同(Stein等,2014)。頓悟是對(duì)自己想法、感覺與行為的理解。個(gè)體反思工作經(jīng)歷,對(duì)“我是誰(shuí)”“我應(yīng)該怎么做”等問題產(chǎn)生頓悟,即領(lǐng)導(dǎo)者通過(guò)反思獲取內(nèi)部反饋,建立認(rèn)同標(biāo)準(zhǔn)學(xué)習(xí)角色所必需的技能,建立其對(duì)工作角色的認(rèn)同。
角色認(rèn)同可以促進(jìn)學(xué)習(xí)行為。個(gè)體行為與角色要求不一致、與群體不一致,會(huì)使個(gè)體持續(xù)調(diào)整行為以符合角色期望。“幼獅”發(fā)展角色認(rèn)同的過(guò)程也是學(xué)習(xí)領(lǐng)導(dǎo)技能的過(guò)程。行為調(diào)整過(guò)程會(huì)對(duì)幼獅本科期間形成的認(rèn)知框架產(chǎn)生挑戰(zhàn),當(dāng)領(lǐng)導(dǎo)者被迫去批判性地評(píng)價(jià)他們的認(rèn)知框架時(shí),相較于只對(duì)具體問題被動(dòng)反應(yīng),他們更可能學(xué)會(huì)面對(duì)挑戰(zhàn)的新方法(Breevaart,2016)。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shè):
H5:個(gè)體反思與角色認(rèn)同成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
H6:個(gè)體反思與學(xué)習(xí)行為的正向關(guān)系被角色認(rèn)同部分中介。圖1列示了本研究的理論模型。
2?研究情景與數(shù)據(jù)來(lái)源
本文的研究情景是王品集團(tuán)的“幼獅計(jì)劃”。王品集團(tuán)是總部位于中國(guó)臺(tái)灣的大型餐飲連鎖企業(yè),“幼獅計(jì)劃”分為“5天魔鬼訓(xùn)練”與“6個(gè)月正式訓(xùn)練”兩個(gè)階段。第一階段為集訓(xùn),以介紹王品文化,建立餐飲服務(wù)意識(shí)為主;第二階段為在職培訓(xùn),“幼獅”5~6人一組被分配到不同的餐飲門店進(jìn)行基礎(chǔ)工作站、特殊工作站、營(yíng)運(yùn)管理的輪崗實(shí)踐,并通過(guò)課室訓(xùn)練學(xué)習(xí)理論知識(shí)。培訓(xùn)結(jié)束后,“幼獅”根據(jù)考核成績(jī)可以被直接任命為主任、副店長(zhǎng)(正常晉升副店長(zhǎng)需要5年以上)。
在本研究涵蓋的時(shí)間區(qū)間“幼獅”沒有正式入職店長(zhǎng),但是該群體可以作為新任領(lǐng)導(dǎo)者研究的對(duì)象,主要基于三點(diǎn)原因。首先,“幼獅”進(jìn)入店鋪后扮演領(lǐng)導(dǎo)者相關(guān)角色,比如道長(zhǎng)需要連接服務(wù)外場(chǎng)與廚房?jī)?nèi)場(chǎng),協(xié)調(diào)內(nèi)外場(chǎng)的服務(wù)同人,區(qū)控需要維持控場(chǎng)節(jié)奏,值班作為全場(chǎng)指揮,需要將人用好。其次,從培訓(xùn)考核來(lái)看,“幼獅”在培訓(xùn)期初、期中與期末需要進(jìn)行考核并達(dá)到85分以上。評(píng)分中團(tuán)隊(duì)協(xié)調(diào)能力、領(lǐng)導(dǎo)者角色擔(dān)當(dāng)?shù)戎笜?biāo)占到50%以上的比重,訓(xùn)練師每周都會(huì)對(duì)“幼獅”的領(lǐng)導(dǎo)能力、規(guī)劃能力、溝通能力、協(xié)調(diào)能力、主動(dòng)性等方面進(jìn)行打分,“幼獅”為通過(guò)測(cè)試必須提高團(tuán)隊(duì)管理、情緒管理等領(lǐng)導(dǎo)者勝任能力。最后,根據(jù)對(duì)“幼獅”學(xué)習(xí)心得的分析,培訓(xùn)過(guò)程中“幼獅”離開或被淘汰的原因主要包括團(tuán)隊(duì)內(nèi)人際關(guān)系不和諧、與下級(jí)沖突處理不當(dāng)、顧客關(guān)系處理能力存在缺陷、無(wú)法完成領(lǐng)導(dǎo)者的角色構(gòu)建、不認(rèn)同王品集團(tuán)價(jià)值觀等。這些原因反映了退出“幼獅”在領(lǐng)導(dǎo)能力、溝通協(xié)調(diào)、團(tuán)隊(duì)建設(shè)、專業(yè)知識(shí)等方面存在的領(lǐng)導(dǎo)者勝任力缺乏問題。
本文以“幼獅”的學(xué)習(xí)心得與訓(xùn)練師評(píng)價(jià)作為數(shù)據(jù)來(lái)源。每位“幼獅”被要求在每周(第二期為每?jī)芍埽懸黄獙W(xué)習(xí)心得,回顧一周的培訓(xùn)內(nèi)容與感想。學(xué)習(xí)心得內(nèi)容中中涉及的場(chǎng)景包括工作站實(shí)習(xí)、營(yíng)運(yùn)實(shí)習(xí)、課室訓(xùn)練等,各主題占比分別為51.12%、14.84%和34.03%。場(chǎng)景中互動(dòng)的人物包括顧客、下級(jí)同人、領(lǐng)導(dǎo)、小組成員等,各角色關(guān)鍵詞占比分別為16.95%、17.07%、12.62%、23.28%等。表1是學(xué)習(xí)心得在各期的分布,共計(jì)3322份。每期中均存在中途退出的參與者,他們的周報(bào)數(shù)量要小于最大周報(bào)數(shù)。所有“幼獅”都具有本科學(xué)歷,其中男性“幼獅”120人(41%),女性“幼獅”173人(59%)。
3?研究方法
3.1?詞典構(gòu)建
內(nèi)容分析將從特定目的的詞典開發(fā)中受益。演繹式的詞典開發(fā)方法是通過(guò)對(duì)相關(guān)主題的高被引文章的詳盡搜索,識(shí)別出反映研究變量的詞語(yǔ)。歸納式的詞典開發(fā)方法是從選定的文本中識(shí)別高頻詞語(yǔ)進(jìn)行歸類,并給出該類詞組所反映變量的概念化定義。因?yàn)閭€(gè)體反思的影響因素以及相應(yīng)結(jié)果變量的研究較少且實(shí)證結(jié)果存在矛盾,演繹式的詞典開發(fā)無(wú)法獲取完備的詞典,所以本研究采取演繹與歸納相結(jié)合的詞典開發(fā)方法。
3.2?演繹式詞典開發(fā)
我們?cè)诘谝徊交仡櫫诉^(guò)去30年發(fā)表在頂級(jí)管理學(xué)期刊上的9篇經(jīng)驗(yàn)學(xué)習(xí)文獻(xiàn),10篇自我反思的文獻(xiàn)、9篇團(tuán)隊(duì)反思的文獻(xiàn),識(shí)別出挑戰(zhàn)性經(jīng)驗(yàn)特征、情緒、反思標(biāo)志等9個(gè)詞典。當(dāng)變量從已有文獻(xiàn)中被識(shí)別出來(lái)之后,由3名研究者獨(dú)立使用Nvivio 11軟件Word格式的學(xué)習(xí)心得進(jìn)行編碼,為詞典開發(fā)下級(jí)類目并識(shí)別詞語(yǔ),類目對(duì)應(yīng)文獻(xiàn)中變量的不同緯度。當(dāng)從文獻(xiàn)中不能識(shí)別出新的詞語(yǔ)后,我們停止了獨(dú)立工作。
第二步,統(tǒng)一詞典結(jié)果與詞語(yǔ)列表。研究者對(duì)各自詞典比對(duì)分析,合并相似的標(biāo)簽,不一致的地方進(jìn)行充分討論形成統(tǒng)一認(rèn)識(shí)。詞語(yǔ)列表的確定則由1名研究者提出觀點(diǎn),另外2名支持或者辯駁,不斷修正與補(bǔ)充,最后我們得到101個(gè)詞語(yǔ)。第三步,咨詢外部專家編碼。根據(jù)Short等(2010)的建議,內(nèi)容的有效性包括專家對(duì)變量測(cè)量的評(píng)估。為了保證編碼表的表面效度,我們向?qū)<覍で蠓答佉源_保我們對(duì)反思、場(chǎng)景與主動(dòng)行為等變量的類目得到理論支持。第四步,預(yù)編碼。隨機(jī)抽取100份文本進(jìn)行預(yù)編碼,主要檢驗(yàn)詞典是否能夠涵蓋主要的研究?jī)?nèi)容,是否存在未被識(shí)別的類目。
3.3?歸納式詞典開發(fā)
完成演繹式詞典開發(fā)后,我們進(jìn)行了歸納式詞典開發(fā)以補(bǔ)充演繹分析的結(jié)果。第一步,對(duì)文本材料進(jìn)行分詞。我們使用R的“Rwordseg”庫(kù)進(jìn)行分詞,并載入哈工大停用詞表刪除這類與研究不相關(guān)的詞語(yǔ)。分詞后,我們得到20275個(gè)詞組。
第二步,確定高頻詞語(yǔ)。已有的內(nèi)容分析的研究對(duì)高頻詞語(yǔ)的確定通常采用的是基于不同研究情景的經(jīng)驗(yàn)值,比如Short等(2010)基于管理者致股東的信構(gòu)建的創(chuàng)業(yè)導(dǎo)向詞典將被提到3次以上的詞語(yǔ)作為高頻詞語(yǔ);Abrahamson和Park(1994)研究管理者隱藏消極組織結(jié)果的動(dòng)機(jī)時(shí),以30次作為高頻詞語(yǔ)的篩選標(biāo)準(zhǔn)。考慮到詞語(yǔ)重要性與詞典豐富性,我們決定選取詞頻數(shù)的前20%(頻數(shù)大于等于11)的詞語(yǔ)作為高頻詞語(yǔ),共計(jì)3864個(gè)。
第三步,詞典迭代。邀請(qǐng)熟悉研究?jī)?nèi)容與背景的專家對(duì)詞語(yǔ)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以確定是否與研究主題相關(guān),同時(shí)由三位研究者各自獨(dú)立對(duì)詞語(yǔ)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移除詞義模糊不清或者明顯與研究主題不相關(guān)的詞語(yǔ)后,專家保留了652個(gè)詞語(yǔ);3位研究者比較各自的詞語(yǔ),并交流分類的依據(jù)。這是一個(gè)反復(fù)迭代的過(guò)程,持續(xù)5個(gè)月,最終得到分類一致的詞語(yǔ)989個(gè)。考慮到后續(xù)計(jì)算機(jī)編碼對(duì)詞語(yǔ)的檢索過(guò)程,我們對(duì)形式存在包含關(guān)系的詞語(yǔ)進(jìn)行合并或者進(jìn)行英文替換,比如“意識(shí)”與“意識(shí)到”,將“意識(shí)到”替換為“Realize”。
第四步,驗(yàn)證詞典的信度與效度。為了計(jì)算上述詞語(yǔ)分類的信度,本研究邀請(qǐng)另外3位沒有參與前階段詞典開發(fā)工作的研究助理判斷各變量及類目下的詞語(yǔ)是否符合定義。表2報(bào)告了反映兩兩之間分類一致性的Kappa系數(shù)均值為0.889,故詞典具有良好的信度。內(nèi)容分析更多依賴表面效度,本研究邀請(qǐng)外部專家、3位研究者獨(dú)立確定變量及詞語(yǔ)歸類,并進(jìn)行詞典反復(fù)迭代以提高詞典的表面效度。
3.4?變量定義
本研究中主要變量的定義在文獻(xiàn)綜述與研究假設(shè)部分已經(jīng)給出,變量測(cè)量如下。
3.4.1?內(nèi)生潛變量
(1)外部消極體驗(yàn)(EX)。本研究情緒類型的劃分參照Russel(2003),將激活的消極情緒定義為消極體驗(yàn)。通過(guò)Stata篩選出同時(shí)包含顧客(如消費(fèi)者、顧客、客人、貴賓、散客)與消極情緒的場(chǎng)景,對(duì)場(chǎng)景所在段落進(jìn)行編碼。如果場(chǎng)景跨越多個(gè)段落,對(duì)這些段落均進(jìn)行上述篩選。如果該段落沒有出現(xiàn)場(chǎng)景詞語(yǔ),則在數(shù)據(jù)分析階段刪除該觀察值。
(2)內(nèi)部消極體驗(yàn)(IN)。通過(guò)Stata篩選出同時(shí)包含職能角色(如道長(zhǎng)、區(qū)控、主管等)與消極情緒的場(chǎng)景,對(duì)場(chǎng)景所在段落進(jìn)行編碼。如果段落中同時(shí)出現(xiàn)顧客與職能角色,則對(duì)(1)、(2)均進(jìn)行編碼。
3.4.2?外源潛變量
(1)個(gè)體反思(PR)。包括能力需要(如態(tài)度、素質(zhì)、度量)與工作價(jià)值觀(如事業(yè)、回報(bào)、成就)兩個(gè)類目。
(2)個(gè)體主動(dòng)性(PI)。來(lái)自訓(xùn)練師每周對(duì)“幼獅”的評(píng)分,包括學(xué)習(xí)精神、進(jìn)取精神、主動(dòng)性。
(3)角色認(rèn)同(RI)。包括工作關(guān)系(如領(lǐng)導(dǎo)力、角色、分工)與團(tuán)隊(duì)氛圍(如團(tuán)體、配合、一家人)兩個(gè)類目。
(4)學(xué)習(xí)行為(LB)。包括學(xué)習(xí)行動(dòng)(如實(shí)踐、磨煉、嘗試)與學(xué)習(xí)內(nèi)容(如數(shù)據(jù)、成本、步驟)兩個(gè)類目。
3.4.3?調(diào)節(jié)變量
培訓(xùn)時(shí)間(TIME)。按照各期周報(bào)的序數(shù)順序取值。
3.5?數(shù)據(jù)分析
本研究基于上述詞典采用Stata 14對(duì)txt(UTF-8編碼)格式的周報(bào)進(jìn)行自動(dòng)編碼。編碼過(guò)程以段落作為消極體驗(yàn)的分析單位,所有的報(bào)告被分解為段落,保留特定標(biāo)識(shí)以識(shí)別它們的來(lái)源。以句為單位進(jìn)行邏輯判斷,比如使用否定詞調(diào)整消極情緒的意義時(shí),先在句子中搜索表示消極情緒的詞,若有,則進(jìn)一步判斷該句中有無(wú)否定詞。編碼完畢后由3位研究者隨機(jī)選擇30份報(bào)告檢驗(yàn)編碼的準(zhǔn)確性。在數(shù)據(jù)清理階段,內(nèi)容少于30個(gè)中文字的段落被刪除,初始數(shù)據(jù)庫(kù)包括22016個(gè)觀測(cè)值。本研究將段落層面的編碼數(shù)據(jù)聚合到周報(bào)層面,并根據(jù)周報(bào)的段落數(shù)進(jìn)行標(biāo)準(zhǔn)化;訓(xùn)練師評(píng)價(jià)的數(shù)據(jù)與編碼后的周報(bào)數(shù)據(jù)按照“幼獅”/周進(jìn)行匹配,得到研究所用數(shù)據(jù)庫(kù);本研究采用Mplus 7對(duì)理論模型進(jìn)行檢驗(yàn)。
4?研究結(jié)果
4.1?驗(yàn)證性因子分析
為了保證詞典測(cè)量的效度,本研究對(duì)關(guān)鍵變量進(jìn)行驗(yàn)證性因素分析,通過(guò)對(duì)比6因子模型及其他模型,檢驗(yàn)內(nèi)外部消極體驗(yàn)、個(gè)體反思、個(gè)體主動(dòng)性、角色認(rèn)同與學(xué)習(xí)行為之間的效度。通過(guò)對(duì)6個(gè)模型的比較(表4),發(fā)現(xiàn)6因子模型擬合效果最好,χ2(50)=146.980,RMSEA=0.026,CFI=0.989,NFI=0.983,CFI和NFI均大于0.9,PMSEA、SRMR小于0.08,表明本研究的6個(gè)變量之間區(qū)分效度良好。
4.2?描述性統(tǒng)計(jì)
表5是對(duì)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jì)。內(nèi)部消極體驗(yàn)與個(gè)體反思、個(gè)體主動(dòng)性(r=0.122,p<0.01;r=0.044,p<0.01),個(gè)體反思與角色認(rèn)同、學(xué)習(xí)行為(r=0.167,p<0.01;r=0.286,p<0.01),個(gè)體主動(dòng)性與角色認(rèn)同(r=0.084,p<0.01),角色認(rèn)同與學(xué)習(xí)行為(r=0.247,p<0.01)均呈顯著正相關(guān),與研究假設(shè)一致。
4.3?假設(shè)檢驗(yàn)
將培訓(xùn)時(shí)間作為調(diào)節(jié)項(xiàng)之后,模型擬合結(jié)果如下:χ2=765.669,df=91,CFI=0.956,NFI=0.934,SRMR=0.032,RMSEA=0.051。模型的直接效應(yīng)、調(diào)節(jié)效應(yīng)與間接效應(yīng)的結(jié)果如表6所示。
內(nèi)部消極體驗(yàn)與個(gè)體反思(β=0.798,p<0.01)和個(gè)體主動(dòng)性顯著正相關(guān)(β=2.282,p<0.01);外部消極體驗(yàn)與個(gè)體反思(β=-0.369,p<0.05)和個(gè)體主動(dòng)性(β=-1.474,p<0.01)顯著負(fù)相關(guān)。隨著培訓(xùn)時(shí)間的增加,每個(gè)學(xué)習(xí)心得周期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平均增加0.032(p<0.01)、0.100(p<0.01),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每個(gè)學(xué)習(xí)心得周期平均增加-0.044(p<0.01)、-0.111(p<0.01),假設(shè)1、2、3得證。角色認(rèn)同與個(gè)體反思、個(gè)體主動(dòng)性顯著正相關(guān),路徑系數(shù)分別為0.584(p<0.01)、0.045(p<0.05),假設(shè)5得證。在控制了角色認(rèn)同后,個(gè)體反思與學(xué)習(xí)行為的直接效應(yīng)為0.534(p<0.01),結(jié)果仍然顯著,角色認(rèn)同對(duì)個(gè)體反思與學(xué)習(xí)行為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設(shè)4得證。根據(jù)Bootstrap結(jié)果可知,個(gè)體反思通過(guò)角色認(rèn)同對(duì)學(xué)習(xí)行為的間接效應(yīng)為0.073(p<0.01),95%置信區(qū)間為(0.041,0.123),區(qū)間不包含0,即角色認(rèn)同的中介作用顯著,假設(shè)6得證。進(jìn)一步,根據(jù)連續(xù)中介的結(jié)果,內(nèi)部消極體驗(yàn)通過(guò)個(gè)體反思和角色認(rèn)同正向影響學(xué)習(xí)行為(β=0.028,p<0.01),外部消極體驗(yàn)對(duì)學(xué)習(xí)行為沒有顯著影響。
5?研究結(jié)論與局限
本文從餐飲服務(wù)業(yè)新任領(lǐng)導(dǎo)者的視角研究了內(nèi)外部消極體驗(yàn)反思與學(xué)習(xí)行為的關(guān)系。實(shí)證結(jié)果支持了內(nèi)外部消極體驗(yàn)對(duì)個(gè)體反思、個(gè)體主動(dòng)性影響方向相反,并且影響強(qiáng)度隨著培訓(xùn)時(shí)間加強(qiáng)。此外,實(shí)證結(jié)果還支持了個(gè)體反思、個(gè)體主動(dòng)性對(duì)角色認(rèn)同的正向影響,角色認(rèn)同對(duì)個(gè)體反思與學(xué)習(xí)行為的正向關(guān)系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在領(lǐng)導(dǎo)力開發(fā)和反思學(xué)習(xí)方面有如下啟示:
首先,本文區(qū)分了內(nèi)部挑戰(zhàn)與外部挑戰(zhàn),從認(rèn)知資源的角度,內(nèi)部挑戰(zhàn)包含的角色、責(zé)任層次比外部挑戰(zhàn)更加豐富,所需要處理的情緒反應(yīng)較少,在與消極情緒的認(rèn)知資源競(jìng)爭(zhēng)中占優(yōu),而外部挑戰(zhàn)則在與認(rèn)知資源競(jìng)爭(zhēng)中處于劣勢(shì)。實(shí)證結(jié)果反映了內(nèi)部挑戰(zhàn)會(huì)激發(fā)“幼獅”反思認(rèn)知加工過(guò)程,促進(jìn)領(lǐng)導(dǎo)者學(xué)習(xí)行為的產(chǎn)生。外部挑戰(zhàn)會(huì)抑制“幼獅”的反思出現(xiàn),沒有發(fā)現(xiàn)對(duì)學(xué)習(xí)行為有顯著作用。
其次,我們發(fā)現(xiàn)新任領(lǐng)導(dǎo)者在培訓(xùn)過(guò)程中完成角色認(rèn)同。“幼獅”進(jìn)入店鋪之前沒有餐飲服務(wù)業(yè)相關(guān)的領(lǐng)導(dǎo)經(jīng)歷,進(jìn)入店鋪后需要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培訓(xùn)中承擔(dān)道長(zhǎng)、區(qū)控、領(lǐng)班等職責(zé)的經(jīng)歷突出了“幼獅”現(xiàn)有技能集合與領(lǐng)導(dǎo)角色要求的技能集的缺口,為“幼獅”學(xué)習(xí)與發(fā)展提供了多源頭的動(dòng)力。隨著角色認(rèn)同的深入,“幼獅”會(huì)持續(xù)調(diào)整行為以符合角色期望。
最后,本研究比較了個(gè)體反思與個(gè)體主動(dòng)性兩種信息獲取策略。個(gè)體反思是內(nèi)在導(dǎo)向的知識(shí)創(chuàng)造戰(zhàn)略,可以增加自我理解,并為各種環(huán)境下的適當(dāng)行為產(chǎn)生見解。新任領(lǐng)導(dǎo)者的主動(dòng)行為強(qiáng)調(diào)從外部獲取信息以更好地進(jìn)行決策。如表5所示,個(gè)體反思與個(gè)體主動(dòng)性顯著正相關(guān)(r=0.046,p<0.05)。我們?cè)诶碚撃P椭型瑫r(shí)納入這兩個(gè)變量,個(gè)體反思與個(gè)體主動(dòng)性對(duì)角色認(rèn)同的直接效應(yīng)都是顯著的,即個(gè)體反思與主動(dòng)行為是不同性質(zhì)的信息獲取行為。
在保證研究嚴(yán)謹(jǐn)、科學(xué)的同時(shí),本文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是樣本選擇,本研究基于王品“幼獅”項(xiàng)目這一具體情景,沒有對(duì)其他情景進(jìn)行研究,后續(xù)研究可以納入更多的研究情景,以提高結(jié)論的外部效度。其次,變量定義方面,可以通過(guò)細(xì)化詞典類目,動(dòng)態(tài)地定義反思、學(xué)習(xí)行為的不同階段,比如將反思按照問題描述、問題分析、理論構(gòu)想與實(shí)施計(jì)劃等四個(gè)階段分別定義。最后,情緒狀態(tài)的產(chǎn)生是由個(gè)體的人格特質(zhì)與環(huán)境刺激的交互作用形成的,本文研究消極情緒時(shí)沒有考慮個(gè)體差異。
參考文獻(xiàn):
[1]?SEIBERT S E, SARGENT L D, KRAIMER M L, et al. Linking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to leader effectiveness and promotabil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leadership self-efficacy and mentor network[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17, 70(2):357-397.
[2]?曹春輝, 席酉民, 張曉軍, et al. 社會(huì)化經(jīng)歷與本土文化對(duì)領(lǐng)導(dǎo)特質(zhì)形成的影響研究[J]. 管理學(xué)報(bào), 2012(8):1118-1125,1153.
[3]?ASHFORD S J, DE-RUE D S. Developing as a leader: the power of mindful engagement[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012, 41(2): 146-154.
[4]?STEIN D, GRANT A M. Disentangl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elf-reflection, insigh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role of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core self-evaluations[J].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4, 148(5):505-522.
[5]?DAUDELIN M W.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through reflection[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1996, 24(3):36-48.
[6]?DRAGONI L, OH I S, VANKATWYK P, et al. Developing executive leaders: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cognitive ability, personalit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work experience in predicting strategic thinking competency[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11, 64(4):829-864.
[7]?INZLICHT M, SCHMEICHEL B J, MACRAE C N. Why self-control seems (but may not be) limited[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4, 18(3):127-133.
[8]?BEEVERS C G.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a dual process model[J].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005, 25(7):975-1002.
[9]?LAVRIC A, RIPPON G, GRAY J R. Threat-evoked anxiety disrupts spatial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an attentional account[J].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03, 27(5):48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