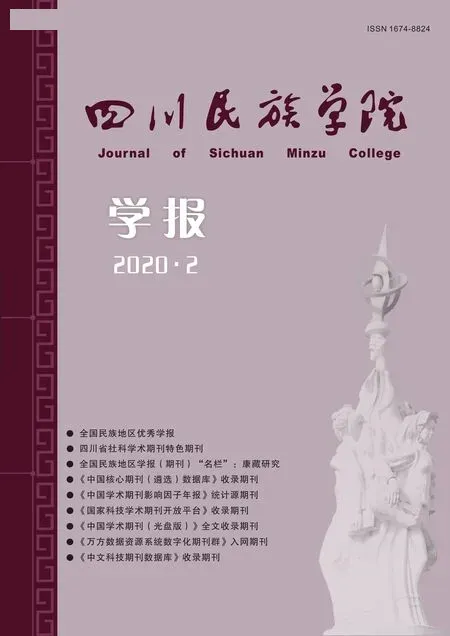文化自信背景下浙江景寧畬族“奏名學法”的系統(tǒng)功能分析
王增樂
(中共景寧畬族自治縣委黨校,浙江景寧 323500)
在黨的領導下,新中國成立的70年是貫徹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70年。在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旗幟下,各民族的文化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重要因子。尊重各民族的文化成果,共享各民族的文化創(chuàng)造是當代中國的基本文化現(xiàn)實。文化自信本質(zhì)上是文化創(chuàng)造和文化進步的直接收獲[1]。在全球化時代,弘揚民族自信是基于各民族源文化的當代闡發(fā)。
習近平總書記的“文化自信”論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fā)展指明了方向[2],對中國境內(nèi)各民族文化的發(fā)展有深遠的意義。畬族是世居浙西南的民族,有著悠久而又獨特的文化,其文化內(nèi)容豐富多彩,“奏名學法”是其中的獨特文化要素。
一、“奏名學法”基本情況介紹
(一)“奏名學法”研究概況
“奏名學法”在景寧畬族文化中又稱“做聚頭”“做陽”“傳師學師”[3], 為了“把活著的人的名字告訴祖先,把祖先的法則傳給后代”[4],兼具強化儀式和轉(zhuǎn)化儀式,既是畬族世代相沿的男子成年禮[5],又是畬族傳統(tǒng)祭祀儀式[6],作為用(含有巫術成分的 )[7]歌舞形式傳授本民族歷史和文化知識的一種途徑,“奏名學法”還具有收族聚宗[8]的功能。
把“奏名學法”作為文化事項開展研究,不但對繼承和弘揚畬族的傳統(tǒng)有重要意義;而且,探討學法弟子(稱之為新罡弟子)在其中的意象構筑和其作用機制,無論是對加強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平等交往基礎上的民族團結和文化交流,還是對“一帶一路”背景下,不同國家跨文化交流的有效開展,都有現(xiàn)實意義。
(二)“奏名學法”儀式及人物情況
按習慣做法,“奏名學法”的儀式流程[9][10],見表1所示。儀式運行狀態(tài),在每一階段內(nèi),都是雙線程并行。
表1 “奏名學法”的儀式流程

“請祖擔”(又稱“采祖”(1)請祖擔,又稱“采祖”,舉行“奏名學法”儀式的人家,事先派人(到保存“祖擔”的那戶人家)把“祖擔”請到(挑到)自己家,“采祖”時,要攜帶雞、豬肉或其他祭品。畬族民眾把裝有祖圖、龍頭祖杖和竹制金鞭等物件的兩只編筐或竹箱,稱作“祖擔”或“游祖”。)是總的起點(A1),第一階段第一行流程是“A1-B1-C1-D1”。雙線程并行表現(xiàn)明顯的是:幾位法師在室內(nèi)進行流程“D1(置香案)”時,另有東道主帶領學法弟子在室外“拜天地日月、拜東皇公西王母”,再回到室內(nèi)“拜祖師拜本師公”,即為“三拜”,見表1的“D2”。直到第一階段的步驟“E2-F2-G2”完畢,第一階段的內(nèi)容方為完成。
表2 “奏名學法”中法師的職責劃分和服飾著裝

步驟A3(示法器)是第二階段的起點,本階段中,要完成“A3-G4”的儀式內(nèi)容。在整個階段中,法師們各司其職,持不同的法器,站不同的方位,進退有度、邊舞邊唱邊履職……
用三天三夜做滿三個階段全部環(huán)節(jié),即為“奏名學法”儀式完成,標志著在傳統(tǒng)上,一個畬族少年“成人”了,也意味著一個新的畬族法師獲得族群認同,允許其以“法師”的身份參加一些儀式了。
在整個儀式中,所有的法師統(tǒng)稱為“十二六曹”[11],除西王母(2)有幾位同時學法的新弟子,就有幾位保舉師,但多位保舉師依視為只有一位;相應地,即使有多位西王母,也依然視同只有一位。學法弟子要在“奏名學法”結束后,拜保舉師為義父,拜西王母為義母。一職通常由保舉師的妻子擔任外,其他十一位男性法師各有其職責,穿著不同服飾以區(qū)別,他們必須是自身經(jīng)歷過“奏名學法”成為法師且會跳傳師舞的,詳見表2。
二、“奏名學法”系統(tǒng)功能分析
(一)“奏名學法”經(jīng)驗純理分析
在傳播中,信息發(fā)布者通過(包括行為、語言、環(huán)境烘托等在內(nèi)的)多種途徑來描述“過程”,受眾要把接收到的信息轉(zhuǎn)變?yōu)榻邮照弑救说慕?jīng)驗,傳播的階段方為完畢。
功能語言學認為,人類作用于世界的活動過程可分為六種:物質(zhì)、心理、關系、言語、行為和存在[12]。人們通過語言在系統(tǒng)中的選擇,用“過程”去表達現(xiàn)實世界中的種種經(jīng)歷[13],即為經(jīng)驗功能,其中還連接到一定的“參與者”和必要的“環(huán)境成分”[14]。
在“奏名學法”儀式中,畬族的法師們用語音和體態(tài)動作以及構筑的場景等來傳遞信息。為對這一儀式及其表達展開經(jīng)驗功能分析,特選取“奏名學法”中的“B6(過九重山)”環(huán)節(jié),如表3所示。
“過九重山”是閭山學法中的重要內(nèi)容,有關閭山學法的民族傳說為整個環(huán)節(jié)設定了基調(diào)。表現(xiàn)在儀式里的情節(jié)是:學法弟子腳穿草鞋,手執(zhí)龍角神刀開路,肩背旅途用品,邊唱邊跳,辭別家鄉(xiāng)父母,前往學法。歷時三年(往程一年,學法一年,返程一年),返回時,風塵仆仆、鬢須滿面,衣服成縷成線、破爛不堪,親人見面幾乎不能相認。
前往閭山學法途中的“B6(過九重山)”環(huán)節(jié),由引壇師帶領新弟子,在虛擬的場景中(“九重山”(3)“九重山”是由九枝綠葉蔥蔥的竹枝,插在村外開闊地、室外草坪或中堂地面構成。)完成。在現(xiàn)實近景與虛擬遠景中,“過九重山”這一事件發(fā)生在當下,但也發(fā)生在先祖的經(jīng)歷(傳說)中,還發(fā)生在一代又一代法師對當年“奏名學法”的記憶中。藝術手段總是要在一定的視覺范圍內(nèi)進行[15],表3中的“過九重山”,在法師們的歌唱、民族樂器伴奏等音效-虛擬場景等構成的氛圍中,“鑲嵌”到學法弟子在未來發(fā)生的一次“奏名學法”儀式里。“過九重山”用這樣的方式,溝通了過去-現(xiàn)在-未來(按照傳統(tǒng),未來更年輕一代的學法弟子也將要經(jīng)過相同的學師階段,才能成為法師),以獨特的民族語言、畬族歌舞的表現(xiàn)手法和畬族傳統(tǒng)的文化背景,巧妙地穿插了民族記憶、現(xiàn)實畫面和未來遠景。
為“更好地把握現(xiàn)在”[16],而實現(xiàn)“時空穿越”,因為“時間的‘越出自身’”的表征,在存在的意義上,“構成人的‘越出自身’”的表征[17]。在價值觀念上,達到個體與(本民族)主體的溝通。正是在這一點上,“過九重山”的環(huán)節(jié),達到了外觀目標—(模擬祖師求法學法的艱辛,從而)強化祖先崇拜和圖騰崇拜的目的,同時也達到了深層目標—實現(xiàn)了民族傳統(tǒng)教育的目的。
表3所示的其他環(huán)節(jié),也可以進行類似的經(jīng)驗功能解讀,通過對展開情節(jié)的“敘事探究來理解經(jīng)驗”[18],從而認可法師們的表達,熟悉歌舞、語言和其他動作的寓意,體會環(huán)境成分的背景渲染效果,感悟情景設置中的意境,傳遞儀式環(huán)節(jié)所敘述的內(nèi)容。
表3 “奏名學法”流程中部分環(huán)節(jié)的經(jīng)驗純理分析簡表(4)畬族的“奏名學法”流程是由許多情節(jié)構成。每個情節(jié)都可劃分出多個環(huán)節(jié),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可以區(qū)別物質(zhì)過程、言語過程、心理過程等。在表3中,只選取其中的標志性環(huán)節(jié),進行相應分析。

(二)“奏名學法”情景意象分析
在“奏名學法”過程中,法師們持三音鑼、響背、木魚、法鼓和龍角伴舞,在綜合各種唱詞、多種曲調(diào)和變化符咒的音響效果中,加以周圍滿掛的三清、玉兔搗藥、金雞報更、救苦天尊等圖幅和刻畫畬族先祖出生、征戰(zhàn)、學法、狩獵、殉身等長聯(lián)祖圖構成的畫影氛圍中,營造了畬族“奏名學法”文化的特定場景,通過畬族傳統(tǒng)的間雜語言文字的人體動態(tài)文化(包括變化多端的手部動作和坐蹲步、三角步、丁字步等多種舞步)完成了同先祖對話、與現(xiàn)在交流、和未來溝通的特殊儀式。
在日常生活中,畬族子弟浸潤在民族傳統(tǒng)的氛圍內(nèi),畬族的文化心理、文化結構和文化習俗已由主體認知、主體感悟、主體體驗等知覺活動建構成畬族子弟自己的文化底色。所以,“奏名學法”的儀式內(nèi)容,產(chǎn)生自畬族文化內(nèi)核之上的“共同的心理和社會基礎”[19]。因此,“奏名學法”在方式呈現(xiàn)和意義表達上,成為維系某種共同體的紐帶[20]。這種共同體就是畬族的傳統(tǒng)文化所構筑的象征體系,其形成同時體現(xiàn)了一個具體歷史過程的結果和微觀的多元社會文化的整合以及較為宏觀的區(qū)域歷史進程[21]。
經(jīng)過“學法”過程的熏陶,喚醒沉睡在學法弟子思想深處對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意識,學法弟子受到民族文化的感召,將畬族傳統(tǒng)與自身責任看作是一個整體,同時又將其蘊含在“奏名學法”自布局至流程-唱詞-舞姿等表達因素的各個層面上。
事實上,這些因素之間的聯(lián)系,更深厚地根植于畬族民眾的普遍信仰。在流程中,“奏名學法”的法師們帶領弟子,歷經(jīng)虛擬與現(xiàn)實場景的“內(nèi)隱學習”[22]來完成民族文化基因的延續(xù)。學法弟子的親身實踐,經(jīng)由其各自的人生經(jīng)歷和審美想象參與積累并相互碰撞,學法弟子方能得以浸潤于文化意境之內(nèi)。
在“奏名學法”的儀式中,學法弟子既是主動參與者,又是從動學習者,還是身臨其境的觀察者。這種獨特的身份,是其審美知覺與純粹的旁觀者產(chǎn)生不同認知的根本原因。學法弟子是具有基本的畬族文化基礎的,這是他們能夠?qū)W習“奏名學法”的“有音樂感的耳朵”和“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所以,他們才能“以全部感受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3]。
格式塔心理學認為,人們有將視聽到的、感知到的形象加工成已知完整形象的趨勢[24]。“奏名學法”儀式中法師們借助光影、唱詞曲調(diào)、動作以及氛圍和畬族民眾共同的文化背景為依托創(chuàng)造一系列意象,來抒發(fā)自己的情感,喚起畬族民眾對先祖的懷念,通過“復制過往的現(xiàn)實的手段,體驗生命進程的手段”[25]和方式,激活學法弟子的主體認知、思考和理解,形成整體意境(對于可能缺失的物品、人物及規(guī)范,學法弟子動用民族文化背景的其他內(nèi)容來填充[26]),把“奏名學法”蘊含的民族文化精神“從表象的存在轉(zhuǎn)變?yōu)楝F(xiàn)實的存在”[27],從而構筑起學法弟子本人對“奏名學法”意義及相關因素初步的格式塔意象。在“奏名學法”過程中,法師們虛擬性的行為方式、表演手法、場景布置,于法師們和學法弟子心理時空中,共同構擬出一個虛擬世界,并由此讓學法弟子在“超常態(tài)行為”中“感受真實”[28]。
在人類思想發(fā)展史上,各古老民族哲學認識方面的內(nèi)容[29],有許多從生活禮儀、宗教儀式中反映出來。“當透過不同的文化外表上特殊的現(xiàn)象,來掌握它的內(nèi)在含義和心理學真實”[30]的時候,要清楚“畬族始祖信仰在畬族文化中占據(jù)重要地位”[31]。所以,由畬族的原始信仰和由其產(chǎn)生的“哲學、神學和科學的內(nèi)容”[32],以及因畬族漢族雜居而雜糅的道教巫術內(nèi)容[33],在此共同影響下派生的“奏名學法”就構成了學法弟子多層次的格式塔形象,使得向下一代傳授文化的過程,盡量保持原有狀態(tài),盡可能“準確地再現(xiàn)”[34]。
三、對跨文化交往工作開展的啟示
在他者文化的旁觀者看來,畬族的“奏名學法”,在氛圍烘托、意蘊塑造、儀式表達及內(nèi)容呈現(xiàn)上,有很多意義空白或者意義模糊。這些意義空白或意義模糊,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無限的審美思維空間,對他者文化的好奇和向往由此產(chǎn)生,對他者文化的隔閡和誤解也由此產(chǎn)生。
(一)對國內(nèi)民族文化交流工作的啟示
中國56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同一民族內(nèi)部不同支系也有多姿多彩的亞文化。具有差異文化因素的民眾在交往時,對自己不熟悉的文化內(nèi)容感到困惑,這種情況在多民族國家是很正常的。
就語言表述而言,交流中信息接收者在跨文化交際中,“通過語言的模糊性和終極意義的不可觸摸性去削弱作者的前在偏見”[35],嘗試在自己的文化底色上,構筑對交流內(nèi)容和情景的格式塔意象。基于文化前提的必然反應構成了我們許多下意識的行為方式的主要部分[36],這既是對雙方交流的正常反應,也是對雙方交流的深化嘗試。
如此境況下,“站在對方的角度上思考”就顯得非常中肯。這就是通常所講的“換位思考”。然而,換位思考并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要做到切實的“換位思考”,并在此基礎上“換位行事”,顯然有許多事情要做:
首先,我們要認同對方的行為及其方式也是有價值的(盡管這種價值是自己一方從未接觸過或暫時不了解的),“我只有構成我的精神個性的形式”[37],對己方是這樣,對他者一方,何嘗不是如此?認識自己,認識對方;發(fā)現(xiàn)對方,“發(fā)現(xiàn)自己”[38]并反思自己。
其次,我們需要篤信在和對方的交往中存在的誤解是“以一種‘深層的共同一致’為前提”[39]的,這個前提就是雙方都認可對方,都渴望與對方進一步的交往。
再次,在雙方平等交往的前提下,給予對方充分的尊重,正視雙方在認知或行為方式方面存在的某些差異,并同時明確表達自己對交往中某些事和某些行為的見解。
因此,帶著欣賞的眼光去了解對方的文化,借鑒對方的文化,學習對方的文化,是非常有效的途徑。正如柏拉圖所倡導的,青年們在不同文化中不知不覺受到熏陶[40]。在此基礎上,理解對方的文化,就是理解不同的人生視角和不同的社會認知。這也是作為學習者的“我者”精神世界的拓展[41]。
基于民族平等團結的前提,我們在交往中,努力擴大自己的視野,學會欣賞其他民族的文化,才可能促進當代中國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42],實現(xiàn)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榮。
(二)對“一帶一路”背景下跨文化國際交流的啟示
自2014 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APEC會議上發(fā)起“一帶一路”倡議以來[43],基于這一背景的跨文化交流已成為中國拓展文化空間的有效方式,是主動展示處于“日常生活狀態(tài)”[44]的中國人形象的全新切入點。
由于作為個體的人時刻鑲嵌于自己過去經(jīng)驗的影響中,浸潤于自己所處的文化與歷史中,個體的人無法徹底消除它們的影響。對本地人而言,進入己方文化的陌生人的涉及當下所在的言論,本地人認為是異域國家的人作為他者對于主體國家的評價與認知;在他方看來,是作為(他者認為的)我者的主動體驗。本質(zhì)上,“是由他們所屬不同群體中所有相互交織的文化力量組成,并且由于他們生活的社會語境所構建”[45]的文化底色面對異質(zhì)文化的自然反應。
因此,在跨文化的交往中,需要主動了解(多方中的)他者文化,尊重他者的文化,充分調(diào)動自身的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理解對方并嘗試“被對方所理解”,認識對方的“文化世界”[46]和以之構建的“理念世界”,對跨文化交往中感知的意義空白或意義模糊進行處理和加工,強化語言認知、行為認知和其他認知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美感體驗,欣賞他者文化。
在跨文化的交往中,我們需要及時分析自身在遇到他者文化時格式塔意象構建過程中出現(xiàn)的偏差,把自身體驗到的經(jīng)驗整體,予以再組織和再建構。在“和而不同”“不走極端”[47]“成人之美”的價值追求基礎上,“各美其美,美美與共”[48],實現(xiàn)民心相通,促進各沿線國家文化的共同繁榮[49],為解決復雜多變的國際問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