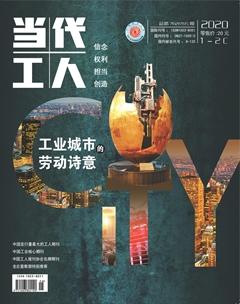鹽從海上來
張北



在遼東半島的最南端,有一個古老又現代化的班組——大連鹽化集團有限公司五運公司五島制鹽廠九班(以下簡稱九班)。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他們向海取鹽的工作方式,已延續數千年之久,而今,在先進機械的加持下,通過雙手創造出的鹽業生產,又是滿滿的科技范兒。
漫長的錘煉
在我國,鹽的主要來源有4個,即井鹽、湖鹽、巖鹽和海鹽。其中,井鹽、湖鹽和巖鹽,雖不易開采,但生產程序簡單得多,海鹽則恰恰相反。別看海鹽是海水中含量最多的一種物質,但想把它提煉出來,需要有納潮、制鹵、結晶、收鹽這一漫長的生產過程。
海鹽以海水為原料,人們借助海水潮起潮落形成的落差,把海水送入鹽田,這個過程叫納潮。納潮采集而來的海水被分流到制鹵區,在面積廣闊的蒸發池內制鹵。制鹵池子星羅棋布,圍成一塊塊鹽田,依靠著海水的逐漸濃縮,使鹵水濃度逐漸提高,達到飽和后,鹽鹵進入鹽場結晶池,利用陽光將水分繼續蒸發結晶,最終,結晶池底部形成厚厚一層鹽粒。
“每一環節都少不了九班的身影。”九班班長孫長偉介紹,班組現有18名職工,平均年齡40歲左右,負責6平方公里面積內的制鹽全過程。
被時間和面積拉長的鹽工,自古以來,都是一份難熬的活計,“所以組員多是鹽二代、鹽三代,或許也只有在子承父業代代相傳中、父輩辛勤勞作的影響下,這份辛苦才會顯得不那么辛苦。”
“這是波美度表,鹽工必備家什,因為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量水中鹽的濃度。”九班鹽工李成龍,在鹵水池邊俯下身子取出水樣,讀出波美度表顯示的數字。“25.5度,基本達到飽和水了,可以進行下一步,進入結晶池了。”
李成龍是鹽二代,他管轄之內有6個蒸發池、3個鹵水池,每天要來回走,反復測量。因皮膚長期暴露在陽光之下,再加上鹽的反射,李成龍面色暗紅,魚尾紋很深,30歲出頭卻顯得比同齡人更老成一些。
“我們負責的是制鹽的源頭,必須把簡單的事情重復做,365天如一日,一點兒錯誤都不能犯,這樣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制出更好更多的鹵水,保證后續產鹽的完成。”李成龍邊說邊將結晶好的鹽進行扒收,集中歸坨,逐一分類。
“我就是從這兒退休的。”今年76歲的孫述章是鹽場退休鹽工,1966年參加工作的他,曬了一輩子海鹽。
如今,他把家安在九班作業區不遠處,閑暇時,就到這里找回憶:“過去跟現在可不能比。我剛參加工作那會兒,正趕上春天修灘,整理結晶池,每天工作9到10個小時就感覺挺累,沒想到后來去曬鹽,早上5點起床先推鹽再吃飯,吃早飯時間不超過半小時,接著一直推鹽到11點吃中午飯,12點接著干,晚上5點吃過飯還要再推一次……當時的鹽工連互相逗趣的時間都沒有,每天只有兩件事,除了吃飯就是推鹽。”
工作條件也很簡陋,因為鹽場提取海鹽,用的是平曬工藝,沒有塑料苫蓋。晴天扒鹽,雨天保鹵,如果雨水落入了鹵池,鹽就會被稀釋掉,損失慘重。“過去只要天一陰,所有在池里的鹽都得立馬撈出來,若是趕上雨天,就需要連夜搶扒海鹽,24小時不休息是家常便飯。鹽工推鹽至半夜,困了,扶著獨輪車瞇一會兒,睡著了手就松了,獨輪車一歪,立馬又醒了,睜開眼睛就得接著干。即便如此,也沒有一個往家跑的。”
“現在有了塑曬工藝,再配合準確的天氣預報,遇到下雨天,一按電鈕,塑料布會自動蓋在鹽上面,不需要人工嘍。”孫述章有些失落,更多的卻是羨慕。
若隱若現的點
從20世紀60年代用單輪車推鹽,人拉肩扛,到20世紀70年代的單輪車變四輪車,人工收鹽改為收鹽機,再到20世紀90年代的管道輸送,生產工藝由平曬改為塑曬,“隨著科技的進步,現代化生產設備的引進,大連鹽化集團也由當初的6300人縮減到今天的1650人,產能卻在節節升高。比如我們班組,6平方公里、年產量3.8萬噸的海鹽生產任務,18個人就可以完成。”孫長偉說。
“1983年我入廠時,只扒鹽一項就要25個人才能操作,現在只要三兩個人,過去的工作強度一般人承受不了,累得連飯都不愛吃。雖然現在對工人的體力要求降低了,但我們也不斷面臨新的挑戰,比如單人作業面積的不斷擴大、操作流程的技術提高、制鹽效率的穩步提升等。”
遠遠望去,鹽山仿佛一座座高聳的白色雪山,隨著鹽工駕駛收鹽機的抽動、過濾和分離,鹽通過管道,從池子里被抽出來,為雪山添磚加瓦,累積出新的高度。鹽工,則被高聳的鹽山與巨大的鹽池“掩蓋”,成為若隱若現的點。正是這一代又一代的九班,正是這些不停閃動的“點”,組成了我國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有鹽化企業——大連鹽化集團有限公司,走過170年的悠悠歲月,不斷轉型升級,依然生機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