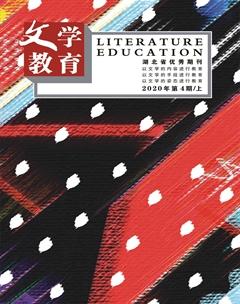從郭沫若的《女神》看“自由體新詩”的嬗變
內(nèi)容摘要:作為中國新詩第一個(gè)偉大的綜合者,郭沫若對(duì)新詩的開拓和發(fā)展作出了劃時(shí)代的貢獻(xiàn)。本文從《女神》的角度入手,具體闡述中國新詩由“以物觀物”向“以心觀物”的轉(zhuǎn)變、在“表現(xiàn)自我”中的“象征主義”移植、最后創(chuàng)造出以浪漫主義為主色調(diào)的“自由體新詩”的嬗變過程。
關(guān)鍵詞:《女神》 表現(xiàn)自我 象征主義 自由體新詩
按照文化是“人類在社會(huì)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物質(zhì)財(cái)富和精神財(cái)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cái)富”[1]的界定說,郭沫若是中國新詩第一個(gè)偉大的綜合者,他把中國新詩從“摹仿自然”階段推向“表現(xiàn)自我”階段,并借助泛神論加強(qiáng)了新詩“表現(xiàn)自我”和反封建力度;使“二十世紀(jì)的動(dòng)蕩和反抗精神”成為新詩藝術(shù)的精魂和生命線。他的《女神》一問世,就急遽地結(jié)束了五四詩壇上的“胡適開一代詩風(fēng)的時(shí)代”,引領(lǐng)中國新詩走上新的里程。
一.從“以物觀物”向“以心觀物”的轉(zhuǎn)變
作為五四新詩的重要成果之一,郭沫若以《女神》為代表的早期詩歌創(chuàng)作,一直被普遍視為現(xiàn)代新詩史的真正開篇。長期以來,研究者們反復(fù)談?wù)摗杜瘛分谐錆M理想光彩的自我抒情形象、大膽叛逆精神以及滲透在內(nèi)容和形式中的徹底解放感,為的是說明郭沫若在五四時(shí)期的新詩創(chuàng)作成就不僅支撐了整個(gè)創(chuàng)造社詩人群,面且照亮了整個(gè)五四新詩壇。他不僅是“代表五四以后最早也是突出的浪漫主義詩潮”,而且也是中國新詩第一個(gè)站在時(shí)代的高度來審視中國新詩壇、
參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
眾所周知,郭沫若在五四時(shí)期的詩體大解放中,沖破了一切舊體詩詞格律的束縛之后,明確地提出“情緒說”或“自我表現(xiàn)說”。他認(rèn)為,詩的主要成分是“自我表現(xiàn)”,“情緒”高于一切,“情緒的律呂,情緒的色彩便是詩”。[2]在1920年1月18日寫給宗白華的信中激情地宣稱:“我想我的詩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的純真的表現(xiàn),命泉中流出來的shain(曲調(diào)),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旋律),生的顫動(dòng),生的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便是我們?nèi)祟惖讱g樂的源泉,陶醉的美醇,慰安的天國。”[3]他的這個(gè)理論追溯起來是導(dǎo)源于盧梭、歌德、華茲華斯等浪漫主義大家。英國的華茲華斯就給詩下過這樣的定義:“所有的好詩,都是從強(qiáng)烈的感情中自然而然的溢出的。”[3]一定的程度上,郭沫若對(duì)新詩理論及創(chuàng)作來說顯然是一次猛烈的沖擊和反叛,創(chuàng)造了和“摹寫自然”迥然不同的“表現(xiàn)情緒”的詩歌。在他的詩歌中,復(fù)沓、排比手法的運(yùn)用不僅使句子讀起來瑯瑯上口,有時(shí)還直接起著結(jié)構(gòu)篇章的作用,這一種手法的使用,可以說是郭詩的一個(gè)創(chuàng)造。一方面有助于造成一種奔騰流蕩的氣勢(shì),將詩人噴瀉而出的激情徑自地融入富于節(jié)奏感的詩行中,既能徹底將早期白話詩從半文半白的狀態(tài)中解放出來,又能表現(xiàn)出五四時(shí)代的自由精神,更能比較容易地獲得新的韻律感,昭示了“摹寫自然”的逐漸消退。
郭沫若筆下的自然已經(jīng)在自然景觀中流溢著詩人心中的詩意、詩境,是詩人情緒中的自然,或者說是詩人在自然中的情緒。因此,在他的詩中,有了更多的“自我表現(xiàn)”成分和較為分明的主體形象,詩歌觀及其創(chuàng)作標(biāo)志了中國新詩由“以物觀物”向“以心觀物”的轉(zhuǎn)移。中國新詩到郭沫若才真正塑造了主體形象,才真正具有審美意識(shí)的主體性,中國新詩才真正躍進(jìn)到現(xiàn)代化的行列。郭沫若的這種特點(diǎn)最清楚不過地體現(xiàn)在他的代表作《女神》中。
二.在“表現(xiàn)自我”中的“象征主義”移植
對(duì)郭沫若而言,表現(xiàn)主義似乎比象征主義更具吸引力。他曾多次引述表現(xiàn)派的觀點(diǎn)與概念,并表達(dá)了與表現(xiàn)派的“共感”。但他所推崇的是那種與其自我表現(xiàn)的浪漫主義精神和原則一致的表現(xiàn)主義,按他的闡釋,這種表現(xiàn)主義“尊重個(gè)性,尊重自我,把自我的精神運(yùn)用客觀的物料,而達(dá)到自由創(chuàng)造”。[4]對(duì)表現(xiàn)主義的其他重要方面,如“擺脫資產(chǎn)階級(jí)社會(huì)的語言、價(jià)值和式樣,表現(xiàn)人格的最深層次,并利用得自現(xiàn)代工業(yè)世界的象征”以及運(yùn)用抽象或變形手法“創(chuàng)造幻象世界的嘗試”等等[5]并未給予特別關(guān)注。換言之,表現(xiàn)主義只是他用來表述其浪漫主義文學(xué)觀的另一個(gè)概念,它消融于這種浪漫主義,而不具獨(dú)立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詩歌還是以浪漫主義為主導(dǎo)的,同時(shí)也與現(xiàn)代主義有若干的聯(lián)系。在《女神》中,可以看出郭沫若是怎樣把激情、想象、聯(lián)想與象征有機(jī)地糅合在一起,以致富于激情與想象的詩篇,幾乎都有象征的意義在,或象征某種精神,或象征某種情感,或象征某種意愿。《風(fēng)凰涅槃》就是象征詩,還帶著神秘的色彩。在詩中,郭沫若把象征與狂幻想的激情、奇麗的聯(lián)想結(jié)合起來,構(gòu)成了象征“美的中國”再生的神話的詩。長詩的《序曲》抒寫鳳凰集香木燃火、群鳥間“冷淡如鐵”、“黑暗如漆”、“腥穢如血”,以及在漫長的歷史中“流不盡的眼淚,洗不盡的污濁,澆不滅的情炎,蕩不去的羞辱”。接著《群鳥歌》展示了對(duì)宇宙人生的不同層面的理解,以及精神宇宙的主體性。群鳥對(duì)宇宙人生的體認(rèn)與鳳凰處在不同的精神層面,說明鳳凰的黑暗、冷酷、荒謬的環(huán)境中的自焚行為充滿了孤獨(dú)的悲壯感。再如《爐中煤》、《晨安》、《匪徒頌》等詩作以及《星空》、《瓶》、《前茅》中的部分詩作,也具有象征的意蘊(yùn)。同時(shí),郭沫若還善于運(yùn)用象征性意象以擴(kuò)大詩的內(nèi)蘊(yùn)和強(qiáng)化詩的情感,其中貫穿的意象,加強(qiáng)了詩歌的表現(xiàn)力,豐富了詩歌的精神內(nèi)涵,展示藝術(shù)魅力。
應(yīng)當(dāng)指出,郭沫若詩中所運(yùn)用的象征,不是嚴(yán)格意義上的象征主義,他對(duì)西方象征主義詩藝并沒有作過認(rèn)真研究,而是取其“類比”方式。其中的重要的觀點(diǎn)是:“真正的文藝是極豐富的生活由純粹的精神作用升華過的一個(gè)象征的世界”[6]。正因?yàn)槲乃嚩际恰跋笳鞯氖澜纭保浴杜瘛穾缀跏窃诹η蟆皠?chuàng)造一個(gè)類比的大網(wǎng)”,這個(gè)“類比的大網(wǎng)”,并不體現(xiàn)為對(duì)象征主義的詩藝(符號(hào))的著意經(jīng)營,而是體現(xiàn)為對(duì)象征精神意蘊(yùn)的關(guān)注與探索。象征主義作為浪漫主義運(yùn)動(dòng)以后興起的一種新的潮流,被郭沫若專注于西方象征主義的移植,由于他的傳統(tǒng)詩詞的深厚功底,使得他得其精義。
三.創(chuàng)建浪漫主義為色調(diào)的“自由體新詩”
郭沫若早期的與浪漫主義共生的那種象征主義,為其“自我表現(xiàn)”和“自然流露”提供了詩意的支撐。在這里,主體情感借助外在物象和情境呈現(xiàn)著自身,這種主客體的統(tǒng)一,使激情的宜泄得到了詩意的升華,因而這些詩都具有所謂的“具體性”,又由于主體的介入而有了某種超越性,給郭沫若的“自我表現(xiàn)”以形體,使其避免了一瀉無余。郭沫若的詩就吻合了“五四”時(shí)代“狂飆突進(jìn)”的個(gè)性解放精神,保持了詩人奔騰不息的個(gè)人風(fēng)格,又不失詩的境界與意趣。這種借助“融會(huì)貫通”而產(chǎn)生的象征意蘊(yùn),在《女神》之后的創(chuàng)作中發(fā)揮著浪漫雄渾的熱情和撼人的藝術(shù)光澤,卻又在自然的沖淡中保持了郭沫若那種淋漓的元?dú)夂酮?dú)特的詩意。
聞一多說:“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7],卞之琳在《新詩與西方詩》中也說,郭詩出現(xiàn)以后,“新詩才真像新詩”。事實(shí)上,郭沫若的詩歌是以浪漫主義為主色調(diào)的,而表現(xiàn)主義和象征主義則是其詩歌的精義所在;他在把象征主義納入了浪漫主義的總體框架中,創(chuàng)造了被稱作“女神體”的真正的自由體新詩,充分顯示了五四“詩體大解放”的實(shí)績(jī)。《女神》的問世,把舊詩詞的限制一掃而光,把一切羈絆統(tǒng)統(tǒng)推倒了,中國詩歌從這里真正得到了解放,為青春的熱情尋找恰當(dāng)?shù)恼Z言和形式,創(chuàng)造出了完全合于自己詩歌內(nèi)容的嶄新的多姿多彩的新形式。連郭沫若自己都說:“我所著的一些東西,只不過盡我一時(shí)的沖動(dòng),隨便地亂跳亂舞罷了。”[8]然而正是這種亂跳亂舞的詩,很好地傾瀉出五四時(shí)期人們胸中那“大波大浪的洪濤”,完美地反映了五四時(shí)期狂飆突進(jìn)的精神。
《女神》以自己的思想情緒支配詩行,以情緒的旋律表現(xiàn)詩的旋律。郭沫若不愿局限于一個(gè)格局,而是徘徊翱翔在所有敘述性、抒情性、戲劇性的形式之間,來回于散文與詩歌風(fēng)格之間。突破了那風(fēng)格之一律的舊原則,詩人以“破壞一切,創(chuàng)造一切”的力量和氣魄去推倒一切舊形式,重建一種新形式,這種新形式再也不是一種束縛人們手腳的鐐銬,而是自如地抒寫自己的激情和想象的自由的形式。從郭沫若開始,新詩不再存在固定的格律規(guī)范,詩中的激流隨著內(nèi)在情緒的節(jié)奏而起伏;讀者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對(duì)音韻形式美的品味和感知,而主要是以聯(lián)想的方式投入情緒的體驗(yàn),從而獲得美的享受。郭沫若的詩歌創(chuàng)作,實(shí)踐了他的自由理論,即“藝術(shù)的自由”的審美觀念,這種觀念要求每個(gè)詩人都成為他自己,沖出狹小的空間,走進(jìn)廣闊的藝術(shù)天地,而實(shí)際是喚起每個(gè)詩人的藝術(shù)的覺醒。
因此,郭沫若黃鐘大呂般的高亢歌聲,無疑是表現(xiàn)自我、象征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逐步嬗變。中國現(xiàn)代浪漫主義詩潮借助郭沫若的《女神》,閃現(xiàn)出強(qiáng)烈而短暫的美學(xué)光輝,而郭沫若的文學(xué)地位也借助浪漫主義得以奠定。我們看到,五四詩歌革命只有到了《女神》才“異軍突起”,才充分顯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威力,新詩陣地才有了主將。《女神》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恢宏的詩歌創(chuàng)造才能,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全新的藝術(shù)世界,為中國新詩開多拓了主體精神的新天地。
參考文獻(xiàn)
[1]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xiàn)代漢語詞典[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5:1427
[2]郭沫若.生命的文學(xué)[J].學(xué)燈,1990(2)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xué)編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0.
[4]郭沫若.郭沫若論創(chuàng)作[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607.
[5]理查德·謝帕德.德國表現(xiàn)主義-現(xiàn)代主義[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2:249
[6]劉增杰.云起云飛[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311
[7]聞一多.女神之時(shí)代精神[N].創(chuàng)造周報(bào),1923-06-03(4)
[8]伍蠡甫.西方文論選:下[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3.
(作者介紹:王秀芹,泰山學(xué)院文學(xué)與傳媒學(xué)院副教授,從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影視傳媒,廣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