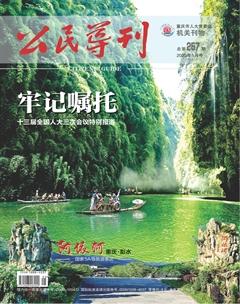杜先智:我的武漢戰(zhàn)“疫”
宋婷婷



“如果能夠哭一場,為了在武漢拼命的57個日與夜,我是愿意的。如果能夠笑一場,為了再度鮮活的名字和生命,我也是愿意的。但過了那個時間,繞著墻根走路的人就是我。”
從武漢回渝后,經過隔離,重慶市第三批援鄂醫(yī)療隊醫(yī)療組組長、專家組組長,重醫(yī)附二院呼吸內科副主任、博士生導師杜先智教授已重返昔日崗位,回歸正常生活。
風蕭蕭兮易水寒
2020年2月1日,武漢封城第十日,杜先智等候兩日的通知下來了:明日出發(fā),前往湖北!
他定了定神,拿出手機,妻子焦急的聲音傳來。
55歲的年紀、一年前經歷過肺部手術、家有90歲老母——在妻子眼里,這些都是杜先智不該遠行的理由。
但杜先智的回答令她更震驚:他是全院第一個報名參加援鄂醫(yī)療隊。
作為老黨員、投身呼吸科31年的資深醫(yī)療工作者,杜先智認為自己有責任、有能力馳援湖北。
回到家中已是夜里,杜先智躲進房間好一陣才出來。妻子拿出剪刀,默默為他鉸短頭發(fā)。
杜先智說:“我寫了點東西,壓在電腦鍵盤下。如果……如果我不能回來,你再打開看。”
頭發(fā)一簇簇往下掉,妻子的眼淚止不住往下流。
2月2日,江北機場候機廳,重慶市第三批援鄂醫(yī)療隊122名隊員集結出征。杜先智被宣布為醫(yī)療隊醫(yī)療組組長,同去的重醫(yī)附二院首批援鄂醫(yī)療成員有10名。
送行的重慶市常務副市長吳存榮言簡意賅:第一,圓滿完成任務;第二,把隊員一個不落地帶回來。
現(xiàn)場氣氛悲壯,杜先智竭力壓抑,仍不自覺潤濕了眼眶。
重慶飛武漢,兩小時既短又長。隊員們或神情凝重、雙手合握;或神思不定,如坐針氈。杜先智坐在機艙中部,亦是心情復雜。
飛機著陸武漢天河機場,大巴載著他們駛向賓館。小雨輕敲車窗,街上空無一人。
稍作安頓,命令便至:2月4日接管武漢大學人民醫(yī)院東院區(qū)十二、十三病區(qū)。
武漢大學人民醫(yī)院東院區(qū)是國家衛(wèi)健委指定的新冠肺炎重癥患者定點救治醫(yī)院。這意味著,他們將是重慶在武漢首批成建制接管重癥病區(qū)的醫(yī)療隊,“戰(zhàn)場”是兩個重癥病區(qū)!
杜先智立即召集核心隊員開會,集中討論、優(yōu)化排班,直至凌晨2點。
而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目光聚焦的這座城市里,在打響戰(zhàn)“疫”的前夜,杜先智失眠了。
君問歸期未有期
2月4日上午,成建制接管病區(qū)后,杜先智發(fā)現(xiàn)困難重重。
辦公環(huán)境和流程生疏,醫(yī)院騰出來的并非負壓傳染病房,但病患將在當夜陸續(xù)送達。
杜先智和隊員們步履生風:迅速熟悉辦公系統(tǒng),緊急進行病房重新分區(qū),根據(jù)病區(qū)功能分區(qū)布置設備。
夜里,病房里一下住進了16名重癥、危重癥患者。此后數(shù)日,又有大量病患涌入,最多時達到82名。
患者驟增,但機制尚未理順。杜先智看到護目鏡背后的眼睛里,全是掩飾不住的緊張。更讓他們焦灼的是,防護物資短缺、醫(yī)用設備匱乏。
這時,杜先智最擔心的事情發(fā)生了:病區(qū)出現(xiàn)第一例死亡病例。
該患者來時神情麻木、喘憋厲害,躺在病床上無法移動,幾乎失去對生的渴望。隊員們積極救治,但限于客觀條件,終是回天乏術。
然而,留給他們悲痛的時間極短。
“快,快進去把他們接出來!”2月10日,病區(qū)上演生死時速。
杜先智接到緊急通知,是日領取的口罩防護時長不是4個小時,而是2個小時。可是,一組護士已經進入“紅區(qū)”多時……
羅曉慶和李霞兩位護士長,立即穿戴好防護裝備,火速接人。出來后,七八名護士圍著杜先智哭了起來。他亦悲從中來,流著淚撥通求助電話,懇請務必保證口罩的數(shù)量和質量。
高壓之下,杜先智深感疲累。
自從來到武漢,杜先智即成為團隊的主心骨。作為醫(yī)療組組長、專家組組長,武漢大學人民醫(yī)院東院國家新冠肺聯(lián)合專家組成員,他不僅要負責收治患者、作出醫(yī)療決策,還需兼顧行政、外聯(lián)等事務。
杜先智一直繃緊神經,未敢懈怠絲毫。
然而這天,他突然被窗外紛飛的大雪勾起酸楚:這樣的日子,何時才是盡頭?
電話里,妻子也一遍遍詢問歸期。
杜先智的心里清楚,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不破樓蘭終不還
一夜失眠,杜先智重燃斗志,照舊6點起床,奔赴“戰(zhàn)場”。
為改變病區(qū)無序的情況,他決定建立病區(qū)醫(yī)療戰(zhàn)時管理模式。
將醫(yī)生和患者對應分組,對患者病情進行動態(tài)連續(xù)監(jiān)測;成立醫(yī)療和護理專家組,每日早晚討論當日工作問題。
建立醫(yī)療隊專家組組長、護理專家組組長定期聯(lián)合查房制;隊內醫(yī)療、護理問題向組長報告制。
自費購置可視通訊設備,及時了解患者的病情變化并做心理疏導。
這期間,國家衛(wèi)健委主任馬曉偉等領導三次來東院區(qū)辦公。杜先智等人借此機會,積極反映并呼吁。
諸多難題一一破解。氧氣鋼瓶得到補充、中心供氧擴容、有創(chuàng)呼吸機等相關重癥搶救設備到位,醫(yī)療護理有序運行。
作為重醫(yī)附二院首批援鄂的醫(yī)療隊,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后方的心。
夜已深,身在重慶的重醫(yī)附二院藥房主任發(fā)來微信,是關于氯喹安全性的文章。杜先智回復:“對,昨日我已要求停用氯喹,只有一個患者服用過一次。”
前方后方,一字一句,一來一回,既是專業(yè)探討,也是友愛關懷。
2月15日晚,為提高重癥患者救治率,醫(yī)療隊發(fā)起視頻聯(lián)線,與重醫(yī)附二院后方的專家組一起,為4名重癥患者會診。
這一“挽救生命于千里之外”的遠程會診機制在后期亦得到不斷完善。
2月20日,38歲胡姓患者的深深鞠躬,讓杜先智深覺拼搏努力的價值。
這是由重慶市第三批援鄂醫(yī)療隊治愈出院的首例重癥患者。他出院的消息與離別時的舉動,讓整個醫(yī)療隊的隊員為之動容、倍感鼓舞。
同日,醫(yī)療隊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登上《新聞聯(lián)播》。
無邊光景一時新
3月,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中醫(yī)藥管理局印發(fā)《關于表彰全國衛(wèi)生健康系統(tǒng)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的決定》,授予10名奮戰(zhàn)在前線的重慶醫(yī)護人員為先進個人。
杜先智作為其中之一,低調地接受了這一榮譽。同事們知道,他一貫內斂,說得少、做得多。
此時適逢抗疫攻堅階段,杜先智繼續(xù)投入全部心力。
被動局面徹底扭轉——病區(qū)的所有患者經過治療,絕大部分轉為普通性。這樣的好消息讓醫(yī)療隊的氣氛恢復了活躍。
杜先智和醫(yī)療隊副領隊賴曉東的防護服,成了隊內才子們的畫布:畫上解放碑、黃鶴樓,寫下“再接再厲把疫趕,柳暗花明定明朝”“漢渝一家親,共飲一江水”等,寄托思念、抒寫斗志。
患者感激他們用生命守護生命,感謝信如雪花般飛來,錦旗也輾轉寄達。
3月23日,東院區(qū)里開展了一場“別樣”的植樹活動。李蘭娟院士和來自全國各地的援鄂醫(yī)療隊員一起,種下寓意“貴人”的桂花樹。
杜先智作為重慶市第三批援鄂醫(yī)療隊代表參與其中,他在樹干系上寫有醫(yī)療隊和隊員名字的名牌,希望以白衣戰(zhàn)士之名,還武漢一個最美的春天。
春天,在盼望中悄然而至。
3月26日上午,醫(yī)療隊負責的兩大病區(qū)“清零”。這意味著,他們可以回家了。
在武漢期間,醫(yī)療隊共收治患者126名,其中重癥患者69名、危重癥患者25名,年齡最大患者95歲;危重癥治愈率達94%,十二病區(qū)連續(xù)43天病亡率為零,十三病區(qū)連續(xù)30天病亡率為零。
他們成為重慶援漢重癥病房堅持最久、撤離最晚的一批隊伍。
出征時,11名重醫(yī)附二院首批援鄂醫(yī)療成員中有8名中共黨員;返回前,另外3名成員被吸收為預備黨員。
返渝前夕,空寂無人的東湖櫻園迎來了杜先智和隊員們。
春光明媚,櫻花似霧。杜先智行至一座紅橋,將外套搭在腕間,神情舒展地面向同事的鏡頭。
走過“天凝地閉”的50多天,杜先智終于有時間看一看這已經到來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