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被遺忘的音樂大師
袁佳敏
1834年,當舒曼在萊比錫聆聽了年僅十四歲的比利時小提琴家亨利·維厄當(Henri Vieuxtemps)的演奏后,發出以上這番感嘆。此后的歲月中,這位技藝精湛且不斷進取的小提琴家,透過自己的演奏和創作,為人們帶來種種耳目一新的感受,贏得了大家的敬重。只是時至如今,維厄當留下的許多作品除仍被廣泛運用于小提琴教學之外,其價值并未受到演奏家和聽眾們足夠的重視,在公眾音樂生活中的影響力也日漸減退。即使是其中最為優秀的作品,也鮮有機會出現在音樂會中,這難免令人感到遺憾。

十九世紀初,意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橫空出世,開啟了小提琴演奏藝術的新紀元。終其一生,帕格尼尼將小提琴的演奏技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將這件樂器的音響潛能發揮到了極致,更為十九世紀器樂作品的創作和演奏中的浪漫主義方向奠定了基礎。受其影響,一股以高度發揮演奏技巧來表現個人才華的風潮席卷整個歐洲。其中,一批法國—比利時學派的演奏家和教師緊跟他的步伐,在繼承維奧蒂(Giovanni Battista Viotti)所建立的古典傳統的同時,他們充分汲取帕格尼尼的技術成就,以此培養出了一大批技巧完美的演奏大師,維厄當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1820年,維厄當生于比利時東部的一座小城維爾維埃。從一開始,這個孩子就顯露出了過人的音樂天賦,他四歲習琴,六歲公演,七歲在列日舉行了第二場獨奏會,緊接著又赴布魯塞爾演出,以神童的姿態頻頻出現在公眾的視野中。在布魯塞爾,維厄當的演奏才能為比利時小提琴學派的奠基人貝里奧(Charles-Auguste de Bériot)所識,此后數年,貝里奧不僅在琴藝上給予維厄當悉心指點,對他的成長也關懷備至。維厄當自身的天才和勤奮,加之恩師的精心栽培,使他的演奏日臻成熟。于是貝里奧帶他到巴黎,師徒二人同臺獻藝,轟動一時。不過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隨著貝里奧即將開始新一輪的巡演,他不能再定期對維厄當進行指導。面對有些惘然無措的弟子,貝里奧叮囑他在往后的藝術生涯中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不要去模仿別人,這讓維厄當銘記一生。
考慮到維厄當那時的演奏已近乎完美,貝里奧臨行前建議他的家人與其再為他尋找新的老師,不如讓他自行安排進一步的深造計劃。于是,維厄當在不斷精進琴藝的同時,開始廣泛接觸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等大師留下的不同形式的作品,并系統地學習和聲、對位等與作曲相關的課程。不久后他終于如愿以償,在父親的陪伴下前往德奧演出、觀光。這期間,他不僅在多個城市一展琴藝,欣賞到了施波爾(Spohr)、梅塞德爾(Mayseder)等前輩的演奏,還結識了許多重要的音樂家,其中包括在作曲方面對他多加指導的西蒙·塞赫特爾(Simon Sechter)教授。這些經歷使年少的他眼界大開。在維也納,他僅用了兩星期時間的準備,就與樂隊合作了當時幾近被人遺忘的貝多芬《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成為作曲家逝世后公演這部杰作的第一人。維厄當憑借其獨具一格的演奏風格和動聽且有力的琴聲贏得了當地聽眾的盛贊,評論界更認為他的詮釋充滿了貝多芬的精神。此后不久,他首次到訪倫敦,當帕格尼尼聽到他的演奏后,欣喜不已,并預言他“前程遠大”。
來到巴黎后,除了繼續活躍于舞臺,維厄當還在名師安東·雷哈(Anton Reicha)的指導下潛心研習作曲技巧。不到兩年時間便完成了《升F小調第二小提琴協奏曲》(Op. 19)。這是一部將莊重的音樂風格和與時俱進的演奏技巧融為一體的作品,篇幅不長,卻在凝練的素材中體現出了全面的創作技法,從中我們不難察覺維奧蒂和帕格尼尼給他帶來的影響。不過相比日后真正成熟的作品,這部協奏曲在配器上仍略顯遜色,維厄當自然也意識到了這點,因此他重新回到布魯塞爾,坐進歌劇院的樂隊中,以便全面了解各種樂器的不同性能和演奏技巧,從而更深入地把握每個聲部的種種細節。正因這種精益求精的態度,他之后所寫的幾部協奏曲既能充分發揮出小提琴獨奏聲部的一技之長,又賦予了樂隊豐富多彩的音響,在兩者間實現了完美的平衡,以此建立起了個性鮮明的藝術風格。
與此同時,維厄當的演奏事業也步入了全盛時期,足跡遍及法國、荷蘭、奧地利、德國、美國、加拿大等各國的舞臺。每到一處,他的音樂會都會立即成為當地文化生活中的盛事。面對舞臺上的他所展現出的輝煌的技巧、華美的音色、崇高的格調和純正的趣味,臺下的聽眾無不為之傾倒。身處浪漫主義風潮盛行年代的維厄當,在追求完美的技巧表現的同時,并不肆意揮灑個人的情感,而是以自己演奏中層出不窮的靈感,以及因對個性化的弓法和指法的嫻熟運用而產生的新穎效果,讓琴聲煥發出與眾不同的光彩和魅力。在演奏曲目方面,他并不僅僅專注于自己的作品,對經典之作的推廣也不遺余力。如果說帕格尼尼當年用盡令人炫目的技巧征服了他的聽眾,那么維厄當則用更為音樂化的表現手法收獲了同樣的效果。即使因年代久遠,如今我們無法通過錄音領略維厄當演奏的原貌,但在他一生創作的眾多作品中,其不拘一格的藝術理念和演奏特征依舊顯而易見。
1846年,維厄當接受俄國沙皇的任命,成為圣彼得堡音樂學院的教授和“帝國宮廷小提琴獨奏家”。盡管此前他早已譽滿全歐,并當選為比利時藝術學院的名譽院士,但正是旅居圣彼得堡的六年,使他不必再受繁忙的旅行演出生活所累,而迎來了創作和教學的高峰。他最重要的幾部小提琴作品大多完成于這一時期,其中藝術價值最高的當屬他在1851年12月首演的《第四小提琴協奏曲》(Op. 31)。

較之當時盛行的許多單純以炫技為目的的協奏曲,維厄當的這部《第四小提琴協奏曲》在展現出高超的演奏技巧的同時,更以高度的幻想性和戲劇性引人入勝。在此他不僅大膽打破協奏曲傳統的三樂章結構,加入了一個技術難度極高的諧謔曲樂章,也進一步增強了樂隊的表現力。無論是高潮迭起的第一樂章、柔美動人的慢板,又或是活躍歡快的諧謔曲、雄渾有力的末樂章,獨奏小提琴與樂隊間始終相輔相成,共同為音樂的發展注入激動人心的力量。起初維厄當對作品的成功與否并無太大把握,也就沒有急于公之于眾,豈料多年后這部構思新穎的協奏曲在巴黎一經首演,立刻備受柏遼茲、柴科夫斯基等同行的推崇,成為演奏家們的最愛。直至二十世紀,海菲茲、弗朗切斯卡蒂、梅紐因、格魯米歐、帕爾曼等小提琴大師仍將之列入各自的保留曲目。特別是海菲茲在1935年留下的錄音,猶如神來之筆,一直被公認為是詮釋這部作品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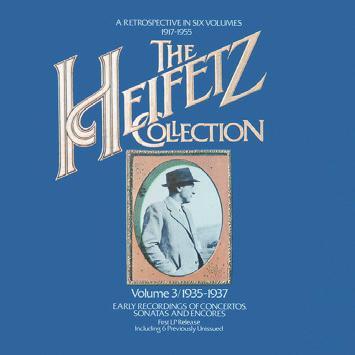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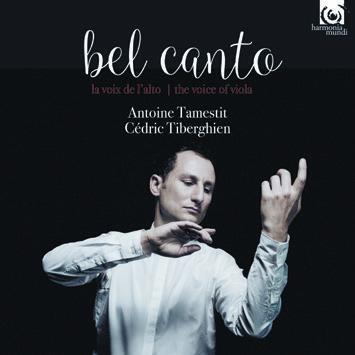

離開圣彼得堡后,維厄當又一次在歐洲各國頻繁巡演,且依舊佳作迭出。1858年,赴美歸來后的他完成了《第五小提琴協奏曲》(Op. 37)。這本是他應布魯塞爾皇家音樂學院教授于貝爾·萊奧納爾(Hubert Léonart)約請,為教學之用而創作的,但它又絕不僅僅是一部循規蹈矩的“學生協奏曲”。除了以明確、多元的手段來實現技巧訓練的目的之外,整部作品從結構到內容都不乏新意。從結構入手,盡管其中三個樂章的情緒不同、篇幅不一,但卻不作間隔,演奏一氣呵成。就音樂而言,這首富有青春朝氣的協奏曲交織著絢麗的色彩和美妙的旋律,在炫技和抒情之間變幻無窮,既能充分發揮演奏者的才能,也帶給聽者極大的滿足。當年柏遼茲在聽到這部作品后就曾評價道:“按照我的理解,這是一部偉大的同時又是非常新穎的作品。”至今,它仍是維厄當所有小提琴協奏曲中上演率最高、錄制唱片最多的一部,也不時被年輕的演奏者們選作參賽曲目。
其實,作為作曲家的維厄當,并不只將目光局限于各類小提琴作品。他對貝多芬弦樂四重奏的熱愛和鉆研,促使他寫出三首同體裁的作品。少年時代豐富的學習經歷,又讓他在為中提琴、大提琴等樂器創作不同類型的作品時均能得心應手。正如他作于1863年的《降B大調中提琴奏鳴曲》(Op. 36),因其唯美的線條和靈秀的氣質而成為中提琴藝術史中一顆閃亮的明珠,備受演奏家們的珍視。從第一樂章那輕柔飄渺、帶有些許冥想色彩的引子開始,聽者就宛若置身于夢境一般。進入主題后,這里的樂聲時而猶疑、沉吟,時而飄灑、歡悅,隨處可見曼妙的風情。第二樂章是一首船歌,透過中提琴獨特的音色流露著些許惆悵之情。最后的“詼諧的終曲”則一掃先前憂郁的情緒,在回旋蕩漾的節奏和旋律中煥發出無憂無慮的意趣。


當年維厄當因妻子埃爾德(Elder)身患疾病而結束了在圣彼得堡的工作,用更多時間陪伴埃爾德。1868年愛妻的病逝給他帶來沉重的打擊,他只能以更忙碌的工作來緩解喪妻之痛。不料五年后維厄當突發中風,致使半身不遂,不得不告別舞臺,將有限的精力投入創作與教學之中。他的兩部大提琴協奏曲就是晚年在病榻上寫成的。這兩部作品中所蘊含的艱深技巧和柔美旋律與他的那些小提琴作品如出一轍,《B小調第二大提琴協奏曲》(Op. 50)更表現出他在臨近生命終點時對生活的眷戀和對藝術的憧憬。有時他還將小提琴的技巧移植到大提琴上來,這對于演奏者自然是嚴峻的考驗。只是與維厄當大多數作品的命運一樣,這兩部佳作如今也已鮮為人知,唯有從大提琴家海因里希·席夫(Heinrich Schiff)或楊文信的錄音中,有心人才能夠領略它們的精彩。
早在圣彼得堡任職期間,身為當地音樂學院教授的維厄當就為培養年輕人才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將當年貝里奧教給他的輕巧而富有彈性的運弓方式,以及自己在駕馭連頓弓時完美而獨特的技巧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還使學生們意識到讀譜的重要性,這些都對日后的俄國小提琴學派影響至深。回到布魯塞爾后,維厄當又接替了那時已雙目失明的恩師貝里奧在音樂學院的教職。直至幾年后疾病纏身,他仍以過人的毅力繼續教學工作,只因他將此視為“神圣的使命”。在學生面前,維厄當是一個嚴格的老師,對錯誤絲毫不能容忍,在音樂處理、藝術趣味等方面也要求甚高。誠如曾受教于他的小提琴大師尤金·伊薩伊(Eugène Ysa?e)所言:“如果沒有充分的技術準備和對音樂的真正感覺,最好不要去找他。他能夠使一個已有相當發展的天才更臻完美,但他不能將就他的學生。”
對維厄當而言,長期奔波于世界各地的巡演生涯固然勞累,卻也使他對旅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即便晚年行動不便,他仍不時出門旅行。未料他的生命也因旅途中的一場意外而走到終點。1881年6月6日,正在阿爾及爾休養的維厄當遭到一名醉酒者的襲擊,受到重傷不治而逝,終年六十一歲。當他的遺體被運回故鄉維爾維埃后,那里的人們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人群中,專程從圣彼得堡趕來與恩師告別的伊薩伊,手捧維厄當生前心愛的瓜內利小提琴走在隊伍的前列。在日后的歲月中,伊薩伊也沿著老師的足跡,不斷將法國—比利時學派的優秀傳統發揚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