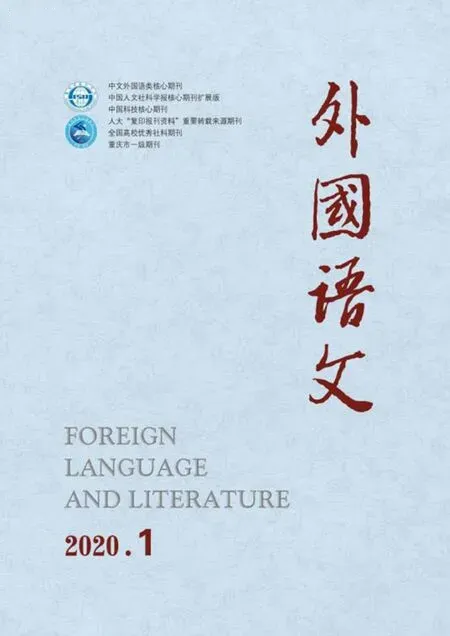框架語義視角下中美貿易戰話語的歷時比較分析
顏冰 張輝
(1.江蘇第二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江蘇 南京.11200;2.南京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江蘇 南京.10097)
0 引言
2018年3月美國宣稱對中國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征收25%和10%的關稅,單邊挑起中美貿易戰,隨后中方予以反制。在此之后,貿易戰局勢一波三折,在沖突緩和與升級之間跌宕起伏。在貿易戰中,中方在不同的局勢變化下采取不同的策略,積極談判或者被迫反制,始終堅持“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的立場。中美是世界兩個最大經濟體,雙方的貿易局勢影響深遠,不僅局限于中國和美國,更緊密關切著世界的利益,中美貿易戰局勢變化也成為世界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因此,2018—2019年對中美貿易戰的研究也成為諸多領域學術研究的熱點。例如,Deng & Feng (2018)從經濟依存視角對中美貿易關系予以定性定量分析,并對中美貿易關系的未來發展提出策略建議。Iqbal et al. (2019)從中美經濟發展和貿易歷史視角對當前中美貿易戰形勢予以分析,預測其貿易沖突難以短時間內解決并深入分析中美貿易局勢對全球經濟貿易的深遠影響。Rhode(2019)根據中美兩國政治經濟形勢發展對2019年中美貿易戰形勢進行預測,認為雙方有很大可能達成貿易協議;Kim(2019)依據國際關系領域內霸權穩定理論和權力過渡理論對中美貿易戰局勢予以分析,認為中美貿易戰的內在動因中政治因素多于經濟因素,主要在于美國對中國實力快速增長的恐懼,因而發動貿易戰遏制中方。此外,他預測中美貿易戰的持續時間可能長于普遍的預期。Kashyap & Bothra(2019)探究了中美貿易關系和導向貿易戰的原因。他們指出中美貿易矛盾可能會持續,這是雙方經濟地位和全球領導力的角逐;并分析中美貿易戰對全球貿易關系的深遠影響。梅新育(2019)從中美政治、貿易歷史角度著手,對中美貿易戰局勢進行評析和展望,指出中美矛盾本質上是守成霸權美國與新興大國中國之間的矛盾,是守成霸權的美國企圖遏制新興大國中國而引發的矛盾沖突,中美史詩級貿易戰是美國遏制中國戰略發展的必經階段,并對未來形勢作出展望:雖然談判之路歷程坎坷并遭遇美方“背約精神”,但應當追尋以合理條件達成貿易協議。由此可見,當前對中美貿易戰的研究多集中于歷史因素、經濟原因、政治動機、國際關系的宏觀分析,并對中美貿易戰形勢予以或積極或消極的預測,而對于宏觀背景下中美貿易戰話語策略的微觀研究較為少見。但是,話語的研究不能被忽略,因為對中美貿易戰事件的建構、立場的表達、信息的傳遞,對公眾的引導皆以話語為基礎。我們認為,宏觀社會政治背景與微觀層面的語言語篇不可分離,中美貿易戰形勢變化下,相應的話語策略也會隨之調整,而語言也蘊含著政治傾向、意識形態。本文將試圖從批評認知的視角并借助框架語義理論來分析宏觀政治背景與微觀話語策略的關系。
1 理論基礎
認知語義學是認知語言學的一個分支,源于對傳統客觀主義世界觀和真值條件語義學的反思,主要探究經驗、概念系統和語言所編碼的語義結構之間的關系。該領域的學者主要關注概念結構(知識表征)和概念形成(意義建構),以語言為透鏡來研究認知現象。認知語義學一個根本問題在于探究概念結構與感知經驗的外在世界的聯系,即通過探索人類與外在世界相互作用及人類對外在世界的意識,試圖建立與人們所感知的世界相吻合的理論(張輝,2011),而框架語義學是認知語義學中一個重要的理論范式。框架的概念由Fillmore(1985)提出,他將“框架”解釋為經驗的組織者、分析的工具,同時也是描述和闡釋詞匯語法意義的工具。闡釋性框架可以導入篇章理解的過程中,它可以被闡釋者或篇章激活。有的框架是固有的,自然出現在人類認知發展過程中,而有的框架則需通過經驗或訓練習得。框架語義學關注知識在理解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對一個句子內在語言意義上的語義分析只是詞匯、語法、語義素材的展示,這種展示形成了闡釋者構建整體闡釋的藍圖(blueprint),而完成整個闡釋的過程需要賦予這個藍圖相應的知識,尤其是已激活或能夠被激活的闡釋性框架的知識,也包括句子所屬的語篇結構的知識,并且語篇中個體詞匯項目和語法構式都促進于構建整體篇章的闡釋。框架概念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已提出,但是當下對它的研究仍有很大繼續推進的空間,比如與批評話語的研究相結合。在話語中,我們參照框架,或部分地通達或激活框架。在話語理解中,我們通過動詞或名詞通達框架,激活的框架或其中一部分為其余部分提供了通達點(access point),從而產生意義建構和情感。Jaworska & Krishnamurthy(2012)和Baker(2014)利用語料庫輔助方法,分別對話語關鍵詞trans、 people和feminism搭配詞予以細致研究以揭示突顯的話語模式和其中蘊含的情感傾向,也體現了對框架思想概念的應用。Knapton & Rundblad(2014)將框架語義學、定位語義學、概念隱喻和轉喻結合闡釋英國飲用水危機話語語篇的概念結構。Shr?ter & Storjohann(2015)基于框架理論在語料庫輔助下對英國媒體2009年financial crisis事件框架構建予以研究。他們將語料庫中financial crisis的搭配詞分配于事件框架下不同的語義描述范疇,包括事件參與者、事件起因、事件變化、影響因素等語義成分,從而探究話語中對事件構建突顯和隱藏的部分。他們對Konerding(1993)歸納總結的事件框架語義范疇描述予以修正和補充,得出了更細化的事件框架語義成分,具體分為:(1)事件發生或起源的條件;(2)事件發揮作用的上義語境;(3)在上義語境中事件所發揮的作用或功能;(4)重要的時期/部分成果;(5)事件的特征;(6)事件中重要參與者;(7)體現事件參與者的重要語境詞項;(8)事件通常發生變化的條件;(9)事件通常的持續時間;(10)事件通常開始的條件;(11)支撐事件的條件;(12)事件重復發生的條件;(13)事件結束或停止的條件;(14)事件所導向的不同狀態或進一步的事件;(15)事件發生對人們所產生的不同的后果;(16)事件發生對人們的意義;(17)相似的事件或事件所歸屬的一般范疇;(18)事件發揮作用的相關理論特征;(19)事件發生所引起的信息特征;(20)指稱事件的其他方式;(21)誰/什么受到事件的影響;(22)事件作為施事者……(23)事件進一步發展的條件;(24)人們針對事件所采取的措施;(25)轉喻詞——事件被視為/被比較為……
總之,國內在話語領域研究中將框架語義理論和批評話語結合的路徑并不充分,Shr?ter & Storjohann(2015)還指出,將話語關鍵詞政治話語分析相融合的方法多見于德語語言學研究,但在英語語言研究領域并未發揮顯著作用,而話語關鍵詞的語義結構影響、反映著人們對所討論問題的認知。話語關鍵詞的使用可以激活相關話語中所固定的知識。框架語義學的方法論啟示人們如何揭示語篇中的知識成分。本文將Shr?ter & Storjohann(2015)所修正的事件框架語義范疇作為模板標準引入中美貿易戰話語的研究中,在此基礎上,對“trade”主要搭配詞語義歸納分類,融入歷時比較視角,從而探究在貿易事件中不同時期對這一事件框架話語構建的不同突顯,蘊含著不同的政策傾向和目的。
2 研究方法
中方2019年6月底至8月底關于中美貿易的話語是我們研究的語料依據。雖然僅有兩個月時間,但其中形勢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成為反映中美貿易戰整體跌宕起伏形勢的一個縮影和例證。具體來看,2019年6月底中美元首在20國集團大阪峰會期間舉行會晤,雙方達成重要共識,宣布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重啟經貿磋商,美方不再對中國產品加征新的關稅。7月底,雙方按照大阪會晤重要共識要求,進行了第12輪中美經貿高級別磋商。這一時期中美貿易戰形勢緩和,釋放積極信號。但是形勢又迅速發生了逆轉,就在中美第12輪上海會談后一天,即2019年8月1日,特朗普便宣稱擬于9月1日起對3 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10%的關稅。作為回應,8月23日,中國宣布對原產于美國的約750億美元商品加征5%—10%的關稅,這一時期中美貿易戰形勢又激烈升級。在這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內,中美貿易局勢就出現多次重大轉折,而中方在應對相應的局勢變化時也隨之對相應的話語進行調整。我們從ChinaDaily中以“trade”為核心搜索詞檢索了兩個時期的相關報道,我們就2019年6月底至2019年7月底期間選取了30篇相關報道,共計19491詞,建立了第一個語料庫,計為語料庫1;就2019年8月選取了30篇相關報道,共計17799詞,建立了第二個語料庫,計為語料庫2。其中,語料庫1“trade”出現頻次242次,語料庫2“trade”出現頻次220次。我們將兩個語料庫文本分別導入AntConc 3.4.3,檢索“trade”左右五個詞距之內的搭配詞,將搭配頻次10次及以上并排除功能詞外的詞項一一統計。首先,我們將被統計的詞項分別用R語言繪制詞云圖,對兩個不同時期“trade”主要搭配詞詞頻分布進行整體感知和分析,隨后,依照Schr?ter & Storjohann(2015)修正的事件框架,將被統計的搭配詞歸入相應的語境描述范疇,分別以表格形式呈現,對未有詞匯填充的語境描述范疇,將不在表格中予以呈現。該表格為微觀細致分析的主要依據。
3 比較分析
根據兩個語料庫中話語關鍵詞“trade”主要搭配詞詞頻分布所繪制的詞云圖,如圖1、圖2所示。

圖1 語料庫1 “trade”主要搭配詞詞云圖

圖2 語料庫2 “trade”主要搭配詞詞云圖
通過詞云圖的直觀展示,我們可以獲得對兩個時期主要搭配詞詞頻分布的整體感知。在語料庫1 中,中美貿易雖然仍處于戰爭、摩擦期,但是顯然此時期側重于雙邊和談、達成協議的態度,注重激活貿易事件框架中和平解決問題這一積極特征,而在語料庫2中,很明顯,中美貿易戰摩擦態勢在升級激化,談判的作用隨著局勢的突變而被弱化,這一時期更為注重激活貿易事件框架中問題的激化特征。
在對搭配詞整體感知基礎之上,我們把具體的搭配詞匯按照Schr?ter & Storjohann(2015)修正的事件框架語義范疇予以細致分類和比較分析。我們的研究以詞匯為切入點,但對詞匯的分析不是孤立的,而是融入整個話語語境、知識背景中,即通過搭配詞突顯模式的分析把語言結構與話語意義和知識相結合。

表1 語料庫1中“trade”主要搭配詞
語料庫1(見表1)中,“deficit”這一搭配詞點明了中美貿易事件發生的起因,即美方把其貿易赤字歸咎于對中貿易,因而挑起中美貿易戰。語料庫1著重突出中美貿易事件框架中的時期特征和參與者部分。從時期特征來看,這一時期的特征是在貿易摩擦矛盾的背景下,要重啟和談,力圖達成協議。“talks”“negotiation”這類詞匯向公眾傳遞了積極信號,引導公眾對大阪會晤后的中美貿易局勢進行樂觀展望,支持關注即將到來的中美第12輪高級別磋商。“restart”“resume”這類詞匯也體現了這一時期的特征,“re”詞綴表示再一次,即指中美貿易戰發生的這一年半時間里,雙方曾經進行過會談,因各種原因而未能達成最終協議,現在基于大阪共識的推進,雙方需要努力再次談判磋商。從事件參與者成分來看,除了“China”“US”使用較多之外,還多處使用了“two”“countries”,后者雖然在語義中仍然指中、美這兩個貿易事件行為主體,但顯然已經弱化了中美對立性,強化整體性,強調貿易戰爭沖突發生在這兩個國家,但同時這兩個國家也產生了解決問題的共識,并要依靠兩個國家的共同努力和平談判,達成協議。與這一點相輔相成的是事件特征詞匯“bilateral”的使用,“bilateral”表征中美貿易具有雙邊雙向特征,強化了合作性和共識性,傳遞了雙邊友好會談的信息,引導公眾不僅著眼于當前的摩擦沖突,更要看到中美貿易的共同利益和相關共識及達成協議的共同夙愿。中美貿易事件特征描述詞中還有“economic”“not”,其中,“economic”即表明中美貿易問題屬于雙方經濟關系領域。否定詞“not”在與“trade”左右五個詞距內出現13次,其中,五次是對貿易談判相關信息的表述,表明雖然當前談判時間安排和最終結果尚未明確,但是雙方承諾不再另增關稅,不再升級貿易戰,這有利于清晰引導公眾及時把握局勢訊息。與前文所分析的時期特征描述相輔相成,即中美雖處于矛盾狀態,但會通過協商解決問題,希望公眾能對貿易事件發展的結果有較為樂觀的期待。此外,“not”有三次出現的語境是對美方將其貿易赤字歸咎于對中貿易觀點的否定,另有五次出現的語境是對貿易戰所帶來不利影響的表述。這八次否定詞應用的語境信息是中方一貫堅持的立場觀點,但是置于當前即將開啟會談的背景下又有特定的意義,強調美方將貿易赤字歸咎于對中貿易的錯誤性表明中方積極尋求談判磋商不等于放棄原則立場,強調貿易戰的不利影響,更強化了尋求和平協商解決問題的必要性。事件影響者組成成分中,中方話語中突出了“world”,其中,有六次出現的語境是表明中美達成大阪共識,即將開展貿易談判對世界是一個有利消息,這一舉動得到世界的贊揚;有五次出現的語境表明中美在世界的重要地位,即世界兩大重要經濟體;有兩次出現的語境是表達中美貿易摩擦對世界的不利影響。“world”一詞直接體現了中美貿易這一事件絕不僅牽涉中美,更對世界有深遠影響,貿易戰影響整個世界,而和平談判達成協議是整個世界的期盼,得到世界的支持和擁護。與針對事件所采取的措施相關的詞匯有“said”“deal”“agreed/agreement(s)”。“said”在文中是對人們分析事件觀點的引用,由于對問題的分析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步驟,我們也把它歸于表征對事件所采取的措施這一范疇框架。值得注意的是,“deal”“agreement”這類詞匯與“trade”搭配頻率較高。協議是解決貿易問題的具體化、實際性的措施,它在此階段多次被提及,突顯了當前貿易戰局勢處于沖突降溫、解決問題的態勢,從而引導人們對最終結果產生積極期盼,支持中美進一步的磋商會談。
語料庫1對于中美貿易事件框架中突出強調在戰爭沖突中談判的時期特征和參與者的雙邊雙向并側重于以具體實際方案解決問題,這樣的話語策略引導人們激活貿易事件框架中具有積極屬性的內容,如雖然中美在貿易方面產生摩擦,但是緩和沖突,穩定雙邊關系,解決問題是主要趨勢,從而激發人們對中美進一步磋商,達成協議的支持、關注和期盼。
語料庫2(見表2)對于貿易事件框架成分中最為側重的仍是時期特征和事件參與者的構建,但是具體的詞匯表征和感情色彩與語料庫1有顯著差異。語料庫2處于局勢突變的時期,8月1日特朗普宣稱擬于9月1日起對3 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10%的關稅打破大阪會晤后形成的積極局面,情況發生逆轉,中方被迫調整態度并于8月23日做出反制回應。體現此階段時期特征的描繪詞主要圍繞表達戰爭沖突含義的詞匯,如“war”“tension”“friction”“dispute”,出現頻率高于語料庫1中相應詞匯,甚至還出現了在語料庫1的搭配詞中未出現的“escalating/escalation”,直接點明這一時期的中美貿易戰升級局勢,發生了顛覆性、逆轉性變化。此外,與“trade”搭配出現18次的“talks”有13次出現的語境都是譴責特朗普在第12輪會談后一天就擬對中加稅的行為嚴重違背其會談諾言,并增加了未來會談形勢的不確定性。另外五次“talks”出現的語境是指中方有誠意進行會談,這一直是中方堅持不變的立場,但是會依據形勢變化調整其傾向和政策導向,當前在特朗普背約升級貿易戰,加強貿易沖突的背景下,中方貿易政策比起前一時期對談判傾向性相對減弱并被迫采取反制措施。在對事件參與者構建中,除了表示中美雙方的詞匯,還有與trade搭配11次的“Trump”,這與語料庫1有著重大差異。在此時期,對貿易事件參與者的激活不再著力強調雙邊雙向,反而強調“Trump”這一個體化名詞。這11次出現的“Trump”語境都表明特朗普無視談判約定,再次發起貿易戰,如:The tariffs supposedly on $300 billion worth of US imports from China were announced by US PresidentDonaldTrumpafter Julytradetalk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n Shanghai(2019-08-15)。

表2 語料庫2中trade主要搭配詞
對貿易事件參與者構建中強調特朗普本人意在引導公眾感知理解貿易事件框架時,明確此時期中美處于貿易戰升級狀態的責任和原因在于特朗普,希望公眾對中方迫于形勢的反制政策予以理解支持。對事件特征描述的搭配詞仍然是“economic”“not”。“not”出現的11次中有三次表示貿易談判進展不順利,體現了當前的時期特征。另外,有一次表示中美關系不應局限于貿易矛盾,有兩次表示美方對中貿易威脅不會得逞,有兩次表示反對雙方打貿易戰,有三次表示貿易戰的不利影響,這八次表明的是中方一貫的立場。這兩個語料庫對于事件特征的話語構建并沒有太大差異,這正說明雖然形勢會改變,但中方對于貿易事件的認知、立場、原則是不變的,只是因時勢變化對相應的政策傾向予以調整。搭配詞“policy”出現11次,這11次都特指特朗普對中貿易政策,大多出現在特朗普8月1日宣稱的對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10%關稅這一背景下。這是此時期事件形勢走向發生顛覆逆轉的直接原因和條件,需要突出強調的是,中方隨之采取的反制措施的合法性理據。此外,“policy”前后搭配多次出現“misguided”“mistakes”“criticize”“no direction”,鮮明地傳遞了中方立場,即對特朗普背約加稅行為表示強烈地批判和譴責。“no”出現的語境多是表明貿易戰不會產生贏家,是對事件所導向后果的判斷,如:The trade war serves no one(2019-08-24)。
在語料庫2的時期背景下,對特朗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更具有警示作用。對于事件所采取措施的話語構建,此時期僅有“said”,即相關人士的分析,并沒有太多具體的方案計劃,這與語料庫1形成鮮明對比,因為語料庫1應用了較多表示協議的詞匯,強調中方積極會談促成雙方貿易矛盾的解決。但是語料庫2中形勢發生了逆轉性變化,由于特朗普在談判后突然宣稱對中加稅,使得隨后貿易形勢由先前降溫態勢轉變為升級態勢,從而與解決問題有了更遠的距離,因而在語料庫2中對事件問題解決的語義結構并不充分,這是這一時期的特定形勢所決定的。
4 結論
通過以上對圖表的分析,我們繪制結構圖來表明兩個不同時期的語料庫在不同形勢下在話語上對于貿易事件框架構建的不同側重和策略,如圖3所示。

圖3 語料庫1和語料庫2貿易事件語義框架圖
對中美貿易戰這一事件框架下,語料庫1和語料庫2由于處于不同的局勢背景,對其語義框架的構建有所不同。圖中左側表示語料庫1的主要語義框架,右側表示語料庫2。我們發現:語料庫1和語料庫2都強調了時期特征和事件參與者,但語料庫1主要表征貿易沖突處于降溫時期,而語料庫2突出貿易沖突處于升級狀態。語料庫1強調中美兩個事件主體的雙邊雙向、一體性,而語料庫2中這兩個事件主體更具有對立對峙性;語料庫1強調了深受中美貿易形勢影響的“世界”以突顯中美貿易戰影響的廣泛性和深遠性,以證明中美雙方通過和談達成協議乃世界所愿。語料庫2強調了形勢突然發生逆轉,和談又出現波折的原因在于特朗普違反約定,肆意對中加稅的貿易政策,從而獲得公眾對中方被迫反制的理解;在對解決貿易問題措施的語義構建中,語料庫1有清晰具體的詞匯表述,而語料庫2未有具體措施類詞匯。這也是由形勢變化所決定的,語料庫2中由于特朗普突然背約逆轉了中美貿易形勢,為問題的解決增加了更多不確定性。但是,雖然形勢在戲劇性急劇性地發生著變化,中方對于中美貿易戰的立場卻沒有變,即: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這也反映在相應的語義框架中,如兩個語料庫中都強調貿易戰是中方經濟領域問題,美方將其貿易赤字問題歸咎中方是錯誤的,貿易戰產生諸多不利影響等,表明中方一向不希望事態擴大,希望依靠和平談判解決貿易問題。但是,根據不同的局勢變化情況,政策的側重會有所不同,語料庫1是積極促成和談,延續大阪共識這一重要成果,因而對整個貿易事件框架的構建更突顯積極的情感傾向;而語料庫2針對特朗普突然宣稱對中加稅損害雙方先前談判成果,中方被迫采取了反制措施,因而對整個貿易事件框架的構建更凸顯其消極的情感傾向。對中美貿易戰話語的研究表明了宏觀社會政治背景的變化會影響相應的語篇話語,而通過語言信息和證據又可產生對宏觀背景的理解。在對某一事件的話語構建中,我們可以以話語關鍵詞作為詞匯節點,研究其相應的語義網絡,從而清晰認識相關事件表征的話語策略,借助語料庫輔助和歷時比較分析的手法更能凸顯宏觀社會政治背景變化對話語層面語義框架產生的影響,并且對話語關鍵詞的語義研究不可脫離整體語義網絡和宏觀知識背景。希望本研究能借此吸引更多學者在框架語義學、批評認知視角下關注話語研究,對此作更深入的闡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