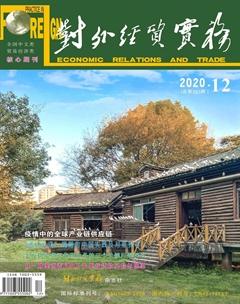全球產業鏈視角下中國制造業的升級障礙與對策
張彥 劉美玲
摘 要:創新驅動為中國制造業突破“低端鎖定”提供指引,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成效顯著。但當前發達國家正在重新布局制造業全球產業鏈,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大。此背景下,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道路并不平坦,將面臨來自宏觀(戰略建構障礙)、中觀(體系重塑障礙)、微觀(技術突破障礙、渠道重構障礙)等多重升級障礙。因此,中國應在避免“路徑依賴”、深耕“區域鏈”和“創新鏈”、聚焦“人財物”和培育“內外需”方面進行有效應對。
關鍵詞:全球產業鏈;創新驅動;制造業;轉型升級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比較優勢,深度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中,并培育出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制造”產業群。但近二十年來,世界經濟發生深刻變革,全球產業鏈已取代傳統國際分工,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為適應新形勢,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成為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新動力機制”,它不僅為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升級注入“新動力”,其“五新”指向(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新業態、新市場)亦為突破“低端鎖定”提供指引。不過,在全球產業鏈中,中國制造業實現轉型升級并非易事,擺在面前有許多凸出的現實困境。當前影響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核心障礙是:發達國家已經提前布局,企圖全方位壓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在此背景下,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實現轉型升級將會遭遇什么影響和困境?應當如何有效應對?
一、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升級障礙
當前,鑒于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大,中國制造業的升級之路并非坦途,可能遭遇各種困境和障礙,影響中國制造業的升級效率的同時可能誤導升級方向,掉入發達國家提前設計的“路徑依賴陷阱”。當前,在全球產業鏈中,中國制造業的升級障礙包括:宏觀(戰略建構障礙)、中觀(體系重塑障礙)、微觀(技術突破障礙、渠道重構障礙)。
(一)戰略構建障礙
創新驅動是中國實現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戰略基石,可以預見,隨著“中國制造2025” “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目標的逐步實現,中國制造業將會進入全球產業鏈的中高端,并且能夠重構和實現自我主導的制造業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
不過,我們不能用靜態的眼光來看待這一問題,因為當前擺在中國制造業面前最大的障礙是: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戰略。迫于危機感,發達國家紛紛提出了再工業化戰略,比如:美國提出的“再工業化戰略”、歐洲提出的“2020戰略”、德國的“工業4.0戰略”、英國的“高價值制造戰略”、法國的“新工業法國戰略”、日本提出的“重生戰略”等。
當前,全球產業鏈分工體系已不再局限于其“經濟內涵”,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賦予了其更多的“政治戰略內涵”。全球產業鏈不只局限于國際分工體系,更是國家權力博弈的競技場。發達國家之所以重啟再工業化戰略,是因為寄希望于利用高端制造業的優勢,重構其在全球產業鏈的霸主地位,從而獲得更多的權力。這給中國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造成一定的影響,而且也將使中國制造業的升級陷入發展困境。一方面,如果中國制造業成功轉型升級,那么中國與發達國家制造業間的差距將減少,將導致發達國家的“相對收益”減少,這一結果與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如果發達國家重構了制造業的全球產業鏈,那么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步伐將會被打亂,將可能重新進入“低端鎖定”狀態。
(二)體系重塑障礙
中國是多邊貿易體系的受益國,在WTO框架下中國在國際貿易領域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在WTO改革和國際經貿規則重構方面做出積極貢獻。然而,當前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系正在遭受來自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沖擊和腐蝕。發達國家正在推動國際經貿規則的變革,進一步削弱中國的國際經貿規則話語權。
首先,“規則爭奪戰”引領全球產業鏈主導權的變遷。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是制造業全球產業鏈的主導者,其通過不同類型的治理模式實現對產業鏈體系的控制。當前,發達國家積極實施“高端制造業回流”戰略,旨在爭奪全球產業鏈的某一行業規則主導權或者成為標準制定者,以達到長期占據制造業的高端分工地位。對于新興經濟體來說,要想實現全球產業鏈分工地位的提升,不僅需要有強大的跨國公司網絡,更需要在高端制造業行業領域有標準制定權。就目前來看,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制度性話語權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有較大差距。
其次,發達國家利用規則變遷實施“精準打擊”。2008年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通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服務貿易協定(TISA)來引領新一輪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從而試圖主導新的全球經濟貿易規則,建立所謂“高標準、高質量”的區域性貿易安排來遏制中國的發展。雖然美國最終放棄了TPP,但我們仍可以看到美國的遏制痕跡,它寄希望于通過“原產地、國企、勞工、環保”等方面的規則制定,讓跨國公司實現產業鏈布局的調整和重構,從而對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制造業發展造成負面沖擊。
(三)技術突破障礙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要實現全球產業鏈分工地位的提升,培育并獲得先進的技術是其中的重要路徑。然而,技術創新越來越依賴資本和技術的積累,特別是技術積累,而技術能力的積累和發展是一個漫長、艱苦的學習過程,因此,“學習-積累-創新”是發展中國家實現技術創新的必經步驟。這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不僅可能陷入升級目標“迷失”問題,而且還隨時面臨發達國家在技術層面的“創新圍剿”。
首先,中國制造業將面臨“內生”的技術依賴陷阱。國際貿易中的技術差距論認為,發達國家依靠技術比較優勢與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但由于“技術溢出效應”的發揮,技術差距將不斷消失,最終發展中國家將會完全掌握該項技術。不過,發展中國家對技術的掌握有明顯的“時滯”,待發展中國家完全掌握了該項新技術后,該技術的附加值已經明顯降低,而發達國家也研發出更為先進的技術。實際上,在發展中國家掌握了該新技術并能夠獨立生產之時,該產品已經走到了產品生命周期的末端,這實際上就陷入了內生的技術依賴陷阱。在當前發達國家實施再工業化戰略的背景下,傳統“學習-模仿-升級”道路的效率將大打折扣,而取得全面的技術創新又需要長期的時間積累。因此,這種內生的技術依賴陷阱危害被放大。
其次,中國制造業將面臨來自發達國家的“創新圍剿”。第一,發達國家通過強化技術保護,鞏固了全球產業鏈的實際控制權。當前,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地位比較低,這是不爭事實。根據歐盟統計局對制造業的技術層次的分類,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均集中在中低技術和低技術制造業。從國際分工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優勢產業集中在產業鏈中的加工制造環節。因此,從升級路徑來看,中國制造業的升級要逐步擺脫低端的加工制造業環節,向高端的零部件生產和產品研發設計領域升級。不過,由于發達國家在中高端技術制造業領域(如:電腦、通訊、電氣、醫藥、技術設備、機動車輛、運輸設施等)有很強的控制力,并且不斷強化產業鏈治理,中國制造業要向獲得更高的分工地位將面臨很大的助力。第二,發達國家干擾中國的技術研發。發達國家為了保持其技術比較優勢,減弱技術和知識的外溢,頻繁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研發干擾。以中國通信行業中的華為和中興為例,美國不僅長期對中國通信行業進行技術封鎖,而且還通過政治手段干擾并削弱其技術研發能力,從2018年至今,美國對中國的中興通訊、華為等高科技行業企業進行制裁,這就是企圖干擾中國技術進步的表現。第三,發達國家通過制造業“雙轉移”,制約中國的技術創新發展。一方面,高端制造業向發達國家回流,影響了“技術擴散效應”的延續性。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西方經濟學家給出了方案: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干中學”和“技術擴散”來實現升級。然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了吸引高端制造業回流國內,制定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例如:美國通過金融手段(美聯儲持續加息)和財政手段(2017年底通過的《大規模減稅法案》),吸引高端制造業資本回流美國。又比如: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巨頭通用、福特、豐田、夏普等大規模遷回本國。另一方面,低端制造業轉移。隨著東南亞和南亞部分國家的經濟不斷開放,其自然、人力、土地等資源的優勢吸引了部分跨國公司的資金,中國在低端制造業上的人力資源比較優勢不再。因此,發達國家利用各種手段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創新圍剿”。
(四)渠道重構障礙
長期以來,由于不重視對品牌和營銷渠道的建立和維護,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體系中顯得非常脆弱,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如果只關注科技層面的創新,忽視商貿流通領域的創新,則無法建立起與“高端制造業”相匹配的“高端商貿流通平臺”;而如果不重視在國際貿易中樹立品牌意識,則無法真正實現全球產業鏈分工地位的有效提升。因此,除了通過“供給側推動”的技術升級路徑以外,“需求側”重構“高端品牌”和“高端商貿流通”渠道系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另一條重要路徑。不過,發達國家也在“需求側”對中國制造的出口渠道進行了“精準打擊”。
首先,發達國家通過優勢地位削弱中國的創新能力。由于中國出口的制造業產品被長期鎖定在低成本生產模式,且發達國家利用其品牌和渠道的優勢,通過跨國公司強化國際購買指向來影響下游廠家對中國制造的購買,精準打擊了中國本土制造業的創新能力。通過對部分國內具有代表性的中小企業關于“創新動能”的調研情況來看,自主創新的“資金需求大、風險高、收效慢”是中小企業創新動能不足的根本原因,這實際上也反映了發達國家利用其品牌和渠道優勢,對發展中國家創新精神的一種削弱。
其次,發達國家提高準入門檻對中國創新能力進行“精準打擊”。從需求渠道來看,外部依賴性強是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制造業產品出口的重要特征。歐美市場是中國制造業最重要的出口市場,而出口渠道又都掌握在歐美國家手中。這種不對稱的相互依賴關系勢必會導致權力關系的不均衡,權力相對弱勢的中國容易受到發達國家的干擾。以TPP為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通過TPP等提高制造業的準入門檻,其目的主要是擠占“中國制造”在亞太地區的市場優勢,以維持亞太市場對美國高端制造的依賴,收效顯著。從統計數據來看,2008年以前美國對TPP國家的高端制造出口比重出現下降趨勢,而2008年之后這一趨勢出現了根本性改變,僅2009-2013年其比重就從24%甚至近28%。相反,TPP成員國中的中國制造出口比重出現明顯的下降。這就意味著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規則和貿易渠道的控制權,對中國制造業的出口進行干擾。
再次,發達國家利用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創新能力進行“精準打擊”。2016年以來,經濟民粹主義在歐美發達國家盛行,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后,掀起了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美國將貿易保護主義的第一槍指向了中國,通過系列非市場手段打擊中國制造。根據美國商務部在4月公布的《建議加稅清單》可以發現,其制裁、調查和建議加稅領域與中國支持的高新技術發展產業名單完全重合。因此,美國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是蓄謀已久且非常具有針對性的,即利用貿易渠道優勢對中國高端制造業進行打擊,其目的在于削弱中國的創新能力。
二、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升級對策
(一)宏觀:避免“路徑依賴”,防范“創新壓制”
與過去僅通過技術層面壓制中國形成“技術路徑依賴”從而實現“低端鎖定”不同,在全球產業鏈中,中國遭遇的升級路徑障礙是全方位的。在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戰略背景下,全球產業鏈也將發生深刻變化,其所帶來的“創新抑制效應”明顯。發達國家希望中國制造業按照它們所設計的路徑轉型升級,但這容易誤導中國的升級方向,并且落入“路徑依賴陷阱”,最終重新被“低端鎖定”。
因此,需要對全球產業鏈的發展以及中國制造業發展的內外環境進行全面評估。宏觀上,應在戰略上“韜光養晦”。當前,發達國家對全球產業鏈主導權的爭奪非常激烈,因此,應當避免在戰略上與發達國家出現正面沖突,亦要防止發達國家聯合進行的“創新壓制”,避免在發展理念、發展方向和發展理論等方面落入“路徑依賴陷阱”。中觀上,一方面,應警惕當前多邊貿易體系遭受“侵蝕”的情況,中國應在WTO改革和維護多邊貿易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應加快國內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培育新的產業經濟增長點。微觀上,應維持“供給側-技術”與“需求側-渠道”的均衡發展。一方面,防止出現“創業有余、創新不足”的雙創不均衡局面;另一方面,防止出現“技術部門創新”和“商貿流動領域創新”不均衡發展的局面。
(二)中觀:深耕“區域鏈”,瞄準“創新鏈”
在戰略上的“韜光養晦”并不代表“無所作為”,筆者認為中國在“區域產業鏈”和“區域創新鏈”上可“大有所為”。一方面,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深耕和重塑“區域產業鏈”是更為務實的選擇。中國與海上絲路沿線的東南亞國家有較為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在這一區域建構中國為中心的區域分工體系是有現實基礎的。而且,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契機,建構并打造“東南亞海洋國家-粵港澳大灣區-廣西云南-東南亞內陸國家-南亞國家”的區域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將為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提供“區域經驗”和奠定堅實基礎。另一方面,瞄準“創新鏈”,徹底擺脫“路徑依賴”。創新是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動力源泉,也是新型產業競爭力和比較優勢的內在體現。人工智能、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術、區塊鏈等都是全球創新鏈中的重要環節,亦是中國最有可能實現突破的領域。只有實現技術創新,特別是突破“卡脖子技術”甚至成功掌握顛覆性技術,才有助于中國制造業實現轉型升級,重構有利于自己的制造業產業鏈。
(三)微觀:聚焦“人財物(務)”,培育“內外需”
一方面,“人財物(務)”(人才、資金、貨物、服務)是中國制造業實現轉型升級的基礎。一是要通過政策,吸引國內外創新創業人才,并進一步形成“人才聚攏”效應。二是要引導金融市場和使用金融工具為創新型企業研發提供足夠通的資金支持。三是重視在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領域協同發展。服務貿易是全球產業鏈的關鍵環節,也是中國當前較為薄弱的環節,除了提升有形商品的附加值外,在服務行業產業分工領域占據一定地位亦是關鍵。
另一方面,加快“內外需”的培育步伐。一是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深入挖掘沿線國家的消費需求,既為“高端中國制造”尋找外銷出口,又能使制造業企業加速完成資本積累并實現產業升級。二是要通過消費升級來實現“內需擴大”,特別是引導和培育國內消費者購買“國貨”,這亦是規避全球貿易保護主義風險的重要路徑。三是充分發揮“市場在中國(sold in China)”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作用,合理利用市場準入規則來防范“鏈主國家”的“創新壓制風險”,亦能在涉及經貿沖突的時候增加“談判籌碼”。
參考文獻:
[1] 張彥.美國貿易霸凌主義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與應對[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8(6):167-173.
[2]保健云.大國博弈中的全球產業鏈分化重構[J].學術前沿,2018(18):45-55.
[3]林致遠.全球產業鏈去中國化趨勢及應對[J].河北學刊,2020(7):141-146.
[4]劉志彪.從全球價值鏈轉向全球創新鏈:新常態下中國產業發展新動力[J].學術月刊,2015(12):5-14.
[5]黃先海,余驍.以一帶一路建設重塑全球價值鏈[J].經濟學家,2017(3):32-39.
[6]黃興年,王慶東.國際貿易新規則的制度非中性與中國產業升級路徑選擇[J].國際貿易,2016(3):14-21.
[7]陸燕.在全球價值鏈中尋求制度性話語權-新一輪貿易規則重構與中國應對[J].人民論壇,2015(12):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