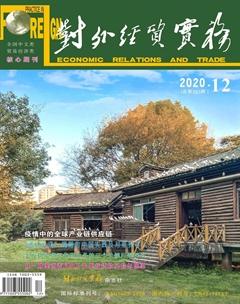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糾紛的類型鄢梢蚣岸圓
楊詠婕
摘 要:隨著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發生的投資糾紛也日漸增多,糾紛類型也呈多樣化趨向。總體看,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糾紛頻發,一方面與我國企業自身的不夠重視投資法律風險有關,另一方面與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及政策有關。基于此,我國企業應該從提升合規管理水平及選擇糾紛解決機制等方面,政府應該從加強國內立法以及加大投資糾紛解決國際合作力度等方面來確立化解策略。
關鍵詞:企業;海外投資;糾紛;法律合規
隨著“一帶一路”倡儀的推進,我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日漸加快,對外投資的規模日漸擴大。截至2019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20674.6億美元,較上年末增加851.9億美元,是2002年年末存量的70.8倍,在全球中的占比由2002年的0.4%提升至6.96%,排名由第25位攀升至第三位,已成為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在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相關政策的引導下,我國企業海外投資成果極為顯著,如聯想并購IBM、吉利收購沃爾沃等,這些成功的案例激勵更多的企業“走出去”,但在海外投資中也引發了較多的糾紛,如華為與思科的訴訟、平安公司與比利時政府的糾紛等等。這些糾紛表明,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存在較大的風險,需要提高警惕。本文立足于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糾紛類型,分析產生投資糾紛產生的原因,進而在此基礎上探尋相關的務實策略。
一、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糾紛的類型
(一)按糾紛主體劃分的類型
從糾紛主體上劃分,我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糾紛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中國企業與外國法人、自然人之間的糾紛,一類是中國企業與外國政府之間的糾紛。我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除了在海外設立獨立的分支機構從事經營活動之外,還有承接海外項目(多數是工程類項目)、兼并海外企業或生產線、在國外獨資或合資新建企業。在這些投資活動中,與外國法人、自然人在投資合作中產生的糾紛占據投資糾紛的大部分。因東道國政府的行政行為或行政合同引發的中國企業與外國政府之間的糾紛也不少。如2018年,浙江臥龍礦業公司等三家中國企業因為采礦許可證未及時年間被蒙古國政府吊銷,三家中國企業通過外交途徑協商無果后,將糾紛提交給國際仲裁法庭仲裁,仲裁結果至今沒有公布。
(二)按糾紛性質劃分的類型
1.商業活動引發的投資糾紛。具體而言:第一,合同糾紛。合同作為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合意表達,是平等民事主體之間交易的契約。作為交易契約,合同本身是投資的保障與憑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投資行為均需要依照合同開展,海外投資更是如此。然而海外投資容易受到多重風險的影響,降低了締約不當或履約能力。第二,知識產權糾紛。近幾年,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糾紛有50%以上是知識產權糾紛。統計數據顯示,從2010-2019年外國政府和企業對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經營中發起的知識產權調查及訴訟量不斷增加,僅美國政府對中國企業在美投資過程中發起的知識產權調查和訴訟案件就達到了106起。第三,勞資糾紛。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中無論是新建投資還是并購投資,維持穩定的勞資關系都是確保企業后續順利經營的基礎。調查數據顯示,2010-2019年間中國企業70%的海外并購失敗案例均與勞資糾紛有關。
2.非商業活動引發的投資糾紛。海外投資迥異于國內投資,東道國的政治、經濟及文化風險千差萬別,不同的風險均可能會引發非商業性糾紛。如東道國的政權更迭、戰亂或是國內經濟不穩定引發的國有化、征收等,這些均可能會產生較大規模的投資糾紛。如2008年,比利時政府按照歐盟的決定以換股形式將富通集團的銀行業務劃轉給巴黎銀行,作為單一最大股東中國平安公司至少要損失320億元,中國平安公司2009年不得不將比利時政府告上布魯塞爾法院,布魯塞爾法院在2012年作出的結論是中止劃轉,此后該案一直沒有進展,歷時11年的訴訟至今依然沒有結果。中國平安公司訴比利時政府這一典型的征收不當案件,對中國企業在海外的金融投資敲響了警鐘。
二、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糾紛的成因分析
(一)中國企業法律風險意識較低
1.合同風險識別能力不足。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所簽訂的合同,大多是依照東道國的法律或是國際通行規則訂立的。在這個過程中因對東道國的法律以及國際社會通行規則了解不夠,難以把握。如締約條款不當或存在法律缺陷與漏洞,會引發較大的投資經營風險。2017年中國遠洋集團因巨額虧損拒付船租糾紛就是因為在當初訂立船舶租賃合同時,與英國環球租船公司(Global Ship Lease)簽訂遠期租賃協議中美元加入“對沖風險條款”有關,導致在糾紛發生后喪失了為自身抗辯的理由。另外,合作方的資信較差造成的履約能力不足或是履約不適當也是海外投資糾紛頻發的重要因素。如2014年四川長虹電器集團與美國電子消費公司(Apex)之間的投資糾紛就屬于此例。糾紛發生后,長虹電器集團委托美國鄧白氏資信調查公司(Dun & Bradstreet)對Apex進行資信調查,結果顯示該公司除了從其他企業賒賬過來的零售商品之外,并無資產。由此,就造成了Apex公司無法履行與長虹集團所簽訂的合同,造成長虹集團虧損13億美元。
2.知識產權風險意識較差。知識產權是提升企業國際競爭力的保障,發達國家眾多的百年企業之所以能夠屹立不倒,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其有自身核心的知識產權,包括核心技術及商標。客觀而言,我國企業并不重視知識產權管理,對核心技術包括發明、專利的作用認知不足,對自身品牌發展沒有建立長遠規劃。造成這些認知或管理上的問題,根源還是在于我國企業知識產權開發能力不強,核心技術創新力有限。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19年全球知識產權指標》中的排名顯示,中國159.6萬件的專利申請成為全球專利申請第一大國。然而福布斯發布的“2018年全球最具創新力企業百強榜單”,美國企業共51家,占比超過50%,中國有7家企業上榜,包括騰訊、百度、恒瑞醫藥等企業,而且上榜的中國企業創新力指數排名比較靠后。中國企業雖然擁有全球最多的專利數,但在專利轉化成功率、專利組合的創新力以及專利延伸的影響力等方面,與發達國家企業相比完全不占優勢,而且大部分專利并不是屬于核心技術領域。正是因為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不足,使得中國企業屢屢成為侵權被告。
3.輕視勞資合同風險。勞資關系事關企業穩定,對于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而言,也事關投資及后續經營的穩定。因東道國的勞動法律、勞動者思維習慣與我國勞動法、企業文化存在較大的差異,很多企業對此種差異不夠重視,思想準備不足,習慣性地照搬國內做法造成勞資糾紛的頻發。具體而言:第一,不了解東道國的勞動用工制度。如煙臺萬華化學集團在兼并匈牙利博蘇化學公司的時候,辭退了幾名匈牙利籍員工。按照匈牙利的《勞資關系法》,在員工沒有觸犯法律或對企業造成重大損失,不能隨意解雇員工,由此給萬華化學引來了沒完沒了的官司,也降低了萬華化學在東歐國家的影響力。第二,勞動工資標準不符合東道國的勞工法律。2019年南非有各類中資制衣企業921家,其中超過半數企業的工資標準低于南非法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引發了南非紡織業協會的不滿,向勞工法庭提起集體訴訟。第三,沒有處理好與當地工會的關系。在發達國家,工會勢力極為強大,而我國企業沒有與工會談判的經歷與經驗,在投資及并購過程中,常常與當地工會處于對立面,最后造成投資失敗。如上海汽車收購韓國雙龍汽車失敗就是因為與當地工會關系緊張所致。
(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與國內差異較大
具體而言:第一,法律制度的差異。外國的法律的制度與國內差異較大,即便是方面相同的法律制度,在調整目標、調整方向以及法律條文上也存在較大的不同。法律制度的差異極易導致后續經營過程中發生糾紛。除此之外,發展中國家的法治不健全,司法腐敗等問題是引發投資糾紛的重要因素。第二,政治環境的差異。東道國政治環境較差也是引發糾紛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是政局不穩。如東道國頻繁發生戰爭、動亂、政變或恐怖主義事件,均會造成對合同條款中“不可抗力”解釋上的差異,進而會引發投資糾紛。二是東道國國內政策多變。東道國政府依照政策而不是法律所采取的征收、國有化等措施,容易引發中國企業與東道國政府之間的糾紛。三是政治保護主義。盡管在全球化背景下,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是大趨勢,但各種政治保護主義依然存在,歐美發達國家近些年盛行的“國家安全審查”就是典型的政治保護主義行為,成為拒絕中資企業投資的最大借口,由此引發了系列投資糾紛。第三,社會文化的差異。文化差異帶來的企業文化及經營理念差異是引發投資糾紛特別是勞資糾紛的根本原因。如首鋼秘魯公司的罷工事件持續多年難以解決,根源就是當地員工無法認同首鋼集團的企業管理模式。在糾紛處理過程中,首鋼集團多次開除當地的工會領導人,這種做法在國內是被允許的合法手段,結果在秘魯造成了無窮隱患,導致勞資糾紛持續了10余年。
三、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糾紛的應對策略
(一)中國企業層面
1.做好投資風險防控,提升法律風險控制能力。具體而言:第一,企業在投資前要做好盡職調查,充分了解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做好風險預判。我國企業到海外投資之前,一定要細致研究東道國民商事法律規范以及國際通行的投資規則,有并購計劃的企業還應該熟悉東道國的勞工法律制度,了解工會談判規則。此外,我國企業還應該做好東道國政治環境、經濟制度等方面的調查。近些年來我國有多家企業在美國投資能源項目,均被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予以否決,這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風險所引發的。第二,改革現有法律風險管理模式,提升合規管理水平。一是合同風險管理。中國企業應該圍繞自身的海外投資業務專長,制定合同信息管理系統,完善對外投資合同文本及合同管理流程。在投資項目立項以及合同訂立階段要強化合作方或被并購方的資信調查,在合同履行階段要強化各個崗位人員職責。當東道國的政治或其他風險導致合同無法履行時,投資方應該及時商談情勢變更事項,避免發生違約糾紛。二是知識產權風險管理。首先,企業要加大技術創新的投入力度,制定科學的研發及創新戰略;其次,針對知識產權分類管理策略,積極參與知識產權交易及轉化活動;最后,重視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尊重其他企業原創知識產權,明確自身的知識產權國際布局。三是勞資風險管理。我國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應該根據東道國勞動法律要求明確規范海外員工雇傭標準、薪酬標準,并做好勞資糾紛解決預案。另外,中國企業在并購后要重視企業本土化發展,盡量避免文化差異引發的勞資糾紛。
2.恰當選擇糾紛解決機制,靈活有效解決海外投資糾紛。具體而言:第一,對于與外國法人、自然人之間發生的商業糾紛,我國企業要及時了解東道國的法律規則及司法制度,包括司法及仲裁體制、管轄權、執行模式等。如果在投資合同簽訂的時候,雙方選擇了糾紛解決機制,就按照合同中的糾紛解決條款辦理。如果沒有選擇,民事糾紛通常按照屬地規則處理。第二,對于在投資合同中約定了仲裁事項,如果合同中約定了仲裁機構,則按照合同條款辦理;如果沒有約定仲裁機構,按照“被告人管轄原則”,可以選擇在我國企業登記所在地的仲裁機構解決;如果一般的商業糾紛對象是外國政府或政府授權機構,可以按照《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來提交國際仲裁機構解決;如果是政治風險引發的糾紛,除了通過我國商務部或駐外使領館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之外,還可以按照雙邊貿易投資協定確立的爭端解決機制來解決;如果有的東道國法律要求必須窮盡本國司法救濟后才能適用國際仲裁,如此先要盡量用東道國國內法解決,解決不成再尋求國際仲裁。第三,如果與貿易相關的海外投資糾紛,當對方是外國政府或政府授權機構,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外交途徑提請WTO解決。
(二)中國政府層面
1.完善國內相關法律規范。具體而言:第一,盡快出臺《海外投資法》。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我國企業對外投資規模還會繼續擴大,雖然當前我國政府制定了大量的海外投資法規及部門規章,但多數法規及規章是重管制,對企業在海外投資中的利益保護著墨不多。因此我國應該及時出臺《海外投資法》,按照“管理與服務并重”的立法原則,在規范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行為的同時還要明確政府在企業海外投資利益受損時保護義務。第二,盡快出臺《海外投資保險法》。一方面,我國現有的海外投資保險僅限于出口信用保險,出口信用保險作為政策性保險,并不是《保險法》的主要調整對象,由此導致出口信用保險法律依據不明,保險費率波動較大,增加了企業投資成本,降低企業投保積極性。另一方面,在當前企業大規模“走出去”的前提下,僅依靠出口信用保險難以完全化解海外投資糾紛,可以仿照日本的經驗,制定《海外投資保險法》,構建以政府公共財政為支撐的海外投資保障機制,降低我國企業解決投資糾紛的成本,保護企業海外投資利益。第三,修訂《仲裁法》。仲裁作為糾紛解決的機制之一,其快捷方便且成本低,容易被糾紛各方所重視。由此,我國仲裁機構要強化公信力,提升對企業糾紛解決的吸引力,不斷提升仲裁員的法律專業素養,完善仲裁機構治理規則,確保仲裁機構的獨立性,切割仲裁機構與政府部門之間的人財物紐帶。通過國內仲裁機構的改革,倡導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遇到糾紛時,選擇國內仲裁機構解決。
2.加大海外投資糾紛解決的國際合作力度。具體而言:第一,加大國際投資協定的商簽力度。國際投資協定包括區域、多邊、雙邊等多種類型,商簽國際投資協定可以有效降低糾紛發生率,另外當海外投資糾紛發生后,國際投資協定可以作為條約法來為我國企業提供相應的法律保護。我國應該盡快與全球主要經濟體以及我國企業投資較多的東道國簽署雙邊或多邊投資協定。我國雖與歐盟絕大多數國家簽署了雙邊投資協定,但根據《里斯本條約》的要求,從2021年期,歐盟成員國與第三國簽署的投資協定將被歐盟對外簽訂的統一投資協定所取代,構建歐盟范圍內統一的對外投資規則,因此要加大與歐盟投資協定的談判力度。另外,我國還應該加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商簽投資協定力度,減少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糾紛。第二,加大與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的合作力度。隨著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海外投資糾紛的增多,特別是非商業性的投資糾紛日漸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我國應該加大與MIGA的合作。MIGA主要承保禁兌險、恐怖主義、征收、國有化等非商業性風險,MIGA的承保險種是化解海外投資糾紛的重要工具。中國作為MIGA第六大股東,應該運用好這一優勢,擴大該機構對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承保力度與規模,擴大承保范圍,特別是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的承保力度,對我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遇到的非商業性糾紛解決有較好的保障作用。
參考文獻:
[1] 段小梅,李曉春.中國對外投資:發展歷程、制約因素與升級策略[J].西部論壇,2020(2):109-124.
[2] 楊挺,陳兆源,韓向童.201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特征、趨勢與展望[J].國際經濟合作,2020(1):13-29.
[3] 王佳宜.“一帶一路”倡議下投資母國的監管義務與法律對策[J].中國流通經濟,2020(2):110-120.
[4] 王軍杰.論“一帶一路”沿線投資政治風險的法律應對[J].現代法學,2018(3):170-179.
[5] 張曉濤,王淳,劉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政治風險研究——基于大型問題項目的證據[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20(1):118-128.
[6] 唐衛紅.開放經濟下企業知識產權風險防范及對策研究——基于“一帶一路”倡議[J].產業創新研究,2020(2):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