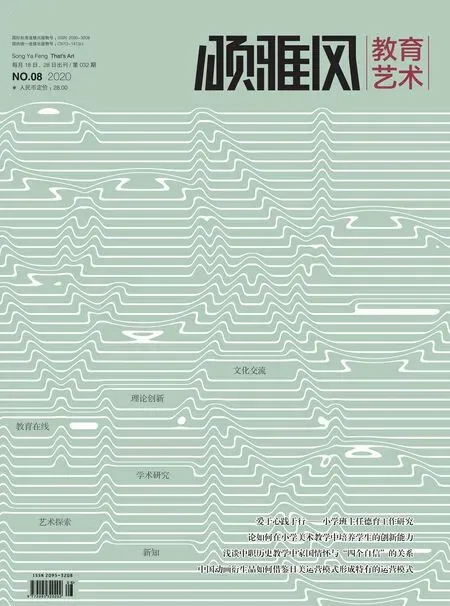試談肖像雕塑的創作心得
◎賈朋
當代藝術語境中,藝術家更注重個人情感和生活態度的表達,在藝術形式上極為多元化,視覺觀感也是令人眼花繚亂,這既是藝術自身發展規律使然,也是當下社會物質文化演變的自然結果。不過,寫實意義上的肖像雕塑仍然有其存在空間,普通大眾需要這種立體再現的藝術形式來紀念和為自己存形,傳統的手工藝也需要傳承,更重要的是,當下藝術是多元文化的組合體,具象寫實藝術仍是大眾消費的主體。
一般意義上的肖像雕塑創作,多以具體的人物形象為前提,此中再現的目的尤為重要,這對創作者的寫實能力是一個很好的考驗,筆者也是以此為創作的第一要務來督促和提升自己。已故的程允賢先生創作了大量人物肖像雕塑,他曾說:雕塑創作既是表現人的,它首先是研究人,因此,肖像雕塑更須通過人物的外貌揭示他的心靈,“形神兼備”是一種藝術評價的標準,而雕塑家在塑造中應當“以形寫神”。程先生的這段話對我的肖像創作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印度Sri Nitai Charan Konch肖像(圖1),這是一位年長的地方協會會長,臉上寫滿了滄桑與智慧。這件胸像花了較長時間才完成,難點在于深棕色皮膚掩蓋了很多面部細節的呈現,這需要時間去觀察、揣摩和不斷調整。

圖1 印度Sri Nitai Charan Konch肖像,泥稿,2016年
不同于繪畫,雕塑占有立體的三度空間,可以表現出與原物完全對等的形體結構,這對于追求物象真實再現、承載特定的表功或紀念重要人物而言意義非凡,并且,神話和宗教中的偶像崇拜也需要這一技術手段。提到寫實,需要注意的是其與具象的區別。寫實,是用藝術手法將客觀物象真實再現出來,藝術呈現與被表現物之間的各個特征盡可能地接近,這有點類似于拷貝的意思。就此而言,古羅馬的肖像雕塑可視為寫實雕塑的典范。文藝復興時期米開朗琪羅的作品,可視作寫實雕塑的一種情緒化再現。米開朗基羅精研人體解剖,對人物的具象寫實有著強有力的把控能力,他的作品以力量和氣勢見長,具有一種雄渾壯偉的英雄主義氣質。另外,17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大師貝尼尼,他塑造的人物大多處于激烈的運動中,人物的表情生動貼切,衣服隨風鼓動,營造一種輕快、活潑和不安的涂繪感覺。實際上,米開朗基羅和貝尼尼的人物雕塑,并沒有脫離古典藝術的范疇,希臘化藝術的精髓也在此中得以有效傳承。具象與寫實的概念比較接近,但含義要更寬泛一些,其造型特征在寫實基礎上有更豐富的變化,甚至允許一些夸張變形手法參與其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梵高的繪畫是具象的,但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寫實。
創作于2017年的奧地利尤根肖像(圖2),是筆者感悟很深的一件作品。這尊胸像從最初的拍大形到最后的完成,前后花了很長時間。原型是一位體格壯實的中年大叔,耿直又帶有一些憨厚的笑容,令人印象深刻,不過,那飽滿的形體結構與面部微妙的肌肉穿插關系,使我一度陷入到局部的刻意摹畫而使得面部表情很僵硬,后來有朋友建議我多看看古希臘、古羅馬的那些經典的頭像作品,認真品味,或有很好的借鑒作用。筆者于是收集了不少高清晰的經典雕塑片子,打印出來貼置于案頭,時時揣摩。古人云畫竹要做到胸有成竹,才能畫出好作品。這句話其實也適用于筆者的學習狀態,認識到只有真正理解了模特面部的結構關系和外在特征,才能更主動地塑造出形神兼備的好作品。經過這種尋根溯源式的學習后,筆者有了新的感悟,然后對泥稿進行大體量和整體結構的調整,步步深入,最終達到了預期效果。
相對而言,古羅馬的肖像雕塑更令筆者心馳神往。古羅馬在征服古希臘本土的同時,反過來又被后者的藝術所折服,這些勝利者們大量掠奪古希臘的藝術品,并復制那些經典雕塑來裝飾自己的庭院,他們在沿襲古希臘雕塑“真實之美”的同時,還大力發展了肖像雕塑的客觀寫實傳統,形成濃郁的世俗風氣。與古希臘那些理想化的審美趣味相比,古羅馬的肖像藝術追求再現被表現者真實的樣貌特征,并賦予了他們一種人格的尊嚴,這種藝術風格,給予了我很大的啟發。
作為一種商品形式,藝術家接受客戶訂單為其創作肖像,這是古已有之的傳統。古希臘、古羅馬傳承下來的寫實肖像雕塑,在文藝復興之后獲得廣大的市場,社會上層人士和富有階層,紛紛邀請藝術家為他們創作肖像,或者在陵園為死者雕塑遺容,這種情形可以說是古今并無二致。我從事肖像雕塑,深受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的藝術傳統影響,具體來說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我熱愛這種心智結合的勞作方式,在泥巴的揉捏和堆塑中再現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能從中獲得一種創作的快感;二是這項工作是當前我所從事的事業,從中能獲取我的一些生活資源。很高興能有這樣的時間和機會,來做自己喜歡的工作。

圖2 奧地利尤根肖像,高80cm,2017年
肖像雕塑中的寫實因素,與亞里士多德的“模仿”存在密切關聯,但實際上,每個歷史時期或社會形態,對于寫實的理解也是存在差異的,比如古埃及的藝術形態和古希臘的就有明顯差別,兩者都認為自己表現的是真實的物象。如果我們認同這樣的觀點,那么我們同樣可以把“具象藝術”理解為這種文化習俗和文化傳統下的重要的呈現形式,它不是簡單的對現實進行抄錄,而是對現實的一種解釋和再現。對于寫實角度不同所導致藝術形態的差異,使得我們的肖像雕塑創作,很難按照一種古代既有的定式來套用,而是要根據當下的具體要求和審美趣向 來創作。就筆者而言,將學院意義上的寫實肖像傳統,與中國自古以來推崇、諸多先賢認同的“形神兼備”美學思想結合起來,或許是值得筆者為之不斷奮斗的目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