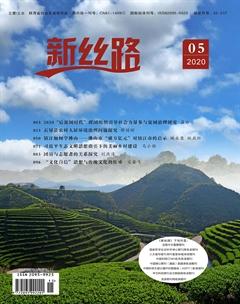論北魏漢化進程中的特點
張鵬
鮮卑民族主要活躍于十六國和北朝時期的政治舞臺,這一時期,是中華文明大轉型時期,民族大遷徙、大融合和社會大轉軌是魏晉南北朝歷史的主旋律。在當時社會現實的驅動下,包括拓跋鮮卑在內的北方各民族相繼步入了漢民族的封建化道路。
鮮卑的漢化在部落聯盟時期便已開始,檀石槐建立的鮮卑部落軍事大聯盟,之所以能兵強馬盛,讓各部臣服,不可忽略的原因是當時有很多漢族士人逃往鮮卑,充當檀石槐的“謀主”,為之出謀劃策,同時漢朝邊塞管理不嚴,許多銅、鐵兵器等物質被偷運出去,這些無不提升了檀石槐軍事大聯盟的文化軟實力和軍事硬實力。在北魏王朝的前身“代”政權時,拓跋鮮卑的漢化更是大大加深。什翼犍深受漢地文化的影響,學習了很多中原的典章制度,回到“代”以后,仿照同時期的晉朝,設置百官分管政務,又制定法律,規定各種罪行。
太祖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權后更是加快了漢化歷程,他召集儒生,對當時不同版本的儒家經典進行編輯和整理,“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余字,號曰《眾文經》。”此后,重視儒學始終是北魏王朝的基本國策。經過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燾三任國君的努力倡導,儒學得以在北方地區復興和傳承。至拓跋燾時期,北魏王朝復興儒學的政策初見成效。拓跋鮮卑全面漢化表現在孝文帝時期的改革,孝文帝的改革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上的整頓吏治、變革稅制、改革官制、遷都洛陽,還包括經濟上的行均田制、創三長制、改革租制,最直觀和典型的還是是文化層面上的改革,具體表現為說漢話、穿漢服、改漢姓、與漢族通婚等方面。
遷都平城后的北魏王朝,雖然統治者仍是拓跋氏,然而政權性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轉變。與盛樂時代拓跋氏政權相比較,新建立的北魏王朝政治面貌煥然一新,不僅在都城建制、政治制度等方面具有鮮明的中原王朝政治文化特征[1],還大力推崇儒學、爭奪中華正統則為北魏王朝塑造了中原王朝模式的政治靈魂和文化精神。平城和洛陽時代的北魏,真正實現了由塞外草原游牧政權到中原王朝、從邊疆屬國政權到皇權國家的華麗轉身。這時期的北魏,還有三個典型性的特點:草原絲路重鎮、后宮干政現象和佛教發展。以這三個特點為線索,能側面梳理出北魏平城和洛陽時代的漢化和發展脈絡。
一、草原絲路
北魏時期的平城是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溝通樞紐,這一時期的北魏平城與周邊國家有著密切聯系,也形成一條以首都平城為重要節點的草原絲綢之路,西域諸國使節從新疆經河套、包頭、呼和浩特至大同和北魏往來,西域的商人和商品也隨之進入平城。《魏書》記載了當時中亞、西亞、西域46個國家共109次的朝貢記錄,除了來自各國的外交使節外,還有包括官僚、姻親、商人、僧侶以及工匠、伎樂各色人等的西域胡人在平城定居。今天大同南郊建筑遺址挖掘出來自薩珊的銀洗、銀碗、波斯風格的銀盤、銀杯等,云岡石窟也有大量西方建筑元素,這些都是草原絲路在平城留下的鮮明印記。
平城還是南方農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匯地,古代平城往北三十余公里是游牧文化最為繁榮的地區之一,往南過了雁門就是傳統農耕文化發祥地之一。長期處在南方農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接壤地帶,不同的利益紛爭常引發各種類型、各種規模的戰爭與沖突,不同的文化,也在碰撞中孕育了大同多民族和多元化的邊塞文明。這種邊塞文明,不僅表現在拓跋鮮卑對漢文化的學習和吸收,還表現為一大批游牧民族的器物或文化對農耕文明的影響,如“胡床”改變了中原民族席地而坐的習慣,胡琴、琵琶、歌舞雜技豐富了中原的戲曲文化。總之,正是這種中外、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才能使平城從一個邊陲重鎮,迅速演變為新興王朝的京師,迅速聚集百萬人口,形成中國北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與交通樞紐。
二、后宮干政
后宮干政[2]是我國歷史發展中的普遍現象,縱觀中國歷史,從戰國秦昭王時期羋太厚開始攝政事,到清末慈溪太后的垂簾聽政,后宮干政現象一直延續不斷、屢見不鮮。鮮卑拓跋部作為一支來自北方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有著濃厚的部落色彩,平城時代的拓跋鮮卑,剛脫離氏族社會不久,受氏族制遺風影響,婦女在生活占有較高的社會地位,這也使得女性在北魏王室中擁有很高的地位,后宮干政現象更為嚴重。
太武帝拓跋燾繼位后,其養母竇氏被封為太后,竇太后不僅能總理皇宮內務,而且在國家危難之中能挺身而出,抵抗柔然的入侵,保衛平城。拓跋燾晚年被身邊宦官宗愛謀殺,宗愛擁立南安王拓跋余繼位,后又將之謀殺,期間宦官宗愛一直把持朝政。直至大臣發動兵變,擁立十三歲的拓跋濬繼位,即文成帝。拓跋濬養母常氏被尊稱為太后,從此,常氏便將年幼文成帝控制在手,干預北魏政治十余年。當然更為人所知的是后期馮太后的攝政,獻文帝拓跋弘即位,時值政局動蕩,馮太后臨朝聽政。獻文帝暴崩后,馮太后又擁立孫子拓跋宏即位,成為太皇太后,二度臨朝稱制,扶持孝文帝十四年,成為北魏中期全面改革的實際主持者。這種后妃干政現象從平城時期一直延續到遷都洛陽后,北魏末代皇帝孝明帝即位后,尊其母后胡氏為皇太后,胡氏臨朝聽政,權勢遍布天下,淫亂縱情,為天下人厭惡,文武官員人心渙散,各地叛逆作亂,北魏政權也土崩瓦解。
三、佛教發展
在拓跋鮮卑活躍于塞北草原時,對佛教知之甚少,佛教也未能在拓跋鮮卑部落里產生重要的影響。然而,在北魏入主中原后,為了更好地適應在中原地區統治的新形勢,從拓跋珪開始,大多數帝王都極力地將佛教拉入自己的統治體系中,大力地支持佛教發展。
道武帝拓跋珪曾“作五級佛圖”、“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等,還派人贈給僧人送錢財、衣物等。第二代皇帝拓跋嗣“亦好黃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雖然佛教在第三代統治者太武帝時期執政期間,因參與到當時的政治紛爭中而遭受到最嚴酷的法難,北方佛教險些被根絕。但文成帝即位后,便頒布了復興佛法的詔書,佛教重新煥發生機。第六代統治者拓跋浚更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他在執政六年后為了研習佛理禪位于太子宏,專心閱覽誦習佛經。第七代孝文皇帝在平城時期就大力推動佛教發展,興建了鹿野寺、建明寺、報德寺等佛寺。繼任者宣武帝則以大同云岡石窟為依據,在洛陽南邊的伊闕山開鑿石窟,即后來的龍門石窟。第九任統治者孝明帝在位期間,佛教發展更是急劇膨脹,當時傾其國力修建的永寧寺,既是北魏崇佛達到狂熱的標志,也是北魏裂亡的開始。遷都洛陽后的孝文帝及其后期繼任者更是把佛教發展到極致,寺廟和僧尼數大增,史料記載,至北魏末年,“略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隨著永寧寺塔的轟然倒塌,北魏最終走向分裂。
佛教之所以在北魏,尤其是遷都洛陽后有如此發展,有多種因素導致。首先是文化層面,北魏統治者想獲得中原士族的支持,擴大統治基礎,而佛教是吸引漢族士大夫的重要方式,所以受到北魏統治者的重視。其次佛教宣傳的眾生平等觀念對于民族融合具有獨特的作用,眾生平等觀念是有利于人與人的和平相處的,更是成為聯系、溝通各民族的精神紐帶,這也是北魏統治者熱衷發展佛教的重要原因。當然,政治的考量也是必不可少的,佛教的因果輪回的觀點可以讓被統治者安于被統治、被奴役的現狀,百姓相信“來生”,佛教還宣傳要求人們消滅欲望,忍耐順從,刻苦修行,注重精神世界的修行而忽略現實的矛盾,這對北魏統治者無疑是有好處的,理所當然得被大肆宣揚。
拓跋鮮漢化是一個長期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草原絲路重鎮的形成、后宮干政和佛教的發展無不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他們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僅使北方社會經濟有了明顯發展,農業生產工具得到改進,開墾荒地,手工業生產日益活躍,商業活動也日趨活躍,更在政治上大大加速了北魏政權的封建化進程,對北魏社會政治生活乃至整個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促進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為后來隋唐時期結束長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
注釋:
[1]在大同都城建設方面,道武帝時期,著力營建權力的中心西宮,太武帝時期,隨著太子監國制度的確立,增建了新的政治中心東宮,孝文帝時期,在宮城的中部建造起以太極殿為中心的宮城和舉行朝會、祭祀、慶賞等大典的“名堂”等建筑。
[2]此處的后宮不僅泛指皇太后、皇后及諸嬪妃等后宮女子,還包括為皇帝和后妃服務的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