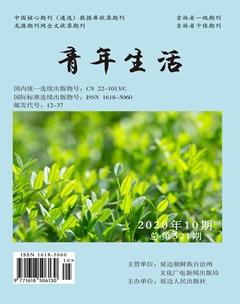文學的“祛魅”與“復魅”
駱江瑜
摘要:科技的發展帶來了大眾的、消費的時代,嚴重擠壓著精英的、嚴肅的文學的生存空間。文學仿佛成為社會的棄兒,又“潛在”成為社會的寵兒。從都市文學到科幻文學,從報刊到網絡,從“純文學”到“泛文學”,科技豐富了文學的種類,改變了文學的傳播方式,擴大了文學的場域,使得文學走向多元、大眾、泛化。科技給文學帶來挑戰,“祛魅”的同時,也為其注入了生命力。
關鍵詞:科技;都市文學;傳播媒介;泛文學;人工智能
“五四”運動爆發一百周年后的今天,科技的發展帶來了數字媒介的興起,網絡文學、“讀圖”時代猛烈沖擊著“純文學”。文學趣味在當今發生了重大的分野,“文學終結論”的言論一時間甚囂塵上。另一方面,我們極大得享受著科技帶給人類的便利,強大的數字化和檢索功能等使得我們擺脫了古人皓首窮經式的研究方式。同時,文學逐漸走向多元、大眾、泛化,有了新的面貌。前所未有不意味著今不如昔,反之,這是文學與科技的雙重再發現。
一、文學種類的豐富:從都市文學到科幻文學
兩次工業革命催生了現代高度發達的工業,也催生了“都市”這一特殊的城市概念。“都市文學”也由此產生。我們通常將具有現代都市意識的文學稱作“都市文學”。就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從朱瘦菊的《歇浦潮》到郁達夫的《沉淪》再到張愛玲的小說,無不具有現代都市文學的特征。都市是“都市文學”成長的搖籃,“都市文學”是對“都市”的再現。
在戴望舒的《雨巷》中“她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飄過/像夢一般地”[1]這樣富有深刻的內蘊性的場景,只有在都市中才能產生。城市人口的劇增,“移民化”的浪潮使得穿行在整個都市中的人,攜帶者多種語言和文化的信息,這種陌生而又豐富的人際交往特征,產生了不少都市中的傳奇故事。“我”和“丁香姑娘”就像是數學上兩條相交的直線,從無限遠的地方而來,有過一個短暫的相交,而走向無限遠的地方,擦肩而過,稍縱即逝。這種內蘊是鄉土文學所不可能具備的。沒有科技帶來的高度工業化的都市形態,也就不會有富有現代性的都市小說。
進入新世紀后,科幻文學漸露頭角。經以科學,緯以人情”[2]的科幻文學對未來世界的描述、想象,不僅僅突破了化學、地理、天文等自然科學層面上的理論束縛,同時也觸及到哲學、倫理等社會科學層面的擔憂與思考。
科技帶來的變革不僅僅是器物層面的,同時也是精神層面的。它在顛覆人類生存方式的同時,也孕育了新的文學種類。
二、文學媒介的改變:從報刊到網絡
19 世紀初期前后,媒介飛速發展,大眾傳播媒介開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著機械印刷技術的普及,我們開始了報刊、書籍的批量化生產和快速傳播。印刷媒介促成了報刊、書籍的批量生產,逐步推動了白話文運動,促進了文學的平民化,也催生了現代小說。電子媒介的出現,為網絡文學的成長提供了空間。新世紀以來,網絡文學發展之快,受眾之廣,影響之大前所未有。科技的發展,改變了文學的傳播媒介,也擴大了文學的影響力。
清末報刊雜志的普及,產生了報載小說、速寫等新的文學樣式。中國現代第一篇白話小說最初是因為《新青年》雜志的錢玄同幾番約稿才寫成的,“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3]現代報刊促成了魯迅的文本創作沖動、小說文體選擇、白話語言方式,還推動了作者——作品——讀者的傳播環節生成。
在現代影視媒介影響下,文學作品不斷被影視改編,概括性的閱讀文本轉變為感性的觀看文本。電影《紅高粱》、《霸王別姬》就是文學作品與影視傳媒互相成就的例證。影視改編使文學更有廣闊性,豐富了文學的形式,也增益了文學創作。21世紀后,互聯網和移動終端的普及,讓大眾的文學接受更為方便。“掌上閱讀”等APP將紙質圖書數字化,載入網絡。不少研究機構也陸續入駐在微博、微信等新型媒介,發布相關作品與研究成果。
除了傳播方式的改變,網絡媒介也孕育了網絡文學。網絡小說的題材與類型繁多。盜墓、玄幻、仙俠等類型的網絡小說憑借著獵奇的情節與新鮮的網絡語言收割了一大批海內外讀者群。除了通俗的、大眾的文學外,網絡同樣為嚴肅的、精英的文學提供了平臺。吳亮先生2018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朝霞》,最初也是在網絡上連載。帖子日更,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也給了吳亮一些《朝霞》啟發。
文學文本的生成離不開傳播媒介。考察媒介在現當代文學生成中身份的形成機制及其衍變邏輯,我們不難發現,正是文學媒介的更新,讓文學有了不同的生成、傳播、互動等更多的可能性。
三、人工智能與文學:AI寫詩
“人工智能”的構想最早誕生于1956年美國的達特茅斯會議[4],其本意是研發“會思考的機器”,以便用它來模仿人類學習,替代或拓展人的某些智能。云計算,無人駕駛,智能機器人,大數據都是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革命。人工智能也向藝術領域滲透,谷歌開發的“阿爾法狗” (Alpha Go)大勝人類引發了大眾新一輪的思考,“人類會不會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微軟小冰”的詩歌寫作,更是使得AI打開了“繆斯之門”。
2018年,微軟小冰升級至2.0版。用戶只要上傳一張圖片,填寫提示文字,小冰就能創作出一首詩歌。小冰的入口界面就是一首AI創作的小詩,于2017年12月16日發表在《華西都市報 浣花溪》:人們在廣場上游戲/太陽不嫌疲倦/我再三踟躕/想象卻皺起了眉。小冰學習了1950年以來519位詩人的現代詩,通過復雜的運算方式和技術的迭代更新,寫出了具有獨特的風格、偏好和行文技巧的詩歌。湛盧文化甚至還為小冰出版了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在微軟小冰之后,能創作舊體詩”“小詩機”也面世了。詞組的隨意拼接與無機組合帶來了陌生化的效果,正好符合了文學的特性,使得AI創作的詩歌頗現驚人之語。但語句的邏輯、語法等存在著明顯的漏洞,詞句的韻律與節奏感也是缺位的。人工智能的本質是“計算”,它的“非人”使其不可能創作出真正的詩歌。但AI寫詩仍是我們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
科技的急速發展使得我們今天的文學前所未有的復雜,同時,也是史無前例的精彩。文學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展,走向多元、大眾、泛化。文學始終伴隨著人類,以新的形態生存,我們不妨對新的文學文本持開放、包容、樂觀的態度,與之展開新的對話。
參考文獻:
[1]戴望舒:《雨巷》,《戴望舒作品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4:177.
[2] 魯迅:《月界旅行·辨言》,《魯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63.
[3] 魯迅 《<吶喊>自序 》,《魯迅全集》 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41.
[4] 達特茅斯會議,是指1956年8月在美國漢諾斯小鎮達特茅斯學院召開的討論如何用機器來模仿人類學習和智能的會議,這年被視為人工智能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