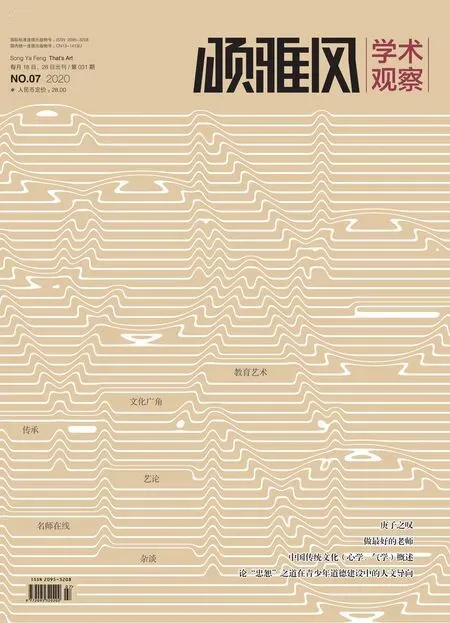參與性藝術(shù)中的觀眾與社群
◎任一飛
從早期美術(shù)館中的觀眾到各種特定的社群,作為參與主體的社群也在不斷變化:由觀眾到公眾、社會邊緣人、社區(qū)、參與者。這些名稱的變化顯示著藝術(shù)實踐不同的政治語境和美學傾向,同時也對應著各種政治進程中現(xiàn)代性發(fā)展的不同路徑和在微觀政治領(lǐng)域?qū)ι缛旱闹匦抡J識。
從早期皇室主導的沙龍,到印象派不斷描繪的巴黎市民生活,再到現(xiàn)代主義時期對各種媒介材料的使用,西方藝術(shù)史中的主體與客體的區(qū)分總是顯得涇渭分明。這種對主體與客體的區(qū)分,同時也反過來形塑了現(xiàn)代性的藝術(shù)主體觀念,藝術(shù)被視為連接觀者(客體)的中介,而作為觀者的客體似乎只有理解和接受的權(quán)利。然而當藝術(shù)實踐的媒介轉(zhuǎn)換成人本身時,當藝術(shù)生產(chǎn)轉(zhuǎn)變成藝術(shù)家與各種社群和團體的協(xié)同合作時,藝術(shù)實踐中的主客關(guān)系就開始變得模糊起來。這種集體性的合作生產(chǎn)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所催生出對“個人”和“自我”私有化的抵抗。那么在社群參與的藝術(shù)實踐歷程中,參與者之間的關(guān)系轉(zhuǎn)變,參與主體間實踐經(jīng)驗的變換過程就成為基于社群的藝術(shù)實踐的關(guān)鍵要素。
從社會學中的一個研究概念,到被視為一種社會資本和抗爭資源,再到藝術(shù)實踐中參與的社群。社群的變化和延展一直處于一種流動的狀態(tài),從其自身結(jié)構(gòu)和與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關(guān)系層面來看待,這種流動性實則為一種人與人交往關(guān)系和參與形態(tài)的不斷轉(zhuǎn)變,其中不斷牽引出主體與權(quán)力,與空間政治之間的斗爭與嬗變。本文所探討的藝術(shù)參與中的社群也并非簡單個體的集結(jié),筆者更傾向性地認為它不是一個即刻就可以被定義,被歸類的概念。而是在不斷地實踐,不斷地斗爭中所散發(fā)出的各種可能意味。這種流動性或許也恰恰就是基于社群的藝術(shù)實踐產(chǎn)生改變的可能。
20世紀六七十年代藝術(shù)去物質(zhì)化和介入各種社群的實踐也符合上述的趨勢。藝術(shù)擺脫了獨特之物的地位,作為一種實踐方式參與到各種社會行動中來。其社會和政治的維度被逐漸打開,并被作用于現(xiàn)實生活之各種可能。這其中逐漸出現(xiàn)的兩條路徑或可區(qū)分為藝術(shù)體制的內(nèi)部批判和藝術(shù)的社會批判兩種形態(tài),前者通過藝術(shù)內(nèi)部對于外部的指涉而獲得話語,后者則更多是打破身份的界限直接參與進新的藝術(shù)與社會生產(chǎn)當中去。
事實上藝術(shù)界內(nèi)部對于藝術(shù)體制的各種批判實踐從未缺席過,每當曾經(jīng)屬于先鋒的藝術(shù)無改變的重復過往之實踐,新形態(tài)的藝術(shù)便不斷質(zhì)疑和挑戰(zhàn)原有的藝術(shù)機制,這種新形態(tài)的藝術(shù)往往也對應著新興起的政治、經(jīng)濟形態(tài)。從這張圖示我們可以看出,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藝術(shù)界的運行系統(tǒng)是一套由藝術(shù)家,藝術(shù)作品,策展人、批評家、觀眾所共同構(gòu)建的藝術(shù)運行機制。而此時歐美所出現(xiàn)對于白盒子美術(shù)館機制批判的各種空間實踐,事實上就是對原有藝術(shù)運行機制的挑戰(zhàn),是關(guān)于藝術(shù)話語權(quán)的爭斗。但正如同姜俊所說:“有趣的是這些發(fā)生在20世紀60—70年代的藝術(shù)實踐既沒有揚棄自我的藝術(shù)身份,創(chuàng)作者也沒有放棄藝術(shù)家的身份,他們雖然熱衷于跨界,打開藝術(shù)范圍的界限,展開各種公共實踐,但始終還是處于藝術(shù)討論之中,他們并沒有開辟一種作品閱讀的跨領(lǐng)域和新評價機制。藝術(shù)家們只是在一種曖昧中否定了藝術(shù)的美學主義自律性,但依舊還是在藝術(shù)體制的圈層內(nèi)指涉著體制之外的一切。”由此可以看出,這種對于藝術(shù)體制的內(nèi)部批判事實上其最終的結(jié)果還是被藝術(shù)體制所吸納,成為新的藝術(shù)主流形態(tài),而并未改變藝術(shù)生產(chǎn)中主體間作用關(guān)系的問題。那么有沒有一種行動的藝術(shù),可以打破藝術(shù)界中對于各種身份的界限,甚至是跳脫出藝術(shù)界所構(gòu)建的運行邏輯,而并非在原 有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打轉(zhuǎn),抑或是一些不痛不癢的批評文字。而是將這種行動直接代入社會發(fā)生的現(xiàn)場,和參與者進行共同生產(chǎn)呢?
當然上述的情境也只是藝術(shù)現(xiàn)代性發(fā)展中的一條線索,我們始終要有對單線歷史敘述的質(zhì)疑,并進而發(fā)掘出對于歷史之理解的多重線索。藝術(shù)是關(guān)于可感性的,那么關(guān)鍵就是對于這種感性形式的歸屬問題,也即誰是這種感性形式的生產(chǎn)主體,不同感性形式生產(chǎn)主體間的關(guān)系又是怎樣的?由此或可以成為進入藝術(shù)社會批判的路徑,這也正是先鋒藝術(shù)家所要行進的實踐。回溯上段所談到的,那么在關(guān)于各種藝術(shù)參與社群的實踐中,所探索的正是如何使得不同的社群重新獲得可感性經(jīng)驗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