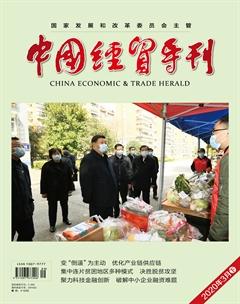五問氫能產業發展
符冠云
近兩年氫能在我國備受社會各界關注。由于具有來源廣泛、能量密度高、清潔低碳、靈活高效等特點,氫能有望成為我國能源革命戰略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熱情高漲之際,需要放下“非我莫屬”“時不我待”“終極能源”等不切實際的觀念,冷靜對產業發展的關鍵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研究,客觀審視氫能發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問題,科學評估經濟性和社會效益,合理選擇技術路線和應用場景,把握好推進的力度和時間安排,引導氫能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一、如何看待氫能與能源系統的關系
根據2019年11月印制的《能源統計報表制度》,國家統計局要求自2020年起,將氫氣和煤炭、天然氣、原油、電力、生物燃料等一起納入到能源統計體系之中,未來氫氣的生產和消費將被單獨統計出來。這一制度調整意味著氫氣在獲取“能源”身份的道路上,邁進了堅實的一步。由于氫能是二次甚至三次能源,需要經過煤炭、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能源的加工轉換才能制成,因此氫能的發展會對我國能源消費總量、結構、效率、碳排放等方面產生影響,由此也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如果將氫氣作為一個新的能源品種融入現有能源系統,那其與現有能源系統的關系是什么?
氫能的發展要服從和服務于我國能源轉型的總體戰略——安全、清潔、高效、低碳。為提升能源安全、減少環境污染和應對氣候變化,我國與世界主要國家同步,積極探索能源轉型的路徑和模式,并在減煤、穩油、增氣和高比例發展可再生能源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績,但也暴露出優質能源供應能力不足、穩定性差、能源轉型成本高、缺少智能管理能力和手段等一系列問題,甚至有專家提出能源轉型存在“經濟合理、穩定安全、綠色低碳”的“不可能三角”。在此背景下,氫能作為即將加入能源系統的一員,應更好地促進能源系統向安全、清潔、高效、低碳方向邁進,并利用其“來源多、去向廣”特點,破解能源轉型過程中遇到的難題。
應建立從生產到消費的全生命周期綜合評價體系,選擇合適的技術路線,提升氫能與能源轉型進程的融合度。能源轉型在不同階段有不同任務,主要矛盾和關注重點也會有所區別。氫能具有“從現有能源而來,再去替代現有能源”的特點。雖然在消費側,使用氫能替代現有能源基本可以做到高效率、零污染、零碳排放,但站在整個能源系統的角度,還要考慮氫能來自于哪種能源,需建立包括資源消耗、能源效率、污染物排放和二氧化碳排放等指標在內的全生命周期評價體系,并在當前能源轉型主要考量因素和價值排序基礎上,選擇合適的技術路線。近期應圍繞安全、經濟、清潔等因素,重點用好工業副產氫資源,并在可再生能源富裕地區探索電解水制氫商業模式,進而開展氫能替代傳統能源的進程。
二、如何找準氫能的定位和作用
2018年以來,氫能在我國掀起了一輪熱潮,然而這一輪熱潮主要由汽車行業、企業推動,再加上日本、韓國等“鄰居”的榜樣作用,使得社會各界對于氫能的關注過多集中于汽車領域,甚至把氫能產業等同于造車。截至目前,我國已有近40個地區發布了氫能發展規劃(或實施方案、行動計劃等),其中絕大多數都把汽車作為氫能產業唯一突破口,手段幾乎是清一色的發展燃料電池裝備制造業和汽車產業,應用場景過于單一。造車、買車、用車的模式引發了對于產能過剩、技術壁壘等方面的擔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既然氫能有望成為一種能源,那這種能源只能用于汽車嗎?如何找準氫能的定位和作用、回答好“我要到哪里去”,是加速發展氫能產業之前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
氫能將扮演高效清潔的二次能源、靈活智慧的能源載體、綠色低碳的工業原料這三重角色,在工業、交通、建筑、能源等領域發揮重要作用,并最終實現深度減碳目標。近幾年,知名國際組織和研究機構陸續發布了氫能發展愿景、路線圖等報告。例如國際能源署發布的《氫能的未來》中認為,氫能將有望在“難以減排領域”(主要包括工業原料、高品位熱源、重卡、船舶、應急保障電源等領域)得到大規模應用,完成這些領域的脫碳。國際可再生能源署認為,氫能在各終端部門的應用,還有助于可再生能源的高比例發展、推動能源轉型進程。這種“大氫能”的觀點也得到了歐盟委員會、英國氣候變化委員會、麥肯錫、國際氫能委員會等機構的印證。可見,氫燃料電池汽車只是氫能用于燃料電池領域的諸多場景中的一個。
“大氫能”發展理念更符合我國階段特點、比較優勢和發展趨勢。首先,我國有很多“難以減排領域”,例如鋼鐵行業用于還原鐵礦石的焦炭、石化和化工行業的氫氣原料等,每年造成近15億噸的二氧化碳排放,可以通過氫能冶金、“綠氫”替“灰氫”等方式解決;柴油重卡、船舶等,也是氫能替代傳統能源的應用重點。其次,未來隨著大數據中心、5G通訊基站建設,氫燃料電池應急保障電源也有較好的應用前景。第三,氫能還可以與可再生能源生產部門及電網對接,通過電解水制氫、氫能的儲運及跨能源品種轉換,能夠有效減少“棄電”現象、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納能力,進而為提升整個能源系統的靈活性和智能性作出重要貢獻。因此,在制定氫能發展規劃時,應充分發揮氫能作為二次能源、能源載體和工業原料這三重屬性,構建多元化應用場景。
三、如何把氫能從“概念熱”發展到“市場熱”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布新能源汽車年度產銷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燃料電池汽車產銷分別完成2833輛和2737輛,同比分別增長85.5%和79.2%。雖然增幅不可為不大,但與業內預期5000輛左右的目標還有較大差距。盡管產業界、學術界、各級政府層面都對氫能發展比較看好,大量規劃得到發布、大批企業進入,卻難掩氫能發展仍僅處于“概念熱”階段的事實,甚至有媒體稱這種現象為“葉公好龍”。相對而言,目前我國氫能產業的發展處于地方政府熱、中央政府冷;設備制造熱、下游應用冷;口頭呼吁熱、實際政策冷。如何走出“雷聲大、雨點小”的局面,實現由“概念熱”到“市場熱”的轉變,是氫能產業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
氫能發展需要在體制機制上做出重大調整和創新。雖然氫能寫入了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高層領導也在不同場合多次表態,極大提振了市場信心,但觀望情緒依然比較重。觀望的背后,是與氫能發展相關的頂層設計、管理體制、政策機制和激勵手段的缺失。首先,氫氣的能源屬性還沒有得到最終明確,如果僅作為危險化學品來管理,在生產、運輸、使用環節都會存在限制。需要承認,氫氣具有易燃易爆特點,危化屬性是確定無疑的,可參照天然氣兼具能源和危化品的模式進行管理。其次,需要明確氫能產業鏈各個環節的監管部門和對應的責任義務。例如氫氣壓力容器標準、液氫相關標準、加氫站的歸口管理部門和審批流程、油氫氣氫合建站監管模式等。第三,在重點地區可采用以政策紅利代替補貼紅包的方式,通過加強環境監管、能源和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等方式,以及碳排放交易、碳稅等價格機制,為氫能應用拓展市場空間。
四、如何“從娃娃抓起”規范產業發展
我國氫能產業已積累了巨大的發展勢能,在體制機制得到理順、政策措施得到明晰以后,極有可能迅速引發投資浪潮和產能擴張。根據已發布的氫能發展規劃,初步統計未來10年內氫能產業的經濟產值或將超過10萬億元,提到的“氫能產業園”“氫能小鎮”“氫谷”涉及總投資多達數千億元,氫燃料電池汽車規劃推廣數量超過10萬輛,加氫站建設規劃超過500座。因此有必要“從娃娃抓起”,充分吸取其他產業從無到有、從有到大、從大到強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在產業發展之初,通過統籌謀劃、科學布局、合理激勵,引導產業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首先,應控制好“市場換技術”的步伐,避免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惡性循環。我國汽車、家電、手機等產業發展之初,都采用了“市場換技術”策略,并逐步實施進口替代。過程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一旦開拓市場領先于技術研發,就很容易將產業引入“打苦工、賺快錢”陷阱,甚至會摧毀自主研發能力。因此,在氫能產業導入的最初階段,應注重技術研發和人才隊伍建設,而非急于打開下游應用市場。在產業布局階段,要重視技術創新平臺的搭建,將技術創新能力提升和平臺建設納入到產業布局的優先環節;在產業推進過程中,應成立專家指導委員會,為人才引進、技術引進和產業項目引進提供必要的專業咨詢服務,提升決策水平。
其次,應統籌氫能產業鏈各環節協調發展,避免“雞生蛋、蛋生雞”的死結。氫能產業“制儲運加用”環節聯系緊密、木桶效應非常明顯,任何環節的脫節都會造成其它環節配套設備的閑置。再加上氫能產業具有資本密集型特點,資產的閑置都會造成投資浪費和資源錯配。因此,氫氣生產、供應網絡、下游應用之間存在動態博弈,各環節行為主體很容易產生互相觀望的結果,有車無站、有站無氣、有氣無車的情況時有發生。所以,根據我國目前氫能資源開發潛力較大而應用市場剛剛起步的特點,政府在謀劃氫能產業發展過程中,應遵循“需求導向”原則,“自下而上”布局生產、儲運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在對本地氫能需求領域、數量和分布做出科學研判的基礎上,倒推基礎設施建設目標、謀劃氫氣供應網絡、尋找低成本氫源,協調氫能供應鏈各環節進展。
第三,應優化財政資金使用方式和支持領域,避免“賠了夫人又折兵”情況。在產業發展之初,適當的補貼是必要的,但要根據現實情況進行及時調整。當前我國氫能產業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不足、關鍵部件自主程度不高、產品性能指標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較大,短期內難以完全實現對進口產品的替代。基于當前技術掌握程度,如果強行通過補貼手段刺激下游需求,相當于把大量補貼資金輸送至國外公司,而這些受益的公司還有可能利用其技術、資金、品牌等方面優勢,進一步統治國內市場。因此,財政支持應向核心技術、部件的研發示范方面傾斜,待產業化條件成熟時,再轉為支持市場開拓;同時,對基礎設施建設、關鍵通用型技術研發、示范和產業化進行適當的補貼。在利用補貼撬動市場之前,做好經濟性評估和綜合效益分析,控制好補貼力度、規模和持續時間。
五、如何降低氫能在應用端的成本
從技術上看,氫能可以應用于交通、工業、建筑等多個領域,但目前高昂的成本使得氫能在應用端的推廣進程舉步維艱。以最受市場追捧的氫燃料電池汽車為例,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對比了10.5米長氫燃料電池公交車和鋰電池公交車全生命周期成本,結果顯示,氫燃料電池路線全生命周期成本超過550萬元,是鋰電池汽車成本的3倍。其中,車輛購置成本高出2倍、能源成本高出4.5倍、維護成本高出2.5倍。在工業領域,“綠氫”替“灰氫”也存在巨大的價格鴻溝,“灰氫”成本普遍在10—20元/kg,而“綠氫”成本在30元/kg甚至更高。產業發展之初有補貼來填補價格鴻溝,但天量補貼也將氫能發展局限在少數財政實力雄厚的地區。因此,如何降低氫能在應用端的成本,是氫能產業規模化、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氫能大規模終端應用須立足于價格競爭優勢,須應用新技術、新機制和新模式,降低氫能在應用端的成本、提升市場競爭力。第一,在制氫環節,著力破解清潔制氫技術“叫好不叫座”難題。可通過峰谷電價、電力需求側管理、參與電力系統輔助服務等方式,獲得低價電力或價格補償、為電解水制氫降成本,還可通過焦爐煤氣“提氫補氧”等技術手段,最大程度、最低成本開發工業副產氫。第二,在儲運環節,通過規模化和集約化來降低單位氫氣儲運成本。應盡快出臺更高壓力等級儲氫設備標準及液氫運輸相關標準規范,提高儲運效率和運輸經濟半徑。第三,在加注環節,開展跨部門、跨領域合作。推廣油氫、氣氫合建站建設和運行模式,降低加氫站建設成本,在電力富余、價格低廉且條件允許地區還可探索應用制氫加氫一體站模式。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改革委能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