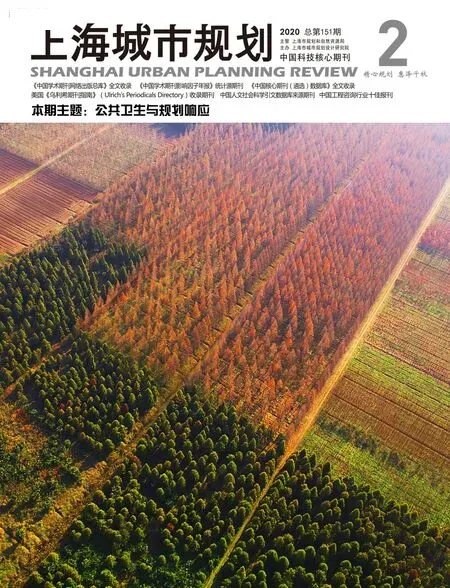高效響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關鍵規劃議題*
黃 怡 HUANG Yi
0 引言
2020年初,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肺炎”)在武漢暴發,現已成為全球大流行病。這場疫情將“如何高效響應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議題迫切地提到了規劃議程上。本文通過分析國內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實踐與研究動態以及我國城市醫療衛生相關規劃現狀,突出在我國行政體系慣性和社會文化特點下,城市醫療衛生設施規模布局和醫療衛生服務效能這兩方面與城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能力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的關聯,而此關聯性分析在現有防災應急類規劃、城市醫療衛生類規劃中相當欠缺。在著重探討該議題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高效響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整體規劃策略。
1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概念、實踐與研究動態
自20世紀以來的百余年中,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頻發,給全球帶來了巨大的生命、健康和經濟損失及嚴重的社會恐慌。圍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各國也形成了自成一體的實踐與研究。
1.1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概念與類型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1],突發公共衛生事件(Acute public health event)指的是任何暴發或是進展迅速、可能對人類健康造成負面影響、需要立即評估和應對的事件,包括尚未引起人類疾病,但可能因暴露于受污染的食物、水、產品、環境或染疫動物而導致人類患病的情形。
由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危害、暴露及背景不同,存在不同的類型劃分。按事件緣由,主要包括由自然、意外或人為釋放的生物、化學和放射性危害引起的公共衛生事件(CBRN),以及火災、洪水、極端天氣、火山暴發、地震及海嘯等自然災害引起的公共衛生事件。按事件發生時間,分為季節性與周期性暴發事件(如非洲每年的霍亂疫情,美洲和亞洲地區的登革熱季節性流行),以及不定期、偶發事件。按傳播方式,分為傳染性疾病和非傳染性疾病引發事件,由傳染性疾病引起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因影響范圍廣而更具危害性。因此,針對不同類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其控制與響應存在適宜性及可行性的問題。
1.2 國內外相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的實 踐與研究動態
就醫療衛生整體水平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而言,澳大利亞、德國、英國、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均處于前列。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于1995年開始聯合發布風險管理標準,是適用于廣泛風險類型的通用指南(The Joint Standards Australia/Standards New Zealand Committee OB-007)。美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預警與應急管理能力在全球首屈一指,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系統主要在公共衛生領域的危機準備和預警能力、流行病監測、科學研究和實驗、公眾健康警報網絡、公共衛生領域的危機溝通和信息傳遞、教育和培訓等6個方面不斷建設和完善。目前以縱向三級應對體系為基本特點,自上而下包括聯邦層面的CDC(Centers for Diseases Control and Prevention)疾病控制與預防系統、地區及州層面的HRSA(Health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dministration)醫療資源和服務應急準備系統,以及地方層面的MMRS(Metropolitan Medical Response System)城市醫療應急系統3個子系統。處于基層的城市醫療應急系統較強調第一現場應對人員之間的協作互動,而前端嚴格防控的態勢使得在美國形成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較少,例如2001年在遭遇炭疽病毒生化襲擊時,公共衛生部門迅速反應,有效避免了炭疽病毒的擴散[2]10。
相關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的國際研究可歸納為3類:第一類較多涉及生化危機,例如在生化核輻射響應中的現場倫理決策[3]、潛在毒性生化恐怖主義的公共健康應急[4]等;第二類側重于規劃,例如針對恐怖襲擊和自然災害的響應規劃[5]、針對重癥監護病房的災害規劃[6];第三類為指南類研究,大多在世界衛生組織指導下開展,例如傳染病應急控制現場手冊[7],特別是一些經常遭遇自然災害的國家,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方面都有所準備,例如亞洲斯里蘭卡編制了傳染病流行病學概況手冊,論述主要類型的突發公共衛生疾病及其防控策略[8]。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發生過多起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各地逐步建立了公共衛生應對體系,全國層面也形成了相關政策,如2003年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事件后國家發布實施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呈現出我國仍然面臨傳染病預警系統與傳染病防治等方面的嚴峻挑戰。
國內對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研究主要在2003年SARS發生之后,包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管理綜述[2]8,[9]、應急能力測評方法及現狀應用[10]、公立綜合性醫院應急救援水平分析[11]等方面。上述研究主要來自醫學、公共衛生、公共政策與管理領域。
關于城市醫療衛生設施專項規劃,有大量實踐項目和一些研究[12]。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關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規劃響應研究極少,局限于城市綜合減災規劃設計初步研究[13]、公共政策層面的城市防災減災規劃探討[14],個別研究涉及傳染病類型。而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特定性質,缺乏直接針對醫療衛生硬件狀況、醫療衛生服務效能與響應能力關系的規劃研究。這也是本文要著力探討的議題。
2 我國城市醫療衛生相關規劃現狀
作為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基本醫療衛生領域在《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年)》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 《“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等政策文件指導下發展,而城市醫療衛生建設按照我國城市醫療衛生相關規劃開展。
2.1 規劃的類型與特點
目前,我國主要有兩類醫療衛生規劃(見表1)。一類是全國和地方層面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大多由各層級衛生部門編制,部分省市還制定了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發展綱要或規劃。在部門系統規劃之外,湖北省武漢曾制定國家醫療衛生服務中心發展規劃,力爭繼北京、上海之后成為下一個全國性醫療衛生服務中心。另一類由原先的城鄉規劃部門編制,包括城市總體規劃階段的醫療衛生專項規劃或醫療衛生設施專項規劃,以及醫療衛生設施布局規劃等。還有一些規劃與健康產業相關,與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關聯不大,例如湖北省黃岡市由發改委組織編制的《黃岡市大健康產業發展規劃(2018—2025年)》。
上述兩類規劃的組織編制部門不同,內容側重也不同。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強調醫療衛生系統內部的資源配置、服務供給及其發展管理,涵蓋城市公共衛生體系的硬件與軟件建設;醫療衛生(設施)專項規劃、布局規劃等著眼于醫療衛生設施用地安排、空間配置匹配度等方面。
2.2 規劃的問題與不足
從我國醫療衛生相關規劃現狀來看,主要存在下述3方面問題與不足。

表1我國城市醫療衛生規劃類型
(1)部分城市僅有衛生部門編制的規劃(例如部門“十三五”規劃)。衛生部門設置了發展目標,但是缺少對應落實的空間專項規劃,因而可行性、可操作性不強,在城市土地緊張時,醫療設施用地得不到保障。
(2)城市總體規劃中編制了醫療衛生(設施)專項規劃,但是與區域衛生規劃、醫療衛生服務規劃等銜接不夠,對于“辦什么、辦在哪、辦多少、辦多大”等重要問題,各部門缺乏有效的溝通協作,專項規劃只管醫療衛生設施的數量、用地和空間布局,對于醫療服務供給機制、運行管理模式不管或不熟,往往導致實際操作中各項醫療衛生設施建設無法按照規劃指標分級落實。
(3)兩類醫療衛生規劃多采用常態思維方式,對于國家層面規劃(綱要)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處置能力和緊急醫學救援能力的要求缺乏深化,對公共衛生、公共健康與新型城鎮化以及區域發展布局的關系考慮不足,在城市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城鄉規劃、國防衛生動員需求等方面缺少銜接,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不確定性與破壞性考慮不足,使規劃的前瞻作用未能得到體現。
鑒于地方保護主義帶來的對危機事件信息的傳導與誤讀等情況,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和嚴重性都不容忽視,而前端衛生防控壓力必然后移至醫療應急系統。就醫療衛生規劃及其實施而言,主要包括醫療衛生設施規模布局和醫療衛生服務效能兩方面。
3 醫療衛生設施規模布局與城市高效響 應能力分析
城市對于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響應能力,取決于其硬件和軟件基礎。硬件主要涉及城市醫療衛生設施的土地使用安排、規劃建設,軟件主要涉及醫療衛生服務供給的制度設計、管理模式等。從歷史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可以探討城市醫療衛生設施應急需求,從城市醫療設施規模數量與空間布局出發可以制定響應預案。
3.1 歷史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的醫療衛生設施 應急需求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烈性傳染病以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而產生高效響應訴求。當傳染病類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形成時,往往存在下述問題:(1)初期確診數量可能遠小于實際感染者數量。(2)疫情進程中,存在確診病例、高度疑似病例和親密接觸者的診治缺口,醫院床位數不能滿足實際需求、隔離治療空間或隔離條件不夠(例如疑似病人居家隔離等待),造成人群交叉感染和持續的社區傳播。(3)疫情嚴重時期,短時期內形成對醫院床位、醫護人員、醫療物資的集中需求,遠超出常規狀態下的醫療服務供給指標,形成擠兌效應,甚至導致醫療系統崩潰。因此,足夠的床位及醫療物資儲備是控制疫情蔓延的重要保障。以下主要采用文獻研究法,以上海、北京、武漢3地的公共衛生事件為例,通過歷次傳染病暴發時的實際應對分析,檢視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和醫療衛生設施空間類專項規劃的響應能力。
1988年上海暴發甲肝疫情,短短3個月內感染近30萬人,當時全市所有內外科病房總計5.5萬張病床[15],而甲肝病人數以萬計,醫院病床嚴重不足,一些廠房、庫房,甚至小區的自行車棚都被改造成臨時隔離病房。
2003年SARS期間,北京于4月中旬設立6家定點醫院,但是早期定點醫院的醫療設備、環境條件和技術水平都難以應付突如其來的疫情。例如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因建筑格局和醫療流程設計不適合收治SARS病人,遭嚴重污染后被迫關門停診、整體隔離。5月又確定了16家定點醫院[16];后臨時建設啟用小湯山醫院,專門收治共680名患者[17]。北京雖然是重疫區,但是患者人數尚未超出其醫療系統的承受能力。
相較之下,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異常嚴重,截至2020年2月26日,累計確診47 824個病例[18]。在早期兩家定點醫院和61家發熱門診的基礎上,武漢市分5批共征用了51家綜合醫院,總計提供1.2萬余張床位[19]。突擊新建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分別編設1 000張、1 600張床位;后又臨時征用大型公共設施改造建設13家方艙醫院,可提供救治床位13 348張。最終實際投入使用共16家方艙醫院。武漢新冠肺炎病人數量迅速增加,與短時期內病房床位數量及醫療物資儲備量嚴重不足互為因果,加劇了疫情發展。
由此可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影響規模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目前我國醫院的編制與開放床位數、醫護人員配置規模和醫療物資儲備量均基于常規的設施功能定位、發病率和人口基數。根據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三級醫院評定的標準床位數是大于500張,省辦及以上綜合性醫院床位數一般以1 000張左右為宜,原則上不超過1 500張。這就決定了既有醫療資源(包括特定醫院、科室)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時遠不能滿足需求。
3.2 城市醫療衛生設施規模數量與響應預案
我國醫療衛生領域在不同屬地層級實行資源梯度配置。地市級及以下,基本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資源按照常住人口規模合理布局;省部級及以上,分區域統籌考慮,重點布局。整體來講,我國存在著醫療衛生資源總量不足、質量不高的狀況,但城市地區的醫療衛生資源相對處于梯度的高位。下文以中部地區兩座省會——山西省太原和湖北省武漢為例,進行研究。太原數據來自現場調研統計成果,武漢數據主要來自新冠肺炎疫情實時報告。
太原醫療資源條件良好,省直、市直三甲醫院數量在中部地區6個省會中名列前茅。截至2019年底,太原市現狀公立醫院共有開放床位35 139張,公立醫院每千人口床位約7.95張,每千人均床位數在全國各大城市中排名第一①數據來自太原市城市發展戰略規劃(2018—2050)專題研究《以人為本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和社區規劃》(專題主持:黃怡)。。2003年SARS暴發時,山西省是全國疫情重災區之一,太原又是山西的疫情重災區,疫情期間在山西省人民醫院附近緊急改建了可容納500張病床的后備醫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太原不是疫源地,輸入性和感染性病例數量可控。太原市第四人民醫院作為定點醫院接診,開放床位數680張。顯然,每一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情形都難以預料。
就響應能力的基態而言,武漢的醫療資源、醫療力量在全國城市中位居前列。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時,武漢市金銀潭醫院與市肺科醫院兩家傳染病醫院的開放床位加起來只有842張[20],已遠不能用捉襟見肘來描述其包括床位在內的醫療資源匱乏的現狀。先是征用和新建定點醫院,接著征用賓館、學校、體育場館等社會場所作為方艙醫院。同時藉“全國一盤棋”戰略,調集國內精銳醫療隊伍,動員國際國內應急醫療物資,才能與疫病鏖戰。
當SARS、新冠肺炎此類烈性傳染病導致的公共衛生事件突發時,要求城市響應能力短時期內達到激發態。應急能力首先體現在醫院開設發熱門診數、床位數兩個主要指標上,當然還有技術力量、設備條件和管理水平。醫護人員、醫療物資固然可以跨區域調配,醫療設施則需要就地安排。這就要求城市未雨綢繆,及早制訂響應預案。首先應充分掌握各類醫療衛生資源的存量、增量及分布情況,尤其是公立醫院的單體規模、床位數量、建設標準和大型設備配置。其次是模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展的分級響應進程,合理制定資源總量標準,確定應急征用的定點醫院名單,對不同級別、類型機構床位的比例關系進行適當調整。需要指出的是,并非現有醫院都能全數、盡快投入使用,有些醫院不具備改造基礎,比如未設發熱門診,急診與重癥仍需維持,病房騰空、病區改造以及醫護人員培訓需要時間等。
根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性質,應制定不同的響應預案。比如,在建有核電站、核設施、大型核輻射裝置的重點地區來說,核輻射災害產生的患者數量相對穩定;在地震、洪澇災害多發地區,可能形成流行性乙型腦炎、瘧疾、黑熱病等蟲媒傳染病。傳染病是最難應付的,對人口高度密集的各類大城市尤其如此,疫情管控時機不當,感染者數量很可能呈指數級增長,常規的醫療設施規模數量根本難以響應。
3.3 城市醫療衛生設施空間布局及響應預案
基本醫療服務和公共衛生資源的空間布局應與其規模數量梯度配置的原則對應。地市級及以下,按照常住人口規模和服務半徑合理布局;省部級及以上,分區域統籌考慮,重點布局。受城市性質、歷史、開發等諸多因素影響,許多城市的醫療衛生設施整體上存在結構與布局不合理、空間發展受限等問題。常見的空間布局呈現為中心集聚和等級分布兩種模式,作為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響應,還出現了郊區集中收治的“小湯山”應急模式。以下結合GIS方法,對太原市中、高等級醫院和武漢市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的空間布局進行圖示分析和定性描述。需要指出的是,精確定量的醫院聚集性分析評估是可行的,但定量程度受多重因素影響,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圖1太原市中心城各區中高等級公立醫院分布圖

圖2 武漢市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分布圖
3.3.1 中心集聚的非均衡模式
由于城市建設發展的歷史原因,許多創辦較早、實力精強的綜合性或專科高等級醫院一般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區。以太原為例,目前中心城區的老城區醫療機構集中,省屬、市屬、企業與事業以及部隊辦的三級公立醫院等優質資源,多分布在迎澤區、杏花嶺區,小店區、萬柏林區次之;汾河兩側差異明顯,河東的二級、三級醫院數量顯著高于河西。“城六區”中的晉源區、尖草坪區,郊區陽曲縣、清徐縣、婁煩縣的醫療資源相對不足(見圖1),郊區區縣尚未能平均配置一所二級甲等醫院。
武漢的醫療設施分布也呈現鮮明的中心集聚模式,全市大中型醫療設施集中于老城區。就武漢三鎮來看,高等級醫療設施在漢口地區最為集中,武昌地區次之,漢陽地區數量最少。就各區來說,高等級醫療設施數量在江漢區最多,江岸區、武昌區較多,青山區、東西湖較少,整體上越向外圍城區靠近,醫療設施布局越稀疏(見圖2)。
常規狀態下,醫療設施中心集聚的模式造成了各醫院運行負荷及其所在地區城市交通負荷的不均衡。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患者就診而向城市中心地區醫院聚集,特別是當疾病傳播途徑屬于直接傳播、接觸傳播、氣溶膠傳播等方式時,極大增加了傳染病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區公共場所大量擴散的風險幾率。
3.3.2 等級分布的均衡模式
層級完善、合理布局的醫療衛生設施體系,均等化、科學化的城市醫療衛生設施布局,是大多數城市醫療衛生領域發展和醫療衛生設施布局的目標。如果城市已編制醫療衛生相關規劃,特別是醫療衛生設施布局規劃,并能付諸實施,那么在城市擴張和新城建設中,各類醫療衛生設施按等級合理布局是可能的。
以武漢為例,近年來在外圍的新城建設中,如武漢開發區、東湖開發區和后湖等地區,構建了“新城中心—組團中心—社區中心”的醫療衛生體系,一個新城中心建設一座三甲醫院,一個組團建設一座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一個社區建設一座社區衛生服務站。太原則將計劃遷建或擴建的醫院分散布局,促進新城建設,使醫療設施在更大范圍內方便群眾,惠及全市。
等級分布的均衡模式是有效利用醫療資源的理想狀態。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早期階段,當患者數量非常有限時,按照就近收治或分布式接診的原則,級配合理、分工明確的醫療救治設施體系是有效的。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患者數量不斷增加,武漢市持續分批征用醫療設施,主要是基于現狀資源、按照等級分布原則調配的,每一批征用中都考慮到各區的服務范圍均衡;前后批次之間則基本是先征用醫院,后征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最后臨時征用非醫療設施加以改建,收治輕癥患者。由于醫療設施分布不均衡,各區的醫療條件不一樣,一些危重癥、重癥患者需要轉診轉院,這個過程可能給患者帶來生命風險。
3.3.3 郊區集中收治的“小湯山”應急模式
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特別是傳染病類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來說,“集中患者、集中專家、集中資源、集中救治”無疑是最有效的方式。針對常規醫院中心集聚模式和等級分布模式的不足,出現了專門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醫院,通常選址在郊區,遠離高密度人口地區,本質上是一個傳染病隔離區,可以阻斷傳染性疾病在城市中大規模傳播的途徑。2003年SARS疫情中,北京在昌平郊區小湯山鎮建立小湯山應急定點醫院,用于集中收治SARS患者。這一模式是依據“大專科、小綜合、應突發”的要求,集中收治傳染性疾病患者和承擔重大傳染病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救治,成為城市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救治中心。目前,國內多個城市已建成“小湯山”應急模式的醫院(見表2)。疫情期間在超短工期內突擊建成的應急醫院大多具有野戰醫院特點,即簡易、適用,在技術要求上較一般野戰醫院復雜。其中一些應急醫院由于選址過于倉促,其選址的合理性及潛在影響還有待驗證。
大多數單一功能的“小湯山”模式應急醫院,往往在某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建成啟用,此后則可能長時間處于廢棄狀態,直到下一次事件發生,再重新修繕或擴建投入使用。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中,時間意味著生命,寧可“床等人”,不能“人等床”。因此一些綜合條件良好的醫院長期維持運行狀態,例如南京江寧的南京市公共衛生醫療中心和位于上海金山的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
4 醫療衛生服務效能與城市高效響應能力分析
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高效響應能力而言,醫療衛生設施的硬件基礎固然重要,醫療衛生服務效能的軟件基礎同樣不可忽視,常規狀態下醫療衛生服務高效有序的供給是前提。目前我國城市醫療衛生體系相對成熟,但是還普遍存在醫療衛生服務效能不足的問題,這潛在地制約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響應能力,構建完善恰當的診療機制則可提升響應能力。
4.1 我國城市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現狀
我國已建成覆蓋城鄉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該體系由醫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組成(見圖3)。歷次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實踐表明,城市公立醫院和公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縣級以下)是主力響應力量,政府專業公共衛生機構則發揮著管理、協調及支持作用。在現狀常態的城市醫療衛生服務供給中,由于醫療服務體系層級、資源要素之間的協調平衡程度存在地域差別,部分城市的服務體系甚至呈現碎片化特征,客觀上有必要在該體系之外建立城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體系或緊急醫學救援體系。

表2部分城市“小湯山”應急模式醫院一覽
4.2 城市醫療衛生體制弊端與響應能力制約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形成已經揭示了城市在響應能力方面的潛在危機,而這種普遍的對響應能力的制約是由諸多體制弊端造成的。
4.2.1 城市醫療衛生資源結構配置欠合理
從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到醫療衛生設施專項規劃,普遍存在“重醫療、輕防保”的態度。一些醫療機構注重營利性,包括部分公立醫院在內追求經濟效益;預防保健工作則側重社會效益,發展相對滯后。這種主觀選擇懷有僥幸心理,并集中反映在城市醫療衛生資源的結構配置上。疾控工作得不到應有的重視,防保資源存在供給約束,導致缺少足夠的人力、物力與能力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遏制在早期階段,最終防控風險將轉變成醫療壓力。在烈性傳染病疫情中,例如新冠肺炎疫情中,瞬時集中的應急醫療資源短缺延遲了醫院接受患者的響應時間,即一個傳染病患者從被確診到被安置隔離的時間。這個時間越長,傳染病傳播的范圍就越廣,疫情后果越嚴重,最終擊潰城市醫療系統。
4.2.2 突發公共健康風險傳導機制失靈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往往是一個地區、城市乃至區域的公共治理能力薄弱的合成結果,直接原因則是城市突發公共健康風險傳導機制失靈,這在2003年SARS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無疑。突發公共健康風險的監測采取自下而上層層報告的線性傳導機制,而不是網絡狀的信息監測預警系統。這種單一路徑的管理機制顯然不夠科學,本身具有相當大的風險。當基層政府及相關責任部門行政效率低下時,就會嚴重阻礙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響應進程,延遲應急醫療衛生服務的有效供給,甚至貽誤戰機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然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風險傳導機制、醫療衛生服務供應機制的設計并不在常規的空間規劃范圍之內。

圖3 我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構成
4.2.3 突發公共健康風險評估不足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大規模和復雜性,要求在醫療衛生相關規劃中包含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風險的評估機制與方法。伴隨此類事件進展的風險評估可能需要解決新的、不同的風險問題。對于某些突發事件,需要來自不同領域風險評估小組的協作,以掌握事件風險的全貌,例如疾病傳播動力學和控制措施、臨床癥狀嚴重程度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僅僅依據公共衛生流行病學的單一學科知識而得出的“可防可控”凸顯了風險評估的不足,缺少對于疫病在城市性質規模、城市聯系等多樣因素構成的社會時空框架中的完整認知。歷次事件的教訓表明:突發公共健康風險是大規模的,可能波及全球;是全方位的,可以引發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難題;是長時間的,可能持續數月乃至經年。
4.3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的診療機制優化
針對一些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典型的疾病社區傳播特征,可以優化構建合理的分級診療機制。例如2017年起太原全面推行的按病種分級診療制改革,通過“基層首診、雙向轉診、急慢分治、上下聯動”,不但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就醫秩序,還可以有效落實各級醫療設施功能定位,提高醫療衛生資源的整體效益。特別是當傳染性疾病類型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于萌芽階段時,易于在社區層面及早發現和有效控制。當然這對城市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能力提出了要求。由三級醫院帶領二級醫院及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緊密發展的分級診療制模式,在我國的整體推廣尚需時日。
5 高效響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整體規劃策略
高效響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將其沖擊降到最低,除了完善社會系統的整體機制,就空間規劃領域而言,圍繞關鍵性的城市醫療衛生設施規模布局和醫療服務效能議題,可形成提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響應能力的整體策略。
5.1 將公共衛生防疫納入城市應急專項規劃
提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高效響應能力,要求在常規的醫療衛生相關規劃之中增加公共衛生防疫應急內容,即在國家、區域、城市層面,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方案切實體現到各級醫療衛生體系規劃或區域衛生規劃中,具體落實到城市醫療衛生設施專項規劃和城市應急專項規劃中。這已是勢在必行。
城市醫療衛生設施專項規劃既是面向常規發病概率下的醫療衛生資源配置,其應急預案也應涉及區域公共衛生服務的系統整合、片區定點醫療機構的分工協作與聯通共享機制,以提高緊急醫學救援能力,提升對不同層級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響應能力。
城市應急專項規劃應針對多種災害與危機應急以及衛生防疫應急,涉及醫療衛生系統與城市決策管理、交通、傳統與新型基礎設施、供應鏈、科普教育等系統之間全方位、立體化、多層次、綜合性的監測、預警、應急、協同。
5.2 預控應急用地與提升設施標準
在城市醫療設施專項規劃等空間類型的規劃中,通過應急用地預控和設施標準提升,可以加強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響應。在嚴格規劃增量、科學調整存量的原則下,在城市外圍預留應急后備醫院用地、防疫物資倉儲用地及相關基礎設施;在新城地區,重視社區醫療衛生設施規劃建設;在中心城區,結合城市更新,優化調整醫療衛生設施布局,均衡急救站點分布,提高醫院的改造適應性(例如發熱門診的“三區二通道”要求),與分級診療機制相適應等。
參照國家公共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設施標準,通過設定指導性指標和強制性指標,突破常規的醫療設施規模標準限制,上調部分公立傳染病醫院的單體建設和床位配置規模。例如武漢市金銀潭醫院,作為湖北省、武漢市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定點醫院,開放床位數為720張,自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8日累計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 200多人[21],而截至當天的排查數據,全市尚有確診重癥患者1 499人無法入院治療[22]。
6 結語
大流行病仍在全球肆虐,我們甚至不確定疫情的結束時間與最終規模。面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帶來的城市、區域、國家和全球層面的巨大負面沖擊,醫療衛生體系規劃、醫療衛生設施規劃已遠遠超出某一部門規劃、某一城市專項規劃的意義,而具有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意義[23]。以科學的規劃及其有效的實施來應對突發公共衛生風險,實現城市響應能力躍遷,是空間規劃發展面臨的新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