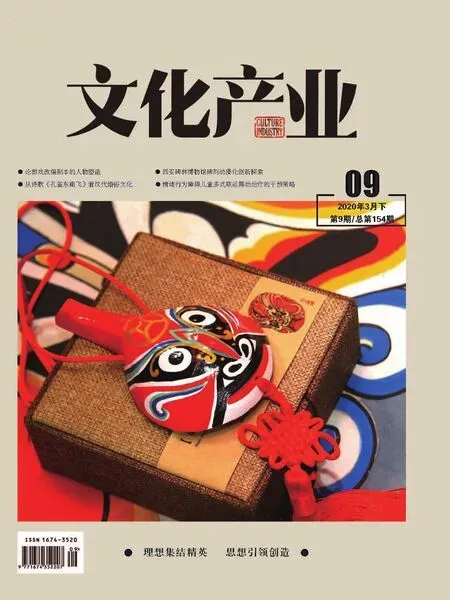淺析南宋《魯國之圖》中的山川表現
◎鄒家賢
(西安美術學院 陜西 西安 710065)
今天我們看到的《魯國之圖》是藝術工匠和畫匠們藝術創作的結晶,是他們辛勤勞動的成果。該圖功能性與藝術性的結合,凝聚著我國勞動人民的智慧和藝術修養。現以南宋《魯國之圖》為對象,探討該石刻地圖的畫面內容、局部山川構圖、表現手法并與同時期繪畫作品進行對比分析。
一、《魯國之圖》的來源
俞舜凱曾游學于山東,無意間得到《魯國之圖》底本;該圖為宋人所畫,后俞請人將該圖刻在石上。立碑年代為紹興甲戌,即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該圖為長方形,圖碑高2.17米,寬1.12米。此圖以曲阜魯城和魯城四郊為中心,并且標注了東西南北四個方向。該地圖是以俯瞰的視角,用平面處理的方式描繪房屋建筑,正面房屋采取平面描繪,側面房屋改變房屋角度進行平面處理。古人在沒有大測量儀器的情況下測出了山與山之間的大小比例,根據實景進行創作,在寫實的基礎上加以修飾,使其繪于圖面中令整體和諧,不突兀。
該石碑1985年出土于湖北省陽新縣一中學內,現藏于湖北黃石市陽新縣,但已毀壞嚴重,不僅圖碑裂斷,圖上所繪畫內容也無法看清了。中國國家圖書館現今珍藏著唯一一份《魯國之圖》早期拓本地圖。目前研究《魯國之圖》相關方面的文章有:綜述性的文章[1-3],考辨性的文章[4],以及借用《魯國之圖》對曲阜古城址進行考證的文章[5]。目前對《魯國之圖》進行的研究,都未從該地圖中的山川表現角度入手。因此,本文對《魯國之圖》中的山川表現進行研究,跟南宋同時期的山水畫進行對比分析。
二、《魯國之圖》局部圖面分析
該圖碑概括地描繪了泰山之下、鳧山以上的山川景色。這幅圖中的山川大多分布在整幅圖的上下兩端,居于整幅圖的邊角位置,雖說是依照山川的實際方位繪制,但是繪圖者依然做出了取舍。泰山以東還有比較低的丘,但是繪圖者將其省略,用留白來代替,這一點顯示了中國傳統山水中留白的特點。同時,也因此圖是功能性的地圖,山川只是地標作用,所以有選擇性地對其進行表現。
《魯國之圖》是以平面線刻來繪制的地圖[6],地圖中相關圖形的遮擋關系運用得很自如,如圖1所示,可以看到樹木遮擋了建筑,建筑又遮擋了山川,表現出了遮擋關系。樹木同樣用平面表現手法加以表現。經過對《魯國之圖》現存拓片的辨析,能看到一些山水畫中常用的近實遠虛、虛實結合的手法,即近處的景物描繪較為細致,遠處景物則相對概括,使圖面整體有一個層次之分,產生一種前后空間的感受,體現了宋代高超的繪畫技巧。這種動靜與虛實相結合的結構方法深得中國古典景觀美學的精髓,并且在南宋院體畫的眾多作品中得到充分的體現,是晉唐以來中國山水畫藝術發展至此時期到達巔峰境界的重要標志之一,有美術史家概括此時畫作的特點是:“善于虛實結合,以較少的景物控制大面積空間,表現特定的意境,并給人以較大的想象余地。”[7]

圖1 南宋《魯國之圖》線圖
三、南宋山水畫對其產生的影響
由于政治和軍事接連受挫,南宋已然是“半壁江山”,大批前朝畫家的“輸入”,促進南北繪畫風格的融合。南宋在經歷變革后,繪畫藝術非但沒有因此陷入低潮,相反形成了一種較為新穎的構圖模式。李唐作為前朝山水畫的集大成者,經歷變遷后在畫面構圖上也有了“全景”到“邊角”的轉換,北宋的全景式構圖不見了,轉而取自然山水一角進行創作。這種邊角式的構圖方法具有豪放、簡約的新面貌。在這種影響下,眾畫家在此基礎上再創新,運用截景特寫方法,留下大面積空白,構圖簡潔不空洞;景物雖有取舍,但構圖上還是完整的;畫家思慮周全地協調各景物間比例關系的微妙變化,留白部分被巧妙處理為紐帶,令畫面融為一體。
《魯國之圖》中描繪山川的部分,大多分布在該圖的上下兩端,且山川部分較多。這是因為《魯國之圖》不僅僅描繪了一座城市,而是描繪了多座城市,涵蓋面積較大。經過修復,拓本保存也較為完好,可以清楚地看到山峰的走勢以及描繪山峰所用的筆法。尤以“魯國之圖”四字下的山川為例,左右兩峰相鄰,卻各有各的形態。左側為“梁父山”,右側為“泰山”。以當時的技術手段斷然測不出泰山究竟比梁父山高多少、寬多少,聰明的宋人通過對自然敏銳的感受以及高超的技法進行構圖,將一眾山峰合理又巧妙地安排在一處,通過山勢的高與低、寬與窄、平緩與奇險以及用筆的多與少來加以區分,使它們雖聚在一處,卻各有各的姿態、不盡相同,盡顯北方山峰險峻的特征。山與山之間既有緊密聯系的部分,又有為了避開具有地標動能性的標志而斷開的部分,斷開的部分似為山水畫中的留白,起到聯通畫面的作用。圖中的山川分布在不破壞其功能性的情況下也有所美化。
四、結語
《魯國之圖》記錄了當時眾城市的不同風貌,更與山水畫創作融合,可以在小尺幅地圖中,高度概括地表現各景物。《魯國之圖》將自然山水中的復雜空間關系轉化到紙面上進行創作,使動能性和審美性加以融合。自然山水和繪畫藝術趨于成熟的標志,就是能夠自如地運用對宏觀空間與微觀空間的創造能力。這幅石刻城市地圖,就是將地圖功能性與山水藝術性融合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