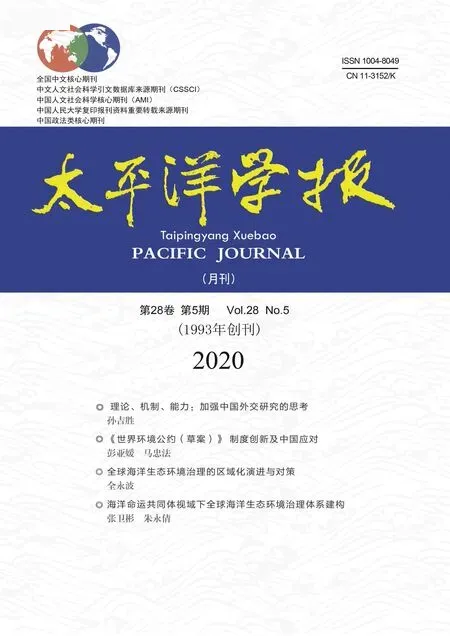經濟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能力建構(1970—2013年)
盧凌宇 胡 怡
(1.云南大學,云南 昆明 650091;2.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1620)
本文旨在探討經濟全球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對中國國家能力的影響。(1)下文若非特別注明,均以“全球化”指代“經濟全球化”。國家能力通常指國家將自己的意志轉化為現實的能力。中國國家能力是一個具有重大理論和政策價值的議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很多關注。1993年,王紹光和胡鞍鋼在《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一書中指出,1980年代中央與地方分灶吃飯的財政的大包干體制導致了政府財務高度分散,國家財政汲取能力急劇下降,嚴重影響了政府履行提供公共產品等基本職能。該書既成為1994年中國實行中央地方分稅制的理論基礎,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能力研究的起點。(2)王紹光、胡鞍鋼著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頁;[美]喬爾·米格代爾著,張長東等譯 :《強社會與弱國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根據國曉光和王彩波的綜述,近二十多年來,國外學者的中國國家能力研究主要致力于從社會經濟資源(如私營經濟、社會組織)、組織制度資源(如貪污腐敗、地方主義和政治派系)和思想意識形態資源(如市場經濟、信息技術革命)等三個方面描述中國國家能力的變化并對之做出解釋。(3)國曉光、王彩波 :“海外對中國國家能力的研究”,《國外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第82-88頁。關于組織制度資源對國家能力的制約作用,也可以參考國曉光 :“中國國家能力的政策困境與應對——基于政策執行的分析”,《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6年第2期,第10-15頁。例如,拉迪(Nicholas Lardy)等學者認為,私營經濟和社會組織等因素削弱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市場化改革則打破了個人對國家的制度性依賴。相反,狄忠蒲(Bruce Dickson)等則指出國家有效地吸納和規制了來自社會力量的挑戰,比如社會組織通常并不尋求體制外的自主性,而是努力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內承擔角色。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體也可以納入上述類型學。比如,孫明軍發現中國國家能力由于效力上的相對下降和范圍上的絕對收縮,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家總體意志的實現,導致了國家直接控制的社會資源的相對量和絕對量大大減少、行政命令的控制作用日益削弱等后果。皇娟則把中國國家能力的不足歸因于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的不對稱以及地方官員以地區生產總值(GDP)為綱的考核標準。(4)皇娟 :“中國國家能力不足之分析:基于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角度”,《理論與改革》,2010年第2期,第32-35頁。
現有研究的一個結構性缺陷是較少涉及影響中國國家能力建設的國際因素。對于中國而言,四十年來政治、經濟和社會所獲得的巨大發展是改革開放結出的碩果,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一個重大國際背景性因素就是經濟全球化。中國能夠在短短四十年之內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離不開對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和推動。
按照赫爾德(David Held)的經典定義,全球化是“一個體現了社會關系和交易的空間組織變革的過程,產生了跨大陸或者區域間的流動以及活動、交往和權力實施的網絡”,(5)[英]戴維·赫爾德等著,楊雪冬等譯 :《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馬峰成 :“全球化概念分析”,《理論前沿》,1999年第18期,第17-18頁。主要的特點是“物資、資本、服務和人員的跨境流動以及觀念和規范的跨境擴散”,(6)盧凌宇 :“全球化對西歐國民生活滿意度的影響(2002—2014年)”,《歐洲研究》,2017年第6期,第90頁。其中經濟全球化既是全球化的基礎和起點,又是全球化發展水平最高的維度。加利特(Geoffrey Garrett)就將全球化狹義地定義為經濟全球化,基本內容為貿易自由、跨國公司的擴張以及巨大的跨國資金流動的出現。(7)Geoffrey Garrett, “The Cause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3, No.6/7, 2000, pp.941-991.
在經驗研究中,學者們對于全球化對國家能力的影響持不同的觀點。一方面,有學者發現二戰后的國際經濟交流提升了國家能力。具體而言,全球化迫使政府擴張規模以應對全球化所產生的外部風險和內部不穩定。(8)毛捷、管漢暉、林智賢 :“經濟開放與政府規模——來自歷史的新發現(1850—2009)”,《經濟研究》,2015年第7期,第87-100頁。一個國家和城市經濟越開放,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的要求就越高,政府就越有動力進行擴張,以滿足人民的安全和福利要求。(9)David R. Cameron,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Econom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2, No.4, 1978, pp.1243-1261; Janet Stotsky et al., “Trade Liberalization, Exchange Rate Changes, and Tax Revenue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17, No.2, 2006, pp.261-284;楊燦明、孫群力 :“外部風險對中國地方政府規模的影響”,《經濟研究》,2008年第9期,第115-122頁;尚元君、殷瑞鋒 :“對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能力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第12-15頁。另一方面,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等認為全球化顯著地削弱了國家能力和權力,非國家行為體正在替代國家的經濟和社會功能。(10)Susan Strange, “The Erosion of the State”, Current History, Vol.96, No.613,1997, pp.365-369.羅迪克(Dani Rodrik)也指出,勞動力、技術以及人員的流動等會加強國家間競爭,從而使得國內的稅收減少,抑制了國內政府的稅收收入。(11)Dani Rodrik,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pp.81-94; Barsha Khattry and Mohan Rao, “Fiscal Faux Pas? An Analysis of the Revenue Implication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30, No.8, 2002, pp.1431-1444.
一、理論建構
本文旨在對經濟全球化對1970年代以來我國國家能力的影響做一個系統的論證和測試。國家能力是內涵很豐富的概念,包括財政汲取能力、調控能力和強制能力等多個維度,其中汲取能力被公認為國家能力的基礎和代表。(12)王紹光、胡鞍鋼著 :《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頁。汲取是國家把社會資源轉化成公共資源的主要手段,也是國家的社會滲透程度的重要標志,其他形式的國家能力——比如軍事能力和官僚機構的效率等——都直接受制于財政汲取的水平。在經驗研究中,汲取能力通常以稅收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來測量。本文沿襲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傳統,把中央政府的財政汲取能力用作國家能力的指標。
本文的理論創新主要體現在自變量的設置上,即探討經濟全球化的不同維度對中國國家能力的影響。在此我們遵循加利特的類型學,把經濟全球化劃分為貿易、投資和國際金融三個維度,并對它們的作用依次展開探討。(13)Geoffrey Garrett, “The Cause of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3, No.6/7, 2000, p.941.
1.1 貿易全球化
貿易全球化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以1978年為起點,中國進出口總量快速增長,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也水漲船高,這個效應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表現得尤其明顯。關稅水平和非關稅壁壘的降低改善了中國的外貿環境,中國的進出口都實現了巨大的飛躍。2004年,中國的貿易總量已經占到GDP的70%,而當年日本的貿易總量的GDP占比只有24%。(14)William Overholt,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U.S.-China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RAND Corporation, 2005, pp.1-15.在2008和2016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同比都有所下降。政府財政收入在這兩個時間點上雖然依然呈上升趨勢,但增速有所下降。2008年財政收入增長率為11.7%,明顯低于前后兩年的增長率,2016年的增長率為4.5%,增速進一步降低。
出口是總需求的一部分,出口的增加促進了國內生產的增長,同時給國內企業帶來了大量的盈利,企業所得稅等其他稅收相應增加;進口雖然擠壓了國內商品的生存空間,但由于交易在國內發生,也使得政府收獲了更多的稅收,同時刺激國內廠商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
2001年12月加入WTO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事件,它標志著我國“接受WTO主導的自由貿易政策。”(15)薛榮久 :“后危機時代中國外貿政策調整的選擇”,《中國經貿》,2010年第3期,第12頁。為了達到GATT/WTO的要求,中國在入世前后對本國法律、行政法規和規章制度做了大刀闊斧的調整和修改,重點是結束經濟貿易稅收法規實施的地域差別、建立和健全出口退稅制度、放棄限制國內企業在當地購買產品等。(16)蘇長和 :“國際化與地方的全球聯系:中國地方的國際化研究(1978—2008年)”,《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11期,第25-26頁。同樣重要的是,為了配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進程以及應對國際貿易環境的變化,中國還調整了對外經濟貿易部門,分別在2001年5月和11月對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進行了兩次重要的機構調整和修改:撤銷了外經貿發展司和對外貿易管理司這兩個職能高度重合的司,并且組建了對外貿易司,增強了對外經貿政策制定的整體性與協調性,同時成立了世界貿易組織司和進出口公平貿易局,使得中國政府能夠保證在入世之后能夠以較快的速度處理有關的事務。(17)“修改涉外經濟第一法 對加入WTO作出法律承諾”,《北京晚報》,2001年3月11日。2003年,中國決定把原外經貿部的外貿管理職能和國家經貿委的內貿職能進行合并,組建商務部,由商務部主管我國的國內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事務。新設立的商務部內設機構主要包括原外經貿部的21個司(局、廳)和新調整設立的職能屬于原國家經貿委和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的4個司(局),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少部分外貿監管職能也并入了商務部,相較于原外經貿部457名的編制,商務部機關行政編制大幅提高到860名,(18)《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商務部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通知》,2005年8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05-08/12/content_8167.htm。使得每個部門都有更加充足的人力資源應對急劇增加的工作量,維持和提高組織的運轉效率。簡言之,外經貿職能的歸并和商務部的成立既達到了WTO融入全球化的要求,又順應了內外貿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商務部的組建和運作顯著地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入世以來,我國國際貿易一直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2003年在世界貿易的排名從2002年的第五位上升到了第四位。如今,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貿易全球化的一個負效應是頻繁、復雜的人員和物資跨境流動所導致的毒品槍支販賣和艾滋病(HIV)等疾病傳播對國家安全形成的威脅。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和貿易開放帶來了侵蝕中國的境外毒品。西南境外“金三角”地區的鴉片、西北境外阿富汗的鴉片和海洛因、東南境外的搖頭丸等借助高技術手段快速地向我國境內滲透。(19)鐘巖 :“新時期中國毒品禁而不絕的原因及對策探析”,《探索與爭鳴》,2005年第7期,第69頁。販毒常常牽涉到武器軍火交易,既增加了毒品控制和管理的難度,又威脅到邊境的社會治安。這是對中國國家能力的重大挑戰。(20)Peter Newell,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State, IDS Working Paper 141,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2, pp.1-25.面對非法貿易的威脅,中國一方面積極參與和利用聯合國、世界海關組織、國際刑警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制,(21)楊鳳瑞:“我國當前的禁毒形勢與國際合作”,《公安研究》,2001年第6期,第16頁。另一方面著力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比如,為了應對如毒品、槍支以及傳染性疾病的流動和傳播,中國加強了國內的安保系統,公安部門加強了對毒品槍支的監管,特別是在中國的邊疆,配備高技術裝備,加強對警察和其他武裝人員的訓練,提高他們的軍事斗爭和辦案能力;安檢部門也在機場、火車和地鐵出入口提高了安檢要求和標準。此外,隨著中國企業和消費者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逐漸增強,我國經濟的風險和成本也在不斷上升。在入世前后,中國的國有企業丟失了440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制造業喪失了2500萬工作崗位,原有的125家汽車生產廠家被整合為3~6家。(22)William Overholt,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RAND Corporation, 2005, pp.1-15.世界經濟的起伏會嚴重地影響我國的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國民經濟的脆弱性。(23)楊燦明、孫群力 :“外部風險對中國地方政府規模的影響”,《經濟研究》,2008年第9期,第115-121頁。盡管存在這些弊端,我們認為貿易全球化給中國經濟帶來了翻天覆地的積極變化,它的積極作用占絕對上風。
綜上,本文假設一:貿易全球化顯著地增強中國國家能力。
1.2 投資全球化
國際投資包括外國資本來華投資和中國資本海外投資。中國入世之后,中國資本對海外投資急劇上漲,2017年,中國對外投資凈額為1582.9億美元。截至2017年底,中國2.55萬境內投資者在全球189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額合計6萬億美元,(24)《2017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商務部網站,2018年9月28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dgzz/201809/20180902791492.shtml。關于中國對外投資的簡況,也可參見:Huiyao Wang and Miao Lu, China Goes Global: How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is Transforming Its Business Enterpris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12-20, 187-188.居世界第三位。本節將聚焦于外來投資對中國國家能力的影響。(25)關于對外投資對中國經濟和國家能力的影響,學者們普遍認為是積極的,比如釋放產能、對沖人民幣升值壓力和改善出口格局等,請參考:錢雪松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動力和影響分析”,《當代經濟》,2007年第4期(上),第116-117頁;謝岷 :“試論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國際貿易問題》,1987年第3期,第10-16頁。
根據世界銀行和其他世界組織的調研研究,中國是從外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以下簡稱FDI)中受益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之一。FDI既為中國帶來了資本,創造了就業,又刺激了出口和進口。開放的經濟增強了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刺激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合理地配置社會資源,實現比較優勢,享受經濟開放帶來的收益。
外資在2001年中國入世后大規模進入。根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委員會的數據,在2000—2016年間,中國是吸引FDI總量最大和增速最快的國家,年均流入中國的FDI為591億美元,其中2010年流入724.06億美元,2016年流入 1 083.12 億美元,2010—2016年間年均增長率為12.39%。(26)丁鋒、姚新超 :“外商投資、技術溢出與能源效率”,《工業技術經濟》,2018年第6期,第154-159頁。外商直接投資吸納國內勞動力的效果也較為顯著,從2000年到2015年,外商直接投資的企業在國內的就業占比從2.77%增長到到6.90%,數量上增長了2 100多萬。與此同時,中國實際利用外商投資數額逐年提高,到2018年該數額已經達到了1 349.659億美元。外資企業的生產所需原材料部分通過進口來獲得,最后的成品部分銷往外資來源國和地區,這就間接促進了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進一步擴大了政府的稅基,促進了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
政府部門負責對FDI的審批、監管和稅收。國外投資的快速增長對中國政府的調控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政府著手簡化辦事程序。長期以來,由于多頭管理,外來投資的申請和資質審查非常繁瑣,審批耗時過長,從立項到正式開展投資至少需要7個月。為了改善國內投資環境,提高對國外資本的吸引力,中國不斷簡化投資的行政審批、提高辦事效率。2019年3月,政府做出規定,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將不再需要經過專門的審批,只要行業不在負面清單范圍內,都可以在當地的工商局進行企業注冊登記。這些規則政策的規定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外來直接投資的審批時限,同時通過對準許進入中國的FDI種類進行調整和篩選,對特定時間段內中國的產業發展重點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
對FDI的管理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不僅如此,由于FDI本身的技術溢出效應,中國政府日益重視引導企業通過追求技術創新來實現發展。更重要的是,外資企業通過直接的內部轉移、許可證和管理營銷合同等方式,為國內企業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手段,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27)Gregory C. Chow,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 Working Papers 87, No.115, 2005, p.2.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經濟往來形式多樣,比如國內企業為跨國公司提供原材料、零配件或提供銷售渠道與服務等。這種產業關聯關系促使國內企業按照外方要求來提高技術水平。激烈的市場競爭也迫使國內企業向外方模仿學習與改進,提高自身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實現技術進步。(28)沈坤榮、耿強 :“外國直接投資、技術外溢與內生經濟增長——中國數據的計量檢驗與實證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第90-91頁。此外,政府還大幅度增加了研發投入。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1995年中國科技研究和試驗經費支出僅為人民幣349億元,而2018年則達到了19 657億元,(29)數據來源:國家數據網,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訪問時間:2019年4月6日。相比1995年,擴大了近60倍。政府的重視和財政投入促進了企業對前沿科技的探索與研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國內企業對國外公司的技術依賴,使得國內企業有了較強的創新能力,增強了在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盡管如此,以跨國公司為代表的FDI是一把雙刃劍。它們既有助于中國企業實現技術發展,也加強了中國企業的技術依賴,削弱了中國企業的技術開發能力,妨礙了中國企業的技術升級。薛榮久也表示,全球化對技術較為落后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較大。(30)薛榮久 :“經濟全球化正負效應論”,《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8期,第45頁。外資企業為了保持自己的技術領先地位,向中國輸出的技術通常不是最先進和前沿的。引進國外技術固然在短期內節省了中國企業的科研支出,但從中長期來看阻礙了中國企業進行自主科技研發和實現自主產業升級。同時,向國外企業支付的技術引進的費用也顯著增加了企業運營的成本,削弱了國家的中長期財政來源,部分地抵消了投資全球化帶來的收益。盡管如此,我們認為總體上投資全球化的積極作用大于消極作用。
綜上,本文假設二:投資全球化顯著地提高中國的國家能力。
1.3 金融全球化
2019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進一步開放金融的十一條規定,主要措施包括允許境外資產管理機構與中資銀行或保險公司的子公司合資設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財公司,允許境外金融機構投資設立和參股養老金管理公司,以及放寬外資保險公司準入條件,取消30年經營年限要求等。金融十一條表明以前中國對金融全球化的參與程度還較低。盡管如此,中國參與全球化本身不僅推進了中國金融制度改革,也給中國帶來了大量的全球融資。
對于各國的經濟發展而言,融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31)厲以寧 :“全球化與中國經濟”,《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年第6期,第11-16頁。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既無內債又無外債。1980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僅0.57億美元, 2013年增長到1 187億美元,2018年高達 1 349.66 億美元,較之1980年,增幅為2 366倍。(32)數據來源:國家數據網,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訪問時間:2019年4月6日。國際金融市場不僅為中國投資者提供了高回報的機會,而且也提高了在中國的資本存量。國際資本進入到中國的第二和第三產業,促使它們擴大生產和再生產,推動了經濟的發展,擴大了政府的稅基。隨著對外融資渠道逐漸拓寬,中國著手整合金融活動規則,改革金融體制。在1978年以前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金融機構受到全方面的管制,銀行也缺乏活力。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形成了“一行三會”體制,即由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保監會來實施金融監管。2018年,中國政府為了解決現行體制下三個機構監管職責不清晰、交叉監管和監管空白的問題,將保監會并入銀監會,并將后者的職責定位為依照法律法規統一監督管理銀行業和保險業,確保銀行業和保險業合法、穩健運行,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和金融穩定,從而形成了銀保監會和證監會兩會各自監督其所負責內容的局面。不僅如此,從1993年起,國家進一步調整金融秩序,陸續出臺了《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等金融法律,確立了分業經營的體制。(33)Mark Robinson, “Hybrid States: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Capacity”, Political Studies, Vol.56, No.3, 2008, p.570.金融全球化還促使中國借鑒一些發達國家的管理手段與方法,改革本國的金融監管機構,同時重建官僚組織系統和經濟結構,以便有效地推動經濟發展。(34)Yongnian Zheng,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87-188.
在信息化時代,網絡和電子支付手段的出現對政府的金融監管提出了挑戰。電子科技類產品在電子交易中廣泛運用,快速取代了傳統的金融交易手段,交易方式不斷更新換代。各大國際金融中心的經紀人可以擺脫有組織交易所工作時間的約束,全天候地從事交易,全球范圍內資金劃撥和融通可以在瞬間完成。網絡的出現加劇了金融監管的難度,抬升了金融監管的成本。
除去技術發展帶來的監管困難,部分加入金融全球化也增加了國內經濟的風險,(35)Joshua Aizenman et al., “The Emerging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racing and Evaluating New Patterns of the Trilemma Configu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29, No.4, 2010, pp.615-641.削弱了國內貨幣政策的作用,使之只能對部分的國內經濟變量起作用,難以實現預期的宏觀經濟目標以及對國內經濟實施強有力的監督和管理。例如,資本過快地流入到外匯市場中會使人民幣升值幅度加快,而人民幣升值又降低了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優勢。由于中國的對外開放,國際資本流動和中國出臺的宏觀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日益緊密。貨幣升值或是貶值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快慢有很大影響,反之國際資本的流動也會使得國家的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和監管失去其本來的作用和影響,削弱了中國貨幣政策的自主性。(36)趙文勝、張屹山、趙楊 :“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對中國市場變化的反應分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1年第3期,第104-118頁。
另外,中央銀行對資本流入的抑制也會使人民幣存量上升。由于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大量向市場注入貨幣預期會出現較強烈的通貨膨脹。(37)同①。當國內經濟過熱時,政府往往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以減少貨幣的供應量,這會提高利率,并導致大規模的國際資本進入國內,結果增加了國內的貨幣供應量,降低了國家經濟政策的調控能力和預期的作用與效果,對國內貨幣的監管政策也會因此得到削弱;反之如果一國因經濟衰退而降低利率,國際資本又會大量進行逃離,達不到增加本國貨幣供應量的宏觀目標。
中國深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2007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11.9%,到2008年就已經跌落到9%,2009年是8.7%,連續三年下跌。中國銀行也由于境外股票債券縮水的影響而遭受較大的損失。(38)陳亞雯 :“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金融和出口企業的影響與政策建議”,《經濟問題探索》,2008年第8期,第62-63頁。股市低迷傷害了國內投資者,影響了國內的金融經營環境。此后,人民幣升值,出口成本上升,海外需求的下降使得國內企業產品過剩,造成大量沿海中小型企業破產。同時,資本賬戶的部分開放導致短期投資增加,地方紛紛出臺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吸引外資政策,導致中央難以對金融進行統一、有效的監管。
盡管存在著上述負效應,總的來看,中國對金融全球化的參與既帶來了很多國際資本,又推動了中國完善金融規則和相關法律。
綜上,本文假設三:金融全球化顯著地提高中國國家能力。
1.4 全球化
以上三小節的分析表明,對于中國國家能力而言,經濟全球化是把雙刃劍。然而,在貿易、投資和金融這三個主要維度上,全球化對中國國家能力的影響都是積極影響占據優勢,所以我們有理由期待經濟全球化本身顯著地增強中國國家能力。
應當承認,貿易、投資和金融并沒有窮盡經濟全球化的內涵。例如,按照喬西(Rakesh Joshi)的觀點,技術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也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內容。(39)Rakesh Josh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7-15.盡管如此,相對于技術和信息,貿易、投資和金融對于經濟全球化而言具有更強的基礎性,其中貿易是第一序列的經濟全球化,投資、金融、技術和信息等都是次生的因素。在功能上,貿易是全球化的起點。跨國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貿易的凈收益,金融是為了彌補貿易和投資的資金缺口。從時間上看,貿易和人類歷史相始終。相比之下,金融和投資全球化發端于1970年代中后期,1980年代得到發展,1990年代加速推進。(40)白欽先 :“經濟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的挑戰與啟示”,《國際金融》,1999年第6期,第11頁。技術和信息則附屬于貿易和投資。如果沒有貿易和投資,技術和信息在經濟上沒有價值。
綜上,本文假設四:經濟全球化顯著地提高中國國家能力。
二、數據與方法
本文將運用多元回歸分析對上述四個假設進行統計檢驗。檢驗的分析單元是國家/年。本文設置了兩種回歸模型:一是對中國國家能力的分析,原始數據覆蓋的年份是1970—2013年。這是統計分析的主體,目的是檢驗上文的理論猜想。二是對全球185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目的是比對全球化對中國國家能力的影響與對全世界、第三世界和發達國家群體的影響有何區別。本文統計分析的原始數據是1960—2018年間的權威宏觀政治經濟數據,但由于關鍵變量的數據有的始于1970年,有的截止到2013年,所以統計分析覆蓋的時間段是1970—2013年;除此之外,本文盡量引用最新的資料和研究。
統計分析的因變量是國家能力,具體而言是國家的征稅能力。本文采用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這支文獻對國家能力最常見的操作方式,(41)較近的研究可參考:Cameron Thies, “State Building, Interstate and Intrastate Rivalry: A Study of Post-colonial Developing Country Extractive Efforts,1975-2000”,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8, No.1, 2004, pp.53-72; Cameron Thies, “War, Rivalry, and State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9, No.3, 2005, pp.451-465; Cameron Th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Build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9, No.3, 2007, pp.716-31; Cameron Thies, “National Design and State Building in Sub-Saharan Africa”, World Politics, Vol.61, No.4, 2009, pp.623-69; Emizet Kisangani and Jefferey Pickering, “Rebels, Rivals, and Post-colonial State-building: Identifying Bellicist Influences on State Extractive Capac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2, 2014, pp.187-198; Jeffrey Pickering and Emizet Kisangani, “Foreign Military Intervention and Post-colonial State-building: An Actor-centric Analysi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31, No.3, 2014, pp.244-264.將之測量為中央政府稅收占GDP的比重,數據來源是庫格勒(Jacke Kugler)等的“相對政治能力”(relative political capacity)數據庫,覆蓋的年度為1970—2013年。(42)Jacek Kugler, Performance of Nation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經驗檢驗的自變量有四個,分別是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以及經濟全球化。其中貿易全球化被測量為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投資全球化則為一國吸引的外資占GDP的比例,金融全球化則側重度量一個國家的金融開放程度。這三個變量的數據來源分別是《世界發展指標(2017年)》和“三元悖論指數”(Trilemma Index)。(43)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17; Joshua Aizenman et al., “The Emerging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racing and Evaluating New Patterns of the Trilemma Configu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Vol.29, No.4, 2010, pp.615-641.經濟全球化是一個綜合指標,是實際國際經濟流量(包括貿易、外來直接投資、投資組合和支付外國人收入占GDP的比重)與國際經濟流通限制(包括隱性進口壁壘、平均關稅率、國際貿易征稅水平以及資本賬戶限制)的加權平均數。(44)Axel Dreher, “Does Globalization Affect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Index of Globalization”, Applied Economics, Vol.38, No.10, 2006, pp.1091-1110.
此外,本文設置了16個控制變量。它們都是國家建設經驗研究中經常使用的變量。(45)盧凌宇:“戰爭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建設”,《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10期,第23-25頁。這些變量包括三種類型,即:一是政治因素:國內沖突(虛擬變量)、國際沖突(虛擬變量)、政治體制(Polity2值)、族群政治(族群分裂指數)、聯邦制(連續變量)、國家年齡、國家年齡平方、國家領導人任期剩余年數、有限任期制(虛擬變量);二是經濟變量:人均GDP、人均GDP平方、農產品占GDP比重、礦產品占GDP比重、以及GDP增長率;三是金融變量:債務率(債務占GDP比重)、通貨膨脹率(%)。(46)Liesbet Hooghe et al., A Postfunctionalist Theory of Governance, Measuring Regional Author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536.
本文的模型設定有兩個特點:一是將中國模型與全球模型區分開來。經驗檢驗的重點是中國模型,全球模型的作用在于比較全球化在中國的作用與在中國以外的地區有什么區別。二是在全球模型中,區分全球樣本、發展中國家樣本和發達國家樣本三種模型,以便于進一步發現中國經驗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排除缺省的數據,中國樣本只有30~40個觀察數,同時鑒于樣本是單一國家時間序列數據,因變量取值受限,最小值為0.043,最大值為0.214,所以本文回避了常規的時間序列回歸,而采取Tobit回歸。(47)Cheng Hsiao, Analysis of Panel Data,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 Press, 2003, pp.225-234.其他模型則采用常見的處理辦法,把自變量都作滯后一年的處理,唯一的例外是“族群分裂指數”,它在橫截面(一國內)是恒量,所以滯后處理在統計上沒有意義。此外,在中國模型中,我們設置了“1978年”這個虛擬變量,即年份大于或等于1978年為1,小于1978年為0。197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元年,是創造經濟奇跡的起點。改革開放意味著鼓勵外來投資,經濟上與國際接軌,國內民營經濟開始發展和繁榮,國有企業開始大量地退出。實際上,國有企業是國家最穩定的稅源,但由于其半行政性質,征稅難度低,成本小,反而不利于國家能力提升。相比之下,對非國有企業及其員工實施財政監控難度較大,成本較高,這對以稅收為軸心的官僚機構既是挑戰,也是規模擴張和效率提高的激勵。這個變量的具體影響主要取決于從國有企業一統天下到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共存為財稅等部門所產生的成本和收益的對比。
此外,中國以外的數據構成了面板數據(panel data)。對面板數據模型通常采用隨機效應(random effect,簡稱RE)模型、固定效應(fixed effect,簡稱FE)模型或混合數據普通最小二乘法(pooled OLS)。兩者的基本區別在于:隨機效應或固定效應分析所用的數據是對相同的單元(國家)在不同的時間點(年)抽樣的結果,而混合數據普通最小二乘法的數據結構則是不同時間點上的抽樣單元(國家)都是不一樣的。鑒于此,我們采取前一種分析方法。具體而言,我們先對每一個模型進行固定效應分析,然后再運行隨機效應回歸,最后進行豪斯曼測試(Hausman’s test),如果測試結果小于0.05,測試結果就否定元假設:未觀察因素與解釋變量是正交關系,需要使用固定效應模型。我們在表2、表3中對要使用固定效應的模型做了標注。使用固定效應的一個結果是把“族群分裂指數”這個不隨時間變化的變量排除在外。
三、發現與分析
經驗分析使用的數據全樣本包括185個國家,時間起點最早是1970年,最近為2017年,觀察數為6 792個。由于不同來源的數據時空覆蓋的范圍有區別,小樣本回歸分析用了中國1970—2013年的44個觀察數;時間序列回歸模型所覆蓋的國家為184個,時間為1970—2013年,觀察數為648個。表1報告了小樣本分析的回歸結果,包含六個模型。表1只用了中國的數據,有四個自變量的設置,其中1978年是虛擬變量(1,0),用于控制改革開放對中國國家能力的影響。由于主要發現都在表1,所以會重點解讀。總的來看,統計證據基本支持或部分支持了假設一、三、四,但證偽了假設二(見表1)。

表1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國家能力的影響(1970—2013年)
注:系數下方“-”后的數字為標準差;*** p<0.01, ** p<0.05, * p<0.1
根據表1的模型7,經濟全球化指數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中國的財政汲取能力增加0.4%,這個影響的力度相當大。具體到全球化的分類指標,貿易全球化每增加一個百分點,中國的稅收就會增加0.3%;金融開放的作用獲得了統計上的顯著性,每增加1%,汲取能力上升0.45%。盡管如此,金融開放的影響范圍卻很有限,因為樣本內該變量的取值在0到0.1658088之間,而在全球樣本中,該變量的取值是0到1,這表明中國謹慎開放金融的國家建設效果是顯著而積極的,而且很可能是妥善的;而在中國以外的發展中世界,樣本內金融開放度的區間也是0到1,但它對這些國家的國家能力的作用卻是顯著負面的。不過,外來投資對中國國家能力的影響卻是顯著消極,不過絕對作用較小:投資每上升1%,汲取水平下降約-0.1%。
對比表1的模型5和模型1、2、3,我們發現當同時將全球化的三個分類指標納入方程,投資全球化的作用雖然沒有喪失顯著性,但改變了方向。1978年這個虛擬變量在模型2和模型7中都統計上顯著,并且為負數。這條證據是合理的,在改革開放之前,國家幾乎控制了一切經濟活動,所以以汲取水平來度量的國家能力非常強大。
表2和表3報告了小樣本分析和時間序列分析的回歸結果。表2和表3都包含六個模型,使用的數據是不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其他國家的數據。表2所有的模型都使用了時間序列分析,但在變量數設置上都與表1相同,即有四個自變量。表2的模型1、模型4是使用了除中國外所有國家的數據;模型2、模型5是使用了除中國之外發展中國家的數據,這里劃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因為是從1978年才產生的指標,所以回歸的數據是從1978年起算的;模型3、模型6則使用發達國家的數據(見表2)。

表2 經濟全球化對國家能力的影響(1970—2013年,全樣本,選擇性變量)
注:系數下方“-”后的數字為標準差;*** p<0.01, ** p<0.05, * p<0.1
表2諸模型與表1的模型5和模型6是直接的比對。兩者共同的發現在于:經濟全球化本身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中國以外的全世界以及發展中國家或者發達國家,都起到了顯著的積極的國家建設功能,其中表1模型6“經濟全球化”這個指標的系數是0.00403,表2模型4、5、6同一指標的系數分別為0.000235、0.000 195 和0.000 511。盡管如此,經濟全球化的三個分解指標并沒有呈現出同樣的規律。在表1中國案例中,貿易和金融全球化顯著地強化了國家能力(系數分別為0.361、0.212),但投資全球化的效應(系數為-0.000 936)則是顯著降低,雖然系數很小。相比之下,在表2中,貿易全球化對中國以外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同樣顯著且積極(系數:0.016 1),金融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則與對發達國家的作用同樣顯著且積極(系數:0.020 9)。從中國以外的全球樣本來看,貿易、金融的影響都不顯著,但投資的作用則是顯著積極的(系數:0.000 126)。不僅如此,發達國家能力由于貿易而顯著受損(-0.042 2),這與中國從貿易中受益恰成反比(系數:0.361)。
表3的六個模型都是全變量的完整時間序列分析,數據規模與表2相同,除了四個與表1、表2都一致的自變量之外還添加了十六個控制變量,是包括了所有變量的完整模型。與表2類似,表3的模型1和模型4使用了除中國以外的所有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模型2和模型5根據除中國外的發展中國家數據做的分析;模型3和模型6則是使用了發達國家的數據。

表3 經濟全球化對國家能力的影響(1970—2013年,全樣本,全變量)

續表
注:系數下方“-”后的數字為標準差;*** p<0.01, ** p<0.05, * p<0.1
表3中六個模型納入了國家建構文獻中的常見變量,是比表2諸模型更可靠的回歸結果。將它們與表1中的模型5、6相比,我們發現,從全球范圍來看,經濟全球化總體上顯著地促進了所有國家國家能力的提高(系數:0.000 317),這個效應對于發達國家同樣適用(系數:0.001 49),但對中國以外發展中國家的作用并不顯著。就三個分解指標而言,中國的所受的影響與全球樣本均不相同,因為貿易、投資和金融全球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分別不顯著、顯著且積極(系數:0.000 136)、顯著且消極(系數:-0.009 46)。與此同時,中國和發展中國家都從對外貿易中受益(后者系數:0.009 98),中國與發達國家都從金融開放中受益(后者系數:0.036 5)。盡管如此,中國未能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從外來投資中顯著受益(后者系數:0.000 235)或者可以說在金融開放中國家能力受損(后者系數:-0.018 6)。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投資和金融的影響都是不顯著的(系數分別為 0.000 103、0.036 5)。
四、結 論
本文探討了經濟全球化的三個維度——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以及經濟全球化總體對中國國家能力的影響。我們基于對1970—2013年間宏觀數據的統計分析發現,經濟全球化總體上顯著地增強中國國家能力。具體而言,貿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顯著地增加中國的國家能力,但投資全球化顯著地降低了中國的財政汲取水平。本文的發現表明,我國應該大力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實現與國際經濟的接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1月17日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所指出的那樣,我國要在國內進行產業升級,對外尋找合適的貿易伙伴,完善法律法規以及國際共識來解決貿易摩擦;在引入外資以促進國內生產的基礎上,加強對外資企業的管理與監督,完善國內法律法規,在風險和收益之間尋找金融開放的平衡點,逐步進行金融全球化。(48)門洪華、王驍 :“中國國際地位動態研究(2008—2018)”,《太平洋學報》,2019年第7期,第90-92頁。本文的發現也印證了伊萬斯(Peter Evans)在1997年提出的“反潮流”的觀點:貿易并不會削弱國家能力,而是為擴張國家功能和機器提供了機會。全球化確實讓國家在某些方面變得脆弱和敏感,但國家也會積極地應對挑戰,并不會因為融入全球化而導致自身空心化。(49)Peter Evans, “The Eclipse of the State? Reflections on Statenes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Vol.50, Issue 1, 1997, pp.62-87.
本文的經驗發現證偽了投資全球化顯著增強中國國家能力這個假設。出現這個結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國對FDI的監管效率較低,沒有達到期待的效果。在2019年3月中國通過《外商投資法》之前,外資管理的法律一直由《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外資企業法》三部法律承擔。它們不僅規定繁瑣,而且在功能上存在大量重合。《外商投資法》則進一步降低外商投資限制,強調建立穩定、透明、公平和可預期的市場環境,加強保護外國投資者和外商投資企業在境內的合法權益。但從法律實施到產生期待的效果,有一個時滯,對中國國家能力的影響也會相應地呈現滯后效應。
中國的經驗表明,對于欠發達國家而言,全球化既是發揮比較優勢、實現經濟騰飛的重要歷史機遇,又能幫助政府提高官僚機構工作效能、加強國家能力建設。然而,全球化并不總是高歌猛進,而是有漲有落。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以“占領華爾街”、歐洲難民危機、英國脫歐、美國對中國挑起的貿易爭端等事件為標志,“逆全球化”強勢興起。逆全球化出現的根本原因是這一輪全球化所造成的社會分配不公和國家間發展不平衡,是全球化“輸家”對“贏家”的挑戰。(50)陳偉光、蔡偉宏 :“逆全球化現象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基于‘雙向運動’的理論視角”,《國際觀察》,2017年第3期,第6頁;周琪、付隨鑫 :“美國的反全球化及其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4期,第1-13頁。全球化是“自由(liberal)國際秩序”的經濟維度。面對全球化的逆轉,中國的應有立場一方面是繼續深入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堅持多邊主義,推動全球化朝著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應努力“構建平等協商、共同參與、普遍受益的區域合作框架,堅定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51)“習近平談全球化”,《人民日報(海外版)》,2017年1月15日; “習近平:全球化大潮不可擋,融合大趨勢未變”,央視網,2019年6月27日,http://news.cctv.com/2019/06/27/ARTIfDd3evXiO6 BcN4r2Bcqd190627.shtml?spm=C96370.PsikHJQ1ICOX.EKuioXvJBBSD.1。既然如此,相對于全球化,區域化和集團化如何作用于中國國家能力?反過來說,中國強大的國家能力對于維持全球化和促進區域化/集體化又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此外,本文重點考察了貿易全球化、投資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實際上,貿易既包括進口和出口,又有不同的構成(比如原材料和制成品);投資則既有對外投資,又有外來投資;程度更高的金融開放意味著允許外資進入并控制我國的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貨公司,開放資本賬戶。那么,不同形式和水平的經濟全球化會怎樣作用于中國國家能力?這些都是具有重大理論和政策意義的后續研究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