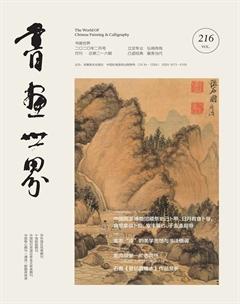論中國書法骨肉筋力的審美構成
郭大興 郭麗偉

關鍵詞:書法審美;骨肉筋力;審美建構;自然審美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書法審美創造異常活躍的一個時期。隨著這一時期的書家對各書體審美創造思想的不斷建立和完善,理論家對這一美學思想的總結也充分彰顯出這一演化特征。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對魏晉書風審美風格的形成,產生了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從漢末到魏晉南北朝,社會的動蕩和朝野的紛爭,深刻影響了文人士大夫對現實生活的復雜情緒。他們面對朝政的頻繁更替和無休止的戰亂,在無奈和惶恐中如履薄冰,產生了朝不保夕、命不終朝的憂慮和擔心。因此,他們逐步對傳統儒家思想產生了懷疑。而好黃老、尚自然,成為文人、士大夫及上層社會的一種主要潮流和風尚。正如當今學者葉朗所說:“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魏晉南北朝的美學發展,是對于孔子美學的否定,是一個回到老、莊美學的活動。”[1]
一、“骨肉筋力”審美的歷史淵源
“骨肉筋力”的審美淵源,首先在于“自然”的審美旨趣。老子曰“道法自然”,這一古老的哲學命題,確定了中國美學是以“自然”為審美旨趣的哲學體系。“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道德經·第四十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這種“有無相生”命題的提出,體現了“道”“生生不息”的規律,以及萬物都存在“負陰抱陽”的生命之“氣”的論斷,都說明了“道”的生命價值是永存的。而這種生命價值還表現在萬物的“形”“勢”上。老子認為:“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道德經·第五十一章》)其意明確用萬物的形態審美表現特征來說明“道”的普遍審美規律,并一再用對人的審美觀照方法去闡釋“骨肉筋力”的外在表現,“骨弱筋柔而握固”,“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道德經·第五十五章》)。因此說,老子所確立的萬物“道法自然”的命題,既包含萬物的普遍發展規律,又存在對萬物生命形態表象的審美認知。老子把這種生命感的審美認知建立在萬物的形態視覺表現上,開啟了中國古代對天地萬物的審美先驗、先覺之門。
莊子在老子“道法自然”的命題基礎上同樣認為“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莊子·天地篇》),“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萬物以形相生”(《莊子·知北游》)。萬物都是通過天地道化而成,萬物這種生生不息的道化,既表現了天地自然無為的審美品德,也表明了“道”的生命永恒精神。莊子還進一步強調:“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莊子·達生》)莊子把對“道”的觀照進一步建立在萬物的“形”“貌”“聲”“色”之上,為后期魏晉南北朝哲學家、藝術家對“自然”審美生命的審美觀照奠定了美學基礎。這種審美觀照方式,也自覺成為魏晉南北朝書法藝術審美風格的重要趣旨。
可以說,魏晉書法骨、肉、筋、力的審美建構,首先取決于漢初統治者對黃老道家哲學思想治國的熱情依賴,以及漢末道家思想的復燃和“清議”之風的盛行,這些都能體現出兩漢思想家、藝術家的美學趣味。漢初《淮南子》所表現出的“質近老子”,東漢《論衡》關于“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意”[2]的闡發,都體現了漢人對“骨肉筋力”的美學觀點。《淮南子·原道訓》曰“夫道者,覆天載地”[3],認為“道”無所不有,無所不包。這體現了《淮南子》對“道”的自然規律和本原的認識,并直接把黃老之“道”對應到自然萬物的形勢審美觀照上來。這種對應的比喻方式,既包括萬物的自然形態又包含萬物的生命審美價值。劉安還認為:“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淮南子·原道訓》)萬物動靜形態和生命特征的動態表現,都是“得道之柄”,認為它們都體現了“道”的法門和規律。尤其是東漢王充在《論衡》中將人體形態、筋骨、氣血與他的“天命論”密切聯系在一起,成為直接誘發漢代書法技藝審美與自然生命息息相關的主要成因。王充認為“形、氣、性,天也”,“人稟氣于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4]。這闡明了人的命格與形體、氣血之間的自然審美聯系。他又言:“人命稟于天,則有表候于體。察表候以知天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5]“表候”就是“骨法”的體現。在王充看來,對人體“表候”的觀照,不只是對“骨力”的一種表象,還當觀照其“筋力”和“氣勢”。他說:“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6]他認為人的“筋力”和“氣勢”都有與天命對應的巧妙之處,并把這一觀點進一步擴展到更為寬泛的層面。王充認為:“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7]在這里,人的知識學問皆成為“力”的表現方式,這就為東漢書法審美開辟了視野。
趙壹《非草書》首先從“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8]的宿命論角度,批評了時人迷戀習學草書的現狀,認為書家是因“氣血”“筋骨”與平常人的差異才取得了不同的書法成就。這里的“氣血”“筋骨”,只是生命構成的術語,還未延伸、發展成為書法的審美概念。但他把這種生命構成術語轉變成了與書法風格有關的因素。而東漢文學家、書法家蔡邕對“力”的關注則直接指向書法審美,成為一種新的書法藝術概念和命題。蔡邕言:“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護尾,畫點勢盡,力收之。”[9]“力”的作用被蔡邕最早引入了書法的審美創造中來,不得不說這是中國書法藝術發展的一大進步。這同時還體現了書法“自然形勢”“陰陽交合”的哲學審美的樹立。東漢書法藝術家這種審美創造思想的形成,絕不是偶然的、憑空想象的,而是有賴于當時“好黃老”“重道法”的文人士大夫審美思想向藝術方面的重大轉移。宋代楊文昌在為《論衡》刻本作《后序》時言:“蔡邕入吳會(稽),始得之,常秘玩以為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耳共之,勿廣也。其后王郎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10]可見,《論衡》一書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作為東漢文學家、書法家的蔡邕也深得其益。而蔡邕關于書法“筆力”的審美見解率先揭開了中國古代書法力度審美的面紗,為東晉書法“骨肉筋力”的審美構成打下了美學基礎。近代學者張宗祥根據蔡邕藏書之說,稱其書為“帳中異書,漢儒之所爭睹”[11]。雖然趙壹、蔡邕率先從不同角度把人體骨感、筋力引入書法審美創造并確立起來,但《論衡》的作用不可小覷。而真正把人體筋骨表象同宿命對應起來的書籍,還應推三國魏時劉邵的玄學著作《人物志》。《人物志》為三國魏時的“刑(形)名”之作。它反映了當時“察舉選士”的人物審美品鑒現狀。文中廣泛論述了“形、容而尚骨”這個命題。現代學者湯用彤認為這和《論衡》的“表候論”具有一致性。識鑒人倫,相其外而知其中,察其章以推其意。[12]根據《隋志》記載,漢末至東晉所錄“刑(形)名家”之書已經形成其學術范式。例如魏文帝的《士操》、劉邵的《人物志》、姚信的《士緯新書》、魯毓的《九州人士論》、佚名的《刑聲論》《通古人論》等,它們的內容都包含了對人物“形名”的觀照。可見,魏晉朝廷以“形”為察、以“名”為治的取士方式,成為魏晉玄學人物品鑒之風盛行的根源。從此,文人士大夫以“形名”競盛。漢末“清議”、魏晉“清談”成為當時文人士大夫進退保身的權宜之策,為“魏晉玄談”的旨趣性轉變創造了過渡性條件。一時間,魏晉研究《老子》《莊子》《周易》的“玄學”之風四起,使得人物品鑒成為一種風尚。“何晏之徒,始盛玄論。于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13]何晏著《老子道德論》、嵇康著《聲無哀樂論》、阮籍著《達莊論》、鄭玄注《周易》、王弼釋《周易》、宋岱著《周易論》、郭象注《莊子》等,大量名士談玄論道、著書立說。著述內容都不乏對人體骨肉、筋力、精神等命題范疇、概念的闡釋。
二、魏晉書法“骨肉筋力”審美的確立
隨著魏晉對人體“宿命論”的重視,人物審美品鑒興趣也逐步擴大。受其影響,文人士大夫對書畫藝術風格的審美趣味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他們把對人物筋骨、體態的審美及力度觀照,逐步運用到書畫的審美觀照中來。如東晉顧愷之在《魏晉勝畫流贊》中對人物繪畫明確要求“骨法”。認為畫伏羲、神農要有“奇骨”,畫季王要有“天骨”,畫孫武要有“骨趣”,畫醉客要有“形骨”,等等。更有甚者,南朝謝赫把“骨法用筆”作為繪畫的“六法”之一加以強調,增強了“骨法”在繪畫中的學術地位。而魏晉南北朝對書法“骨肉筋力”的審美要求更為具體、獨到和強烈。這種認識對應“骨肉筋力”人體審美特征的方式,被完全運用到書法用筆的審美表達中來。這種審美觀照方式,首先表現在東晉書法家衛鑠的《筆陣圖》書論中。衛鑠是西晉大書法家衛恒之女,自幼受書法熏陶,世稱“衛夫人”,為王羲之的啟蒙老師,在東晉書法發展史上有著卓越的貢獻。她在《筆陣圖》中也特別強調筆力,認為筆力是書法審美的一種重要表現。而筆力的表現因素,在于筆墨“骨”“肉”“筋”的表達。她說:“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筋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圣,無力無筋者病。”[14]按衛鑠的看法,書法用筆首先要表現筆畫的力度,而“力”的表現又在于“多骨”“豐筋”。衛鑠反對“多肉”,但并不全然排斥“肉”,只有在“骨”“筋”的強烈表現下,“微肉”才是最好的審美表現形態。如果“肉”多,就會掩蓋和損害“骨”“筋”和力的審美感,就會成為“墨豬”,造成“無力”的弊端。衛鑠對書法“力”的創造要求,賦予了中國書法以深刻的審美內涵,揭開了中國書法“骨肉筋力”筆法審美創作的序幕。由此,中國書法“骨肉筋力”的審美創造成為一種標準被確立起來。
東晉王羲之在衛鑠審美思想影響下,同樣把書法的審美創造直接建立在“骨”“肉”“筋”“力”的美學基礎上,促進了這一書法美學概念、命題、范疇的建構和鞏固。王羲之一再強調書法要“藏骨抱筋,含文包質”[15],“欲書,先構筋力,然后裝束”,“存筋藏鋒,滅跡隱端”[16],“筋脈相連,意在筆前”[17],“如是則筋骨不等,生死相混”[18],等等。王羲之認為,書法用筆必須具有鮮明的“骨力”和“筋力”。“骨”,代表了堅強和穩固,它透露的是一種陽剛之氣的力量美。“筋”,表現的是纏綿和映帶,它突出的是筆畫的陰柔之美。在王羲之看來,無論“骨”還是“筋”,都不能外露,而應“藏抱”于筆畫之中。如果說“骨”主要是筆所確立的主題,那么“筋”就是“意”的傳載。這就顯示出王羲之從技法層面對用筆的具體要求。進一步看,正是東晉注重對書法藝術生命體態的“骨、肉、筋、力”的表達,才成就了東晉書法 “流美”“今妍”的時代書風。沒有“力在其中”的審美表達,就沒有書法筋脈相連的藝術創造和審美建構。
三、魏晉書法“骨肉筋力”審美確立的影響
隨著魏晉書法“骨肉筋力”審美確立與建構的形成,南北朝書法家對“骨肉筋力”的審美觀照陸續展開。蕭衍曰:“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并皆然。……肥瘦相和,骨力相稱。”[19]這里,蕭衍既反對一味注重“純骨”用筆,也反對一味過多或過少地用墨。他將用筆技法與審美趣味聯系起來,認為書法需要“媚”與“澀”的裝點,但筆墨要合度,以提升到“和”的審美高度,只有這樣才能達到“相和”的美學境界。蕭衍把衛鑠和王羲之的思想往前推進了一步。如他評陶隱居書法“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評蔡邕書法“骨氣洞達”,評王僧虔書法“奕奕皆有一種風流氣骨”[20],等等。王僧虔的《書論》《筆意贊》,對張芝、衛恒、索靖、韋誕、鐘會、衛鑠、王子敬、郗超、蕭思話等書法的品評,同樣是從骨、肉、筋、力的審美形態上進行的。這表明,從筆的“骨肉筋力”進行書法風格的確立,成為書法藝術研究的一個焦點。這既表明魏晉南北朝書法風格的研究進一步得到深化,又意味著這種風格表達正在向審美自由境界提升。因此說漢代書畫已經從感性層面飛躍到理論審美自覺的層面。
東晉書法“骨肉筋力”審美風格的形成和確立,對后世書法影響深遠。由于唐代對東漢及“二王”書法風格的推崇,書法“骨肉筋力”的審美創造風格逐漸成為書畫界的一組美學概念、命題、范疇和美學標準。如李世民、荊浩、蘇東坡、米芾、豐坊、項穆、宋曹等,他們都有關于書畫“骨肉筋力”的審美論述。李世民認為:“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和,則字無態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21]他還說:“太緩者滯而無筋,太急者病而無骨,橫毫側管則鈍慢而肉多,豎筆直鋒則干枯而露骨。”[22]唐代畫家荊浩同樣認識到了“骨肉筋力”用筆的重要性:“凡筆有四勢,謂筋、肉、骨、氣。筆絕而不斷,謂之筋。起伏成實,謂之肉。生死剛正,謂之骨。跡畫不敗,謂之氣。”[23]在荊浩看來,前人所重視的“筆勢”,就是書法骨、肉、筋、力的生命審美表現。蘇東坡重申:“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缺一不可成書也。”[24]米芾強調:“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25]陳思也說:“多力豐筋者圣,無力無筋者病。”[26]豐坊說:“書有筋骨血肉。筋生于腕,腕能懸則筋骨相連而有勢;骨生于指,指能實則骨體堅定而不弱。血生于水,肉生于墨,水須新汲,墨須新磨,則燥濕調勻而肥瘦得所。”[27]項穆評唐人書法曰:“唐賢求之筋力軌度,……宋賢求之意氣精神……元賢求性情體態。”[28]“猶世之論相者,不肥不瘦,不長不短,為端美也”,“瘦不露骨,肥不露肉,乃為尚也”[29]。宋曹說:“每作草,行首之字,往往續前行之末,使血脈貫通,……衛瓘得伯英之筋,索靖得伯英之骨,……顛喜肥,素喜瘦,瘦勁易,肥勁難,務使肥瘦得宜、骨肉相間。”[30]如此等等。歷代書法藝術家在觀照書法各體的審美創造時,形成了對筆畫“骨肉筋力”的審美品鑒方式,并把這一審美方式作為統一的創作標準來看待,直至今天,書畫家同樣把用筆的“骨肉筋力”作為藝術創造的審美品評標準。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及后期書畫藝術家,對“骨肉筋力”概念的認知和審美建構,突破了東漢書法家的理論認識視野,回到了筆墨經驗的藝術審美創造上來。筆的緩急、欹側、抑揚、頓挫、提按、使轉和墨的干枯、濃淡,都與書法審美內含的骨、肉、筋、力密切相關。魏晉南北朝書法“骨肉筋力”的審美建構,形成了中國古代書法藝術風格的基本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