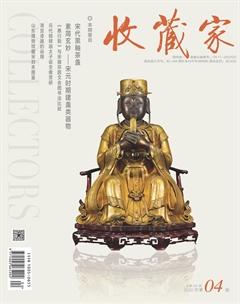唐王公淑墓志考釋
魯曉帆


1992年9月在北京市海淀區八里莊地區的玲瓏公園西墻外,發現了一座四周帶有壁畫的唐代墓葬。可惜的是墓葬早期已被盜掘,隨葬器物早已不知所終。幸運的是在塌陷的墓室四周,遺留下了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精美壁畫,尤其是北壁上牡丹蘆雁圖壁畫,被認為是我國北方現存唐墓壁畫中最為重要的發現。它是以大幅的牡丹花為中心,并在左右兩側配有兩只栩栩如生、相互呼應的鸕鶿烏,以及花草中兩只靈動的蝴蝶所組成的生動畫面。而根據墓中僅存的題有“唐故幽州節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盧龍節度留后、營府都督、柳城軍使,平州諸軍事、平媯等州刺史、上柱國太原王府君墓銘并序”的墓志銘及志文中記載的內容,可知此墓是唐代王公淑及其夫人吳氏的合葬墓。該墓葬給人留下的突出特點就是墓葬中以花烏題材及居家生活為主的精美壁畫,以及磚雕仿木構門,這些充分體現出唐末幽州地區高超的建筑藝術與繪畫水準,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科學研究價值。而近年來研究此墓壁畫的學者不乏其人,但是對此志文內涵的研究卻顯得相對淺顯,至今還沒有人對志文內容進行完整深入地考證。筆者認為此志文對研究唐代幽州城的歷史,還是有一定價值的。同時,它對豐富北京地區唐代地方史料,也是一件不可多得實物資料。
王公淑墓志銘,唐大中六年( 852)上石。青石質地,高、廣均為62厘米。志文正書,全文共計28行,滿行35字。寇倫撰。蓋為盝頂,高、廣均為62厘米。正中陰刻篆書“王公墓銘”4字,2行、行2字。四坡陰刻有十二文臣立像,四交角陰刻有牡丹花紋飾。此志書法用筆質樸卓茂,結體寬舒。雖屬于晚唐作品,但又與常見的唐墓志有所不同,即帶有濃郁的北碑意味,這可能是源于刀刻的緣故。志文拓片見載于《新中國出土墓志·北京卷》等多部書籍,墓志現收藏于北京市海淀區博物館。為便于讀者對照考證,現將原志文抄錄如下(另加標點)并加以考釋。
(蓋文)
王公墓銘
(志文)
大唐故幽州節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盧龍節度留后、營府都督、柳城軍使、平州諸軍事、平媯等州刺史、上柱國太原王府君墓銘并序 儒林郎、試率更寺丞、攝幽府功曹參軍寇倫撰。
府君諱公淑,字均,太原人也。其先周靈王之子,得道升天。后裔以貫三才而為王,遂千古以作氏。四十代之余慶,八百年之洪休,垂裕奕葉,固其宜矣。曾祖亮,皇幽州節度衙前虞侯。祖連,皇盧龍節度要籍。列考戩,敦詩閱禮,果行鬻德,饜聞羔雁之征,不改箕穎之操。府君即征君之元子也。懸弧之時,弄璋之儀,足慰九族之心,已駭四海之目。五歲從師受業,百家罔不漁獵。鄉人數薦,觀光京輦。元戎累辟,解褐幽州節度要籍。立談邊務,坐見塵清。持署盧龍節度巡官,紫塞繇是又安。智略涌于灸輠,安危恃其參佐。政令合宜,庶績允暢。遷幽州節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蘊魏絳和戎之美,恢田疇開塞之功,揚名閫外,就列殿中。恩光寵賜,榮曜金紫。授盧龍節度留后、營府都督、柳城軍使、平州諸軍事、平州刺史。扇和風以糜草,冒靈雨以赴期。虎聞渡河,不假飛將之射;民和讓畔,甚于西伯之時。樂輸井稅,轉牧媯汭。入境露冕,下車求瘼。奸邪屏跡,疲田亡息肩。鄰有凋弊,藉以撫綏。更充防御軍使,古人辭大不辭小之義也。趣裝蒞之,政理仁慈,邊俗樂業,邦家遽肥。遵老氏之止足,同泉明以揭來。祁奚請老,菜子寧親。返駕角巾,色養不遺。神味福善,天胡奪魄。春秋六十九,大中二年十月十四日,兌易簀歸全于薊門私第。六年二月十七日,祔葬于先吳氏夫人之真宅,候通年也。夫人吳氏,濮陽人。太伯封吳,子孫著姓。皇節度驅使官之女。年纔十七。廟見榛栗。孝乎舅姑,工于織紅,閨門肅穆,中外克諧。嗚戲!命矣!不享遐齡,五十有一,屬纊牖下,開成二年九月廿五日。幽邃華堂,俄成兇室。來年三月十三日,窆于幽州幽都縣西北界樊里之原,禮也。子八人,女三人。長日弘裕,幽州昌平縣丞。次日弘爽、弘慶、弘道、弘安、弘信、弘順、弘德,俱稟義方,深閑輯理。婚偕茂族,歸盡名家。即丁憫兇,幾至滅性。哀榮薤露,稱家送終。抑呼天殞絕之聲,假玄壤乃遷之志。銘日:
薊北迥野,原上孤墳。朱輪走日,皂蓋凝云。夫人茂族,玉潔藍熏。神游冥寞,風散氤氳。劍沉淥水,為龍不分。雁隨丹旒,棲隴離群。祔遵周禮,哀慟吾君。積德素行,載揚斯文。
志云:王公淑“太原人也。其先周靈王之子,得道升天。后裔以貫三才而為王,遂千古以作氏。四十代之余慶,八百年之洪休,垂裕奕葉,固其宜矣。”在《元和姓纂》載: “王姓,出太原,瑯琊、周靈王太子晉之后(即王子喬)。”志與史載相同。在這里“貫”即是指貫穿。而“三才”即是指天、地、人。據《周易·系辭下》載: “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而在中國的傳統啟蒙教材《三字經》中載:“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而這里“余慶”就是謂先代為后代所遺留下來的福澤。在《周易·坤·文言》載:“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這“洪休”即指洪福。“垂裕”是謂為后人留下業績。而“奕葉”即謂累世。在東漢蔡邕《瑯邪王傅蔡郎碑》中載: “奕葉載德,常歷宮尹,以建于茲。”而《隋書·禮儀志七》載:“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奕葉共遵,理無可革。”志文在這里是說王公淑的籍貫是為唐河東道的太原,而他的祖先是周靈王太子喬的后人。而王姓的后裔能一代代延續,就是被貫穿于天地人之間的神靈來保佑的。所以流傳千古的氏族延續,就是用王姓來擔當的。這是四十代流傳下來的福澤,是八百余年修來的洪福。而歷朝歷代留傳下來的豐功偉績,王姓是承繼與鞏固這些的最佳選擇。
墓志首題王公淑的衙銜“幽州節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檢校太子賓客、盧龍節度留后、營府都督、柳城軍使、平州諸軍事、平媯等州刺史、上柱國。”從這些先后任職的衙銜來看,王公淑一生的官職較多,但可分為:勛官“上柱國”,正二品。文散官“銀青光祿大夫”,從三品。職事官“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上。 “檢校太子賓客”,正三品。檢校實為加官。而“盧龍節度留后”是節度使府下設的官員,即相當于節度副使,未見品級。這“營府都督”則是“營州都督府都督”簡稱,為從三品。而這“柳城軍使”,在《新唐書·地理志三》載:河北道“平州北平郡,下。縣三。有府一,日盧龍。有盧龍軍,天寶二年載置,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可見,唐“柳城軍”是設置在盧龍地區的營州與平州一帶,其治所就在今河北省昌黎縣西南的靖安鄉,其主要職責就是防范奚、契丹族南下侵擾的。墓志與史記載相同。而“平州諸軍事”及“平媯等州刺史”,即唐河北道設有的“媯州媯川郡”是為上州,刺史為從三品。 “平州北平郡”是為下州,刺史為正四品下。而按照唐制:刺史加“使持節”“諸軍事”的則為將官。即王公淑既是當地的父母官,又是當地的最高軍事首長。這里“幽州節度判官”,在《新唐書·百官志四下》載:外官“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事、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在2001年4期《文物春秋》登載的馮金忠《從王公淑墓志看唐代盧龍鎮》 一文,詳細闡述了幽州節度使與盧龍節度使之關系,即盧龍節度僚佐不僅受命于盧龍留后,還受控于幽州節度使。幽州節度使擁有對盧龍鎮官員絕對的調配權。可見,王公淑一生都是為歷任幽州盧龍節度使盡職盡責服務的,從而先后獲得這些官職。
墓志中詳記王公淑的上三代。曾祖父王亮,其衙職“皇幽州節度衙前虞侯”。這里“虞侯”原來是掌水澤出產之官。在隋時為東宮禁衛官,掌偵察、巡邏等職責。而在唐代的后期,藩鎮節度使以親信武官為“都虞侯”“虞侯”“衙前虞侯”等等,是作為軍中各級的督察執法的長官,他們的權力很大,必要時可以直接執掌軍使等官職。祖父王連,其衙職“皇盧龍節度要籍”。在《新唐書·職官志四下》載:節度使屬下有“府院法直官、要籍、逐要親事各一人”。可知,王公淑的父親是為盧龍節度使府的僚屬,即管理卷宗記錄治理文件的官員。而作為隱士的父親王戩“敦詩閱禮,果行鬻德,饜聞羔雁之徵,不改穎之操”。這里“饜聞”即是成語“厭聞飫聽”的縮寫,指充分聽取。這里“鬻德”即指言施德澤。在《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載有:“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而這“羔雁”是指小羊和雁。這在古代是被用作卿、大夫的贄禮。《周禮·春官·大宗伯》載:“卿執羔,大夫執雁。”鄭玄注: “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東漢班固《白虎通·文質》中載: “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志文在這里是說王公淑的曾祖父王亮曾是幽州節度使府負責軍中執法的官員,祖父王連曾是盧龍節度使府負責文件歸檔管理的官員。而父親王戩則是一個知書達禮、溫柔敦厚、行為果斷、道德高尚、拒絕官府征聘、不改讀書人品行的隱士。
志云: “府君即徵君之元子也。懸弧之時,弄璋之儀,足慰九族之心,已駭四海之目。五歲從師受業,百家罔不漁獵。鄉人數薦,觀光京輦。”這里“徵君”即是對徵土的尊稱。在《后漢書·黃憲傳》載: “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日徵君。”晉代皇甫謐《高土傳·韓康》載: “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這里“懸弧”即生男孩。古代風俗尚武,家中生男,則于門左掛弓一張,后就稱生男為懸弧。在《禮記·內則》載: “子生,男子設弧于門左,女子設巾兌于門右。”漢代的賈誼《新書·胎教》載: “太子生而泣……然后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而“弄璋”也是指生男孩。在《詩·小雅·斯干》載: “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這里“足慰”謂足夠可以慰籍。而“九族”泛指其親屬。在《三字經》中對九族的解釋是“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孫。自子孫,至玄曾。乃九族,人之倫。”即為高祖、曾祖、祖父、父親、己身、子、孫、曾孫、玄孫。而“四海”是指全國各地。“百家”即許多的家族。 “漁獵”謂之泛覽,涉獵。在<隋書·文學傳·潘徽》載: “遨游必名教,漁獵唯圖史。”而在《云笈七簽》卷五六載: “漁獵百家,披尋萬古。”而這“京輦”即是指國都。晉代葛洪《抱樸子·譏惑》載: “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志文在這里是說王公淑是隱士王征的長子,王家幾代人都曾為幽州盧龍節度使府服務。而在婚配生子上,王公淑的降生足以告慰家族的期盼,并震驚了左鄰右舍。王公淑在5歲時就跟隨老師識文斷字,廣泛地閱讀了大量史籍。在他成長過程中,曾在家鄉眾人的建議下,去到京城游歷,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
志云:“元戎累辟,解褐幽州節度要籍。立談邊務,坐見塵清。持署盧龍節度巡官,紫塞繇是又安。智略涌于灸輠,安危恃其參佐。政令合宜,庶績允暢。”這里“元戎”是謂主將,統帥。而按王公淑生活的年代,假設他20余歲出仕,大致在這里是指時任幽州盧龍節度使的劉濟、劉總父子。這“累辟”即連續招來,授予官職。“解褐”是指脫去粗布衣服,喻初任為官。這“邊務”是指邊境事物。而因土質為紫色,古人也曾把長城稱之為“紫塞”。在這里“灸蜾”本是作“炙轂過”。這“過”為“輠”的假借字。 “輠”是古時車上盛貯油膏的器具,在這里比喻言語流暢風趣。志文在這里是說幽州的節度使多次力邀王公淑到府衙任職,他只好脫去平民衣服供職于幽州盧龍節度使府,出任了節度要籍。上任后即刻就獻出了與奚、契丹交境線上的管理方略,使幽州北部周邊的危機形勢很快地就有了改變。他在出任盧龍節度巡官后,很快就使得幽州北部長城地帶的混亂局面得到了安寧。其才智和謀略在他流暢風趣的言語中,得到了很好地體現。幽州與盧龍地區平安與危險的各項事物,也都仰仗著他的參謀與輔佐,在治理政策上得到了應有的保障。
志云:王公淑“遷幽州節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蘊魏絳和戎之美,恢田疇開塞之功,揚名閫外,就列殿中。”因政績他升任掌管文書工作的幽州節度使自辟的“節度判官”,以及兼任由朝廷任命的糾察失職的“殿中侍御史”等官職。這里“魏絳”是指春秋時期晉國上卿。他的先祖為庶人,與周同姓,因伐紂有功被周武王封于畢,于是以畢為姓。到畢萬時,事晉獻公,因伐霍、耿、魏等國有功,又被封于魏,遂又以魏為姓。魏絳在晉國提出并實施的“和戎之策”,即與晉國相鄰的北方少數民族采取和戎政策,借鑒歷史的經驗,采用以德服人的辦法,在和戎政策實施的短短八年中,晉國與戎狄取得了和睦相處。而“田疇”是為東漢末年人,是漢魏之際著名的隱士、學者。他剛直不阿,俠膽仗義,在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脅迫漢獻帝遷都長安。他代表幽州牧劉虞去朝廷拜見皇帝,以示支持朝廷。但田疇完成使命還沒回到幽州,劉虞卻被公孫瓚殺害,但他不顧別人的勸阻執意到劉虞墳前哭泣。他曾率領民眾到深山謀生,并為他們制定各種政策,使他在北方民眾中名聲大振,就連北方少數民族烏丸、鮮卑等也都派遣使者送來貢物。他曾被朝廷、袁紹父子多次征召都被他蜿拒。而他卻甘愿為曹操出力,在曹操北征烏桓時立下赫赫之功,但他多次又拒絕獎賞,甘當一名隱土。這“閫外”是指京城外任的將吏。在《晉書·陶侃傳》載: “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志文在這里通過兩個歷史典故,形容王公淑在調任幽州的府衙任職后,就像歷史上著名的魏絳、田疇一樣,運用謀略采取的“懷柔政策”,使得幽州邊界安寧、人民樂業,其取得的成就使得他成為遠近聞名、享譽朝野的賢能之官。
志云:王公淑“恩光寵賜,榮曜金紫。授盧龍節度留后、營府都督、柳城軍使、平州諸軍事、平州刺史。扇和風以糜草,冒靈雨以赴期。”這里“恩光”本意是指恩光星,它是以星宿配合十二宮的術數算命方法,是一種星相術,亦是中國傳統相術中的一支,因其系統里以紫微星為諸星之首,故得名。而“寵賜”即指帝王的恩賜。在《三國志·吳志·士燮傳》載:“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而“榮曜”即富貴、顯耀。 “金紫”是“金印紫綬”簡寫,指高官顯爵。唐代三品以上官員的服飾是為金魚袋及紫衣。這里“和風”是指速度和緩的風。 “糜草”是藥草名。在《呂氏春秋·孟夏》載: “是月也,聚蓄百藥。糜草死。”這里“靈雨”是喻君王的恩澤。唐代楊巨源《春日奉獻圣壽無疆詞》載:“靈雨含雙闕,雷霆肅萬方。”而“赴期”即赴約。志文在這里是說王公淑受到了好運的垂青,皇帝的恩賜使他得到顯耀的官位及高級的服飾。他又榮升“盧龍節度留后、營州都督、柳城軍使、平州諸軍事、平州刺史”等官職,這些榮耀使得他每每都在和緩微風的伴隨下,聞著靡草的芳香,沐浴著君王的恩澤,愉悅地到各地去赴任。
志云: “虎聞渡河,不假飛將之射;民和讓畔,甚于西伯之時。”這里“飛將”是指西漢時期著名軍事家李廣將軍。李廣的祖先是為秦朝鼎鼎大名的大將軍李信,李信曾率領秦軍戰敗燕國太子丹,成就秦國的統一大業。而李廣深得家傳弓法的精髓,射得一手好箭。在匈奴大舉入侵大漢邊關時,李廣帶兵多次抗擊匈奴侵擾。因他善于用箭殺敵,而被人們稱為“飛將軍”。而文中“西伯”即是指戰國時期魏國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及無神論者西門豹。流傳至今《西門豹治鄴>的故事,就是講述了西門豹初到鄴地時嚴懲貪官巫婆,并且大力興修水利,使鄴地經濟很快地得以繁榮的故事。志文在這里用歷史人物的典故,來喻王公淑到任后治理地方事務的速度與成就,即掃蕩貪官污吏的時間,要快過李廣用箭射死正在飛躍渡河時老虎;而提升民眾幸福和諧的指數,可堪比西門豹治鄴時的成就。
志云: “樂輸井稅,轉牧媯汭。入境露冕,下車求瘼。奸邪屏跡,疲甿息肩。鄰有凋弊,借以撫綏。更充防御軍使,古人辭大不辭小之義也。趣裝蒞之,政理仁慈,邊俗樂業,邦家遽肥。”這里“樂輸”原是指東晉和南朝時期對浮浪人所征之稅。在《隋書·食貨志》載: “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準所輸,終優于正課焉。”而“井稅”即謂田稅。在《魏書·李世安傳》載:“井稅之興,其來日久。”唐代錢起《觀村人牧山田》詩曰: “貧民乏井稅,塉土皆墾鑿。”而這里“媯汭”即媯水之意,即指幽州城西北部的媯州。而志文“露冕”是指隱者所戴的一種便帽。在《晉書·溫嶠郗鑒傳》載: “方回踵武,奕世登臺。露冕為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而這“求瘼”是謂訪求民間疾苦。唐代陸贄《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載: “求瘼救災,國之令典。”這里“奸邪”是指奸詐邪惡的人和事。“屏跡”即指躲避隱匿。在《晉書·卞壺傳》載: “轉御史中丞,忠于事上,權貴屏跡。”而在《北史·拓跋景山傳》中載: “法令明肅,賊盜屏跡,部內大清。”這里“疲甿”是指疲困之民。唐代白居易《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策》載: “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甿,遠乖富庶。”這“息肩”是謂休養生息。在《史記·律書》載: “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而這“凋弊”是指凋敝。在《三國志·魏志·衛覬傳》載: “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不可復振。”而“撫綏”即謂安撫,安定。在《書·太甲上》載: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志文中“辭大不辭小”是指做大事的人不拘泥于小節,有大禮節的人不責備小的過錯。在《史記·項羽本紀》載:樊噲“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而志文“趣裝”是指速整行裝。 “邊俗”即邊地民眾。在《后漢書·獨行傳·趙苞》載: “抗厲威嚴,名振邊俗。”而《北齊書·盧潛傳》載: “潛輯諧內外,甚得邊俗之和。”志文在這里是說由于王公淑在任上治理有方,成績頗豐,賦稅及治安都有很大提升,他又一次被調任到幽州北部的媯州進行治理。剛一到任就化裝成平民百姓深入民間,調查百姓疾苦與訴求,他很快地就把當地整治得井井有條。雖然相鄰的州郡還有許多不和諧因素,但他的治理還是鎮定了一方。此后他又兼任了鎮守幽州北大門的防御軍使。
志云:“遵老氏之止足,同泉明以朅來。祁奚請老,萊子寧親。返駕角巾,色養不遺。神味福善,天胡奪魄。”這里“老氏”是指老子。東漢張衡《東京賦》就載有:“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而“泉明”是指晉代的陶淵明。在唐時為了避唐高祖李淵的名諱,唐人改稱淵明為“泉明”。在《晉書·隱逸傳·陶潛》曾記載陶淵明在當彭澤縣令時,因不“為五斗米折腰”,從而棄官歸隱山林。以后借指欲作歸隱之計的縣令。唐代李白的《送韓侍御之廣德》就有:“暫就東山賒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王琦注: “《野客叢書》載: 《海錄碎事》謂淵明一字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淵明為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淵之稱楊泉,非一字泉明也。 《齊東野語》載:‘高祖諱淵,淵字盡改為泉。”這里“祁奚”是謂周代的晉國大夫。他食邑在祁,初任中軍尉。晉悼公三年,請告老。先后推舉了自己的仇人和兒子來接替。被譽為“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晉平公即位,任以為公族大夫。而“萊子”即是指春秋時楚國著名的隱土老萊子。相傳他居于蒙山之陽,自耕而食。楚王多次召其出仕,而他就是不就任,以至世上留傳有老菜子“戲彩娛親”的故事。而文中的“寧親”即是謂使父母安寧。漢代揚雄在《法言·孝至序》載: “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于寧神。”即是指老萊子。這里“返駕”即是指回歸。在晉代王嘉《拾遺記·前漢下》載: “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舍于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歌‘萬歲。”這里“角巾”原意指棱角的頭巾,是謂古代隱土冠飾。在《晉書·王導傳》載: “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而“色養”是指晚輩孝敬前輩的一種言行最高規范。這里“神味”即神韻趣味。“福善”即指福德善行。 “天胡”代指運氣。而“奪魄”是指驚心動魄。唐代宋之問《嵩山天門歌》載: “晚陰兮足風,夕陽兮艴紅。試一望兮奪魄,況眾妙之無窮。”志文在這里用了大量筆墨,列舉了眾多歷史人物與典故,即老子、陶淵明、祁奚、老菜子等,用這些歷史上的實例來說明王公淑在出仕過程中的辛苦及成就,這是神奇的善行與驚心的運氣交匯而成的。
志云: “春秋六十九,大中二年( 848)十月十四日,兌易簀歸全于薊門私第。六年( 852)二月十七日,祔葬于先吳氏夫人之真宅,候通年也。”這里“易簀”即指人病重將死。而“薊門”代指幽州城。春秋戰國以后的燕國,它是以“薊”作為都城,稱薊城亦為薊門,而唐幽州城它是承繼了漢魏時期的薊城。這個稱呼在唐人的詩詞中經常地出現,如:祖詠的《望薊門》、于鵠的《送韋判官歸薊門》等。而詩人王昌齡的《穆侍御出幽州》中載:“一從恩譴度瀟湘,塞北江南萬里長。莫道薊門書信少,雁飛猶得到衡陽。”這些詩詞中所指的“薊門”,無疑都是代指唐朝的幽州城。此志文所記“薊門”,是唐代石刻文物中的又一實例。而“真宅”是謂人死后的真正歸宿。在《列子·天瑞》中載:“鬼,歸也,歸其真宅。”從志載可知,他因病逝于“春秋六十九,大中二年( 848)十月十四日,兌易簀歸全于薊門私第。”即幽州的家中。按他去世的年歲倒推,他應出生于唐代宗大歷十四年(779)。按最早他20余歲入仕,從而推斷他出仕的年代大約是在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785~810)、劉總(810~821)父子統治幽州時期,并曾在朱克融(821~826)、李載義(826~831)、楊志誠(831~834)、史元忠(834~841)、張仲武(841—849)等多位時任幽州盧龍節度使手下任職,可以說他得到眾多幽州地區最高統帥的認可與信賴。特別是他在風云變幻的四十年出仕過程中,經歷了幽州盧龍節度使十余次的爭斗、更替,但他始終是左右逢源、屹立不倒,并且還得到了他們的賞識與晉升,可見他的能力之強、情商之高是一般人不可比擬的。他逝于幽州盧龍節度使張仲武統治時期,而家人卻在四年后把他下葬于幽州盧龍節度使張允紳(850~872)治理時期,這一方面是用心血來整治修膳原有墓室,而另一方面也是在等待一個吉兆的年景。而幽州盧龍節度使張允紳治理幽州二十佘年,他被后人普遍認為是幽州最為安定的時期。志載其吳氏夫人于開成三年( 838)“窆于幽州幽都縣西北界樊里之原,禮也。”即其夫人吳氏早于他十年去世,葬于今日北京海淀區八里莊地區玲瓏公園西墻外墓葬出土地。可見,他死后被其子女重新整修完先逝夫人墓地后,才把他們合葬在一起,并鐫刻了墓志銘。這里葬地“樊里”之名,應是指歷史上的“樊村”。在唐代鄉屬下是村,這“里”和“村”是互通的。雖然此墓志沒有記載鄉屬,但其志銘日: “薊北迥野,原上孤墳”,即是指葬于幽州城北,這與墓葬實際出土地方向是一致的。幽州城在春秋戰國至漢魏時一直是被稱作薊城,而此墓銘稱墓地方位為“薊北”是無誤的。而根據史上歷年來在北京舊城西北部出土的眾多唐代墓志記載,這里應屬于唐幽州幽都縣的保大鄉樊村,而保大鄉現今只出現過兩個村名,其中一個是“杜村”,另一個就是“樊村”。保大鄉“杜村”的記載也僅見于清乾隆年間出土的《唐崔載墓志銘》云:元和十四年( 819)崔載“窆于幽州幽都縣保大鄉杜村北一里之原。”筆者考證其葬地“杜村”就是在今天的北京海淀區中關村廣場南側的丹棱街一帶。而對唐保大鄉“樊村”的記載就較多了,如:在清代道光十一年(1831)于京師西直門外出土的《唐王公晟夫人張氏墓志銘》載葬于“幽州幽都縣保大鄉樊村之原。”1959年在北京西直門外紫竹院三虎橋水利學校出土的《唐范陽盧公夫人趙氏墓志銘》載:趙氏“文德元年( 888)二月九日葬于府城西北十里樊村之原也。”而1966年在北京阜成門外八里莊引水工程工地出土《唐耿宗倚墓志銘》載: “以廣明二年( 881)十月二十七日葬于幽都縣界保大鄉樊村。”1975年在北京阜成門外甘家口北京鋼絲廠出土的《唐姚季仙墓志銘》載:成通五年( 864)“窆于幽都縣界保人鄉樊村之原。”(保人鄉是為保大鄉之誤)據《光緒順天府志》記載,清代出土的《唐閻好問墓志銘>云: “咸通十四年(873)仲秋月二十八日厝神于幽州之乾十里高梁河岸保大鄉。”而其子即2005年在北京海淀區三虎橋一帶渣土中發現的《唐閻晉及夫人馬氏合祔墓志銘》載: “改卜地于府城西北樊村先塋西北一里之原。”結合以上這些墓志的出土地點來看,王公淑墓葬的出土地點恰就在這些墓葬出土地點的包圍之中,所以此墓志所稱“樊里”就是指“樊村”無疑。而志文中的“幽都縣西北界”應是指幽州城外幽都縣與同是幽州治下九縣之一廣平縣的分界線,這里因證據不足暫緩考證。
志云: “夫人吳氏,濮陽人。太伯封吳,子孫著姓。皇節度驅使官之女。年才十七,廟見榛栗。孝乎舅姑,工于織紅,閏門肅穆,中外克諧。嗚戲!命矣!不享遐齡,五十有一,屬纊牖下,開成二年九月廿五日。幽邃華堂,俄成兇室。”據《元和姓纂》載: “周太王子太伯、仲雍封吳,后為越所滅,子孫以國為氏。”是說吳姓源于姬姓,肇端于吳國,形成戰國初期,始祖是周朝的太伯和仲雍。武王滅商后,封仲雍的曾孫周章為吳子,追封太伯為吳伯。以吳國號為姓,是黃帝軒轅氏的直系后裔。吳氏夫人其父為“皇節度驅使官”,這是中唐以后備藩鎮使府特設置的官職,其主要職責較雜,似有督察催辦等多項工作,唐后期在左右神策軍中亦設有驅使官二人。這“廟見”是謂古代婚禮成婦之禮中的重要儀式。即婚后至遲三個月內,須擇日率新娘至夫家宗廟祭告祖先,以表示婚姻已取得夫家祖先的同意。這“榛栗”就是指榛子、栗子,而“舅姑”在古時是指“公婆”,即甥男娶舅父的女兒為妻。由于是既是舅父也是岳父。所以二人稱之為翁婿關系,且又是舅甥關系。從而把丈夫的父母稱之為“舅姑”。這“克諧”在這里有如愿已償、順利成功的意思。志文在這里詳記了其夫人吳氏的生平過往及逸事賢德。
志云:王公淑“子八人,女三人。長日弘裕,幽州昌平縣丞。次日弘爽、弘慶、弘道、弘安、弘信、弘順、弘德,俱稟義方,深閑輯理。婚偕茂族,歸盡名家。即丁憫兇,幾至滅性。哀榮薤露,稱家送終。抑呼天殞絕之聲,假玄壤乃遷之志。”即是說王公淑的長子王弘裕,是為輔佐幽州昌平知縣的縣丞。而其他子女也都是按規矩行事且遵守道理的人。這些婚配給茂族的子女,都已返回家中進行哀悼,而四子的傷心哭嚎,差點使他喪失了性命。在悲痛哀嚎祭祀后,他們一同把父母合葬于墓穴之中,并鐫刻了墓志銘。
綜上所考,王公淑是為多任幽州盧龍節度使手下的得力干將,他入仕的時代大致是在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父子治理時期,后又在朱克融、李載義、楊志誠、史元忠、張仲武等諸多幽州盧龍節度使手下任職。他不僅在幽州、盧龍節度使府內盡心盡力、出謀劃策,先后出任幽州節度要籍、幽州節度判官、盧龍節度留后等,并且還多次出任幽州以外其它州郡的行政官員,直接來治理屬地,成績斐然、百姓稱道。在兼任柳城軍、防御軍等使職時,更是常年活動于幽州城的東北部與北方契丹、奚族等異族爭奪疆土,并開墾田地、整頓民風,既保全了幽州的疆域,又取得了多次大捷,是多任幽州盧龍節度使手下不可多得的以謀略著稱的戰將與謀士。正是他的英勇付出與謀劃,從而得到了多任節度使的信賴。而他逝后子女也為他精心修建了豪華的墓室,可惜的是眾多的隨葬品被盜墓賊所窺竊,早已被一掃而光,只是留下了在當時來看價值不大且不好攜帶的墓志銘,以及不易揭走的壁畫作品。也正是因為這樣,才使我們今天還能夠欣賞到幽州地區在唐代的壁畫佳作及繪畫水平,并根據墓志記載內容對唐幽州的歷史文化進行一定的研究,從而為今天的北京地方史研究做出一點點貢獻。
(責任編輯:田紅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