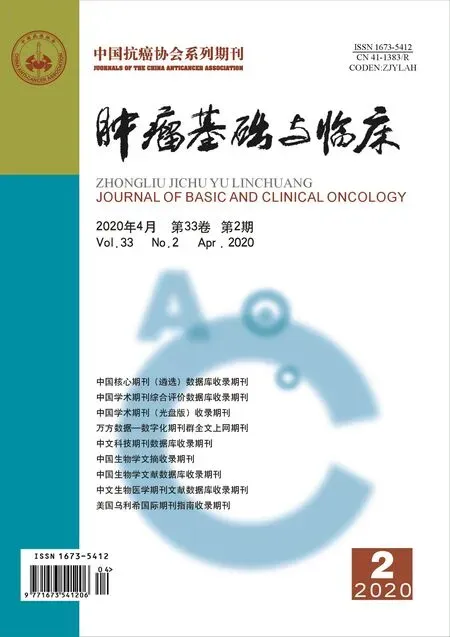22例高級別B細胞淋巴瘤非特指型的臨床分析
李佳音,張明智
(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腫瘤科,河南 鄭州 450052)
2016年新版WHO淋巴瘤修訂分類提出“高級別B細胞淋巴瘤(high grade B-cell lymphoma, HGBL)”的定義[1-3]。其中包括2種類型:1)HGBL,伴有MYC和B細胞淋巴瘤-2(B-cell lymphoma-2, Bcl-2)(或)Bcl-6基因重排,又稱為“雙打擊”或“三打擊”淋巴瘤(double- and triple-hit lymphomas, DH/TH),即存在MYC重排,同時伴有B淋巴細胞瘤Bcl-2或Bcl-6基因重排的B細胞淋巴瘤;2)高級別B細胞淋巴瘤-非特指型(high grade B-cell lymphomas-not otherwise specified, HGBL-NOS),即形態(tài)學介于Burkitt淋巴瘤(Burkitt lymphoma, BL)和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diffused large B cell lymphoma, DLBCL)之間,不含有MYC和Bcl-2(或)Bcl-6基因易位的淋巴瘤[4-5]。
HGBL-NOS發(fā)生率較低,主要發(fā)生于成年人,該腫瘤具有極強的侵襲性,且生存期較短,超過半數(shù)的患者初診時即出現(xiàn)廣泛的、結(jié)外部位的累及[6]。對于HGBL-NOS患者,目前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wǎng)絡(NCCN)指南多推薦應用利妥昔單抗聯(lián)合環(huán)磷酰胺、表柔比星、長春新堿和潑尼松(R-CHOP)方案,利妥昔單抗聯(lián)合依托泊苷、環(huán)磷酰胺、表柔比星、長春新堿和潑尼松(R-EPOCH)方案,或高強度治療方案[如利妥昔單抗聯(lián)合環(huán)磷酰胺、長春新堿、表柔比星和地塞米松,交替甲氨喋呤和阿糖胞苷(R-Hyper CVAD/MA)方案、利妥昔單抗聯(lián)合環(huán)磷酰胺、表柔比星、長春新堿、阿糖胞苷和甲氨喋呤,交替依托泊苷、異環(huán)磷酰胺、阿糖胞苷和甲氨喋呤(R-CODOX-M/IVAC)方案等],尚無最佳推薦治療方案。
由于HGBL-NOS發(fā)病率低,臨床少見,其病因及發(fā)病機制至今尚不清楚[7],診斷需依據(jù)臨床資料、細胞形態(tài)學、免疫組織化學、細胞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特征綜合考慮,所以為了提高對該病的認識,本研究對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收治的HGB-NOS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總結(jié)其臨床病理學特征,以提高對該類腫瘤的認識。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本研究納入的22例患者均為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2013年1月至2019年6月收治的經(jīng)病理學確診且資料完整的HGBL-NOS患者,病理切片均經(jīng)2位以上經(jīng)驗豐富的病理科醫(yī)師觀察并獨立診斷,病理結(jié)果參照WHO淋巴造血系統(tǒng)腫瘤分類,并結(jié)合細胞形態(tài)學、免疫組織化學、細胞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特征綜合考慮進行診斷分類,如診斷意見不一致,則進一步會診病理切片。雙表達淋巴瘤(double expressor lymphoma, DEL)定義為:通過免疫組織化學檢測MYC蛋白表達率≥40%,Bcl-2蛋白表達率≥50%。單打擊淋巴瘤(single-hit lymphoma, SHL)患者定義為:經(jīng)熒光原位雜交技術(shù)(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檢測結(jié)果提示MYC基因易位。
1.2 治療方案根據(jù)22例患者初始治療方案可分為2組:1)R-CHOP/EPOCH方案組(12例):接受R-CHOP方案患者8例,接受R-EPOCH方案患者4例;2)高強度化療方案組(10例):接受R-HyperCVAD/MA方案5例,接受R-CODOX-M/IVAC方案5例。
1.3 觀察指標對患者的性別、年齡、Ann Arbor分期、國際預后指數(shù)(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IPI)評分、乳酸脫氫酶(lactic dehydrogenase,LDH)水平、β2微球蛋白水平、美國東部腫瘤協(xié)作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評分、B癥狀、病變侵犯部位、首發(fā)癥狀、病理特征、初治化療方案強度及疾病轉(zhuǎn)歸等進行分析。
1.4 療效評價根據(jù)Cheson淋巴瘤療效判斷標準[8]進行近期療效評價,分為完全緩解(complete remission, CR)、部分緩解(partial remission, PR)、穩(wěn)定(stable disease, SD)以及疾病進展(progressive disease, PD)。以CR+PR計算總有效率(overall response rate, ORR)。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 OS)定義為從確診時間至因任何原因死亡的時間或末次隨訪截止時間。疾病無進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定義為從接受治療開始,至觀察到PD、復發(fā)、發(fā)生因任何病因死亡或末次隨訪的時間。兩者均以月為單位。
1.5 隨訪隨訪采用查閱病歷和電話隨訪的形式,末次隨訪日期為2019年12月1日,中位隨訪時間為23(4~76)個月。
1.6 統(tǒng)計學處理采用SPSS 24.0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繪制生存曲線,用log rank檢驗比較組間累計生存率差異。采用單因素分析篩選影響HGBL-NOS的預后因素。檢驗水準α=0.05。
2 結(jié)果
2.1 臨床特征本研究22例患者中,男15例(68.2%),女7例(31.8%),中位年齡33(14~71)歲。首發(fā)癥狀主要表現(xiàn)為淋巴結(jié)腫大、發(fā)熱、腹痛、腹脹等,有B癥狀者(發(fā)熱、盜汗、半年內(nèi)體質(zhì)量下降超過10%)7例(31.8%),Ann Arbor分期Ⅰ~Ⅱ期患者9例(40.9%)、Ⅲ~Ⅳ期13例(59.1%),IPI評分低危/低中危(0~2分)6例(27.3%)、高中危/高危(3~5分)16例(54.5%)。結(jié)外侵犯>1處者14例(63.6%),其中累及部位包括胃腸道5例、骨髓7例、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2例、骨骼2例、眼瞼2例、肺部1例。實驗室檢查結(jié)果示,LDH水平升高8例(36.4%),β2微球蛋白水平升高6例(27.3%)。
2.2 病理特征22例患者病理標本均采用HE染色,并進行免疫組織化學及FISH檢測。形態(tài)學檢查:腫瘤細胞呈中等大小,彌漫性增生伴部分區(qū)域大細胞浸潤,小淋巴細胞少見。免疫表型:22例CD20陽性,17例CD19陽性,14例CD79a陽性,18例Ki-67增殖指數(shù)>90%,15例MYC陽性,14例Bcl-2陽性,15例Bcl-6陽性,其中符合DEL診斷標準患者11例。分子細胞遺傳學水平上,22例患者均行FISH檢測,其中伴有單一MYC基因重排且符合SHL診斷標準患者8例。
2.3 治療及轉(zhuǎn)歸22例患者中位隨訪時間為24(4~76)個月,2 a PFS率及OS率分別為40.9%和59.1%(圖1)。截止至末次隨訪時間,其中22例患者中死亡8例,存活14例,中位PFS為5個月,中位OS暫未達到。其中8例死亡患者中,因PD而死亡5例,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免疫療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CAR-T)不良反應1例,化療相關(guān)不良反應1例,余1例死因不明。其中一線治療中未獲得CR或治療后復發(fā)的患者,換用其他方案治療。4例患者經(jīng)化療達到CR后聯(lián)合自體造血干細胞移植(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SCT),1例復發(fā)難治患者聯(lián)合CAR-T治療。見表1。
22例HGBL-NOS患者確診后均接受一線化療,療效評價為CR 6例(27.3%),PR 9例(40.9%),PD 7例(31.8%),ORR為68.2%。其中初治時采用常規(guī)的R-CHOP/EPOCH方案患者(R-CHOP/EPOCH方案組)共12例(54.5%),ORR為58.3%;采用高強度化療方案患者(高強度化療方案組)共10例(45.5%),ORR為80.0%。高強度化療方案組ORR較R-CHOP/EPOCH組稍高,但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80%、58.3%,P=0.381)。在遠期療效對比中,高強度劑量組PFS和OS均優(yōu)于R-CHOP/EPOCH組(PFS:χ2=6.912,P=0.009;OS:χ2=4.192,P=0.041;圖2)。在亞組分析中,DEL患者的PFS與OS均稍短于non-DEL患者,但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FS:χ2=1.926,P=0.165;OS:χ2=2.975,P=0.085;圖3)。與SHL患者相比,non-SHL患者的OS與PFS稍好,但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FS:χ2=3.100,P=0.078;OS:χ2=1.089,P=0.297;圖4)。

表1 22例HGBL-NOS患者的基本臨床資料

圖1 22例HGBL-NOS患者的總體PFS(A)和OS(B)生存曲線

圖2 R-CHOP/EPOCH組與高強度方案組患者的PFS(A)和OS(B)生存曲線

圖3 DEL組與non-DEL組患者的PFS(A)和OS(B)生存曲線

圖4 SHL組與non-SHL組患者的PFS(A)和OS(B)生存曲線
2.4 預后分析為了進一步探討影響患者OS的預后因素,采用單因素分析對相關(guān)因素進行分析,包括性別、年齡、Ann Arbor分期、IPI評分、LDH、β2微球蛋白、ECOG評分、Ki-67增殖指數(shù)、B癥狀、累及結(jié)外病變等,分析結(jié)果顯示IPI評分3~5分患者預后較差(χ2=4.344,P=0.037)。見表2。

表2 22例HGBL-NOS患者的預后相關(guān)因素分析
3 討論
近年來,惡性腫瘤已居我國居民死亡原因第1位,淋巴瘤是常見的血液系統(tǒng)惡性腫瘤,具有極強的異質(zhì)性[9-10]。HGBL-NOS是一類特殊的、罕見的侵襲性B細胞淋巴瘤[11-12],2008年WHO修訂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分類將其單獨分類列出,其中包括形態(tài)上介于BL和DLBCL之間不能分類,伴或不伴有MYC與Bcl-2或Bcl-6重排的淋巴瘤,命名為DLBCL/BL[13]。2016年WHO新提出HGBL的定義,包括HGBL,DH/TH和HGBL-NOS[3]。自2016年WHO非霍奇金淋巴瘤分類修訂以來,既往研究報道DH/TH較多[14-15],而暫無關(guān)于HGBL-NOS的研究報道,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22例HGBL-NOS患者的臨床資料,進一步了解其臨床病理特征,增加對該類型淋巴瘤的認識。
該類型淋巴瘤的發(fā)生率極低,主要發(fā)生于成年人,占成人侵襲性B細胞淋巴瘤的3%,屬于灰區(qū)淋巴瘤的一種類型,中位發(fā)病年齡為55(18~80)歲,男性發(fā)病率高于女性,結(jié)外侵犯多見,如胃腸道、骨髓[6]。超過半數(shù)的患者初診時即出現(xiàn)廣泛的、結(jié)外部位的累及,外周血和骨髓亦常有累及。本研究患者中,發(fā)病的中位年齡為33(14~71)歲,結(jié)外侵犯>1處者14例(63.6%),其中累及部位包括胃腸道5例、骨髓7例、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2例、骨骼2例、眼瞼2例、肺部1例。
HGBL-NOS這種新分類淋巴瘤具有DLBCL和BL之間的形態(tài)學特征,缺乏DH/TH遺傳學改變。腫瘤細胞形態(tài)呈多樣性,這些病例通常具有中等大小或爆破樣的細胞特征,具有細而分散的細胞核或類似BL樣的細胞核,有時存在“星空”現(xiàn)象[16]。HGBL-NOS腫瘤細胞的大小和形狀較BL變化更大,形態(tài)學變化不定,多為中等大小腫瘤細胞彌漫性增生伴部分區(qū)域大細胞浸潤,小淋巴細胞少見[17]。免疫表型上,該型淋巴瘤細胞多表現(xiàn)為B細胞標志物(CD19、CD20、CD22等)陽性,CD10和Bcl-6陽性,Bcl-2可陽性,Ki-67增殖指數(shù)常>90%,遺傳學上沒有MYC和Bcl-2基因重排,經(jīng)常表現(xiàn)為復雜核型。有些病例細胞類似于BL,但免疫表型和遺傳學特征與BL不符;有些病例免疫表型符合BL,但核的大小呈多樣性,介于BL和DLBCL之間[6]。HGBL-NOS的診斷需要結(jié)合細胞形態(tài)學、免疫組織化學、細胞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特征綜合考慮,臨床上較為少見,其病因及發(fā)病機制尚不清楚。
MYC基因可表達于多種惡性腫瘤,約50%的HGBL-NOS病例中可檢測到單一MYC基因重排[18-19],Li等[20]的中位隨訪時間為25個月的回顧性研究發(fā)現(xiàn),61例SHL與DHL患者的2 a OS率為41%和48%(P>0.05),且與DLBCL/BL患者中不伴有MYC重排患者比較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Landsburg等[21]的一項前瞻性研究發(fā)現(xiàn),與DLBCL或介于DLBCL與BL之間特征的B細胞淋巴瘤(B-cell lymphoma,unclassifiable,BCLU)中不伴有MYC基因重排的患者相比,SHL患者的預后較差(PFS和OS比較,P均<0.001)。Herrera等[22]的回顧性研究發(fā)現(xiàn),在DLBCL患者中,與DEL相比,non-DEL患者的預后較好(4 a PFS率:48%、59%,P=0.049;4 a OS率:56%、67%;P>0.05)。既往多項研究[22-23]表明在DLBCL中,DEL是不良預后因素之一。本研究中DEL患者的PFS與OS率均稍短于non-DEL患者(PFS:27.3%、54.5%,P=0.164; OS:45.5%、81.8%,P=0.085);與SHL患者相比,non-SHL的OS與PFS率稍好,但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FS:57.1%、12.5% ,P=0.078; OS:71.4%、50.0%,P=0.297)。在HGBL-NOS患者中,DEL和SHL可能與預后不良有關(guān)。但由于病例數(shù)較少,所以需要進一步擴大樣本量來驗證。
由于該型淋巴瘤發(fā)病率低,較為罕見,臨床對其認識較少,暫無標準的治療方案。美國NCCN指南多推薦R-CHOP/EPOCH或高強度化療方案(如R-Hyper CVAD、R-CODOX-M/IVAC等),后續(xù)可聯(lián)合ASCT。Lin等[24]回顧性分析52例DLBCL/BL患者的臨床資料,結(jié)果顯示,伴有MYC基因重排的患者中Hyper CVAD或CODOX-M/IVAC組較R-CHOP組預后較好,但在不伴有MYC基因重排的患者中,不同化療方案間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McPhail等[25]回顧性分析了100例診斷為HGBL-DH/TH的患者,與接受其他治療的患者相比,接受R-CODOXM/IVAC治療的患者PFS效果更好(72%、39%,P=0.04),但OS改善不顯著(P=0.10)。Corazzelli等[26]一項前瞻性研究發(fā)現(xiàn),在BCLU患者中,CODOX-M/IVAC方案聯(lián)合甲氨喋呤等藥物鞘注與CODOX-M/IVAC方案相比較,可提高PFS率(65%、37%,P<0.05)。由于本研究未將鞘內(nèi)注射納入研究對象,聯(lián)合鞘注是否能改善預后需要進一步探索。本研究發(fā)現(xiàn)接受強化治療的患者與R-CHOP/EPOCH組患者近期療效未見明顯差異,但遠期療效評價中,高強度化療方案可改善PFS和OS,與上述研究中結(jié)論相仿。本研究22例患者中4例接受ASCT,其中1例因疾病復發(fā)死亡,余3例達到CR且持續(xù)隨訪中。鑒于目前病例數(shù)較少,ASCT是否能改善預后仍需進一步擴大樣本量驗證。
Perry等[27]研究發(fā)現(xiàn)IPI評分0~2分(低危/中低危)及血清LDH水平正常的BCLU患者預后更好。多項研究[28-29]表明在DLBCL或BL型淋巴瘤中,IPI評分是獨立預后因素。本研究通過單因素分析研究發(fā)現(xiàn),IPI評分與HGBL-NOS預后有關(guān)。
綜上所述,HGBL-NOS是一種罕見的、且生存期短的高度惡性腫瘤。高強度化療可延長患者的生存期,DEL和SHL可能與預后不良相關(guān),IPI評分3~5分是預后不良的因素。然而,由于我們的小樣本和回顧性分析的潛在局限性,所以結(jié)果需要擴大樣本量及開展前瞻性研究來進一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