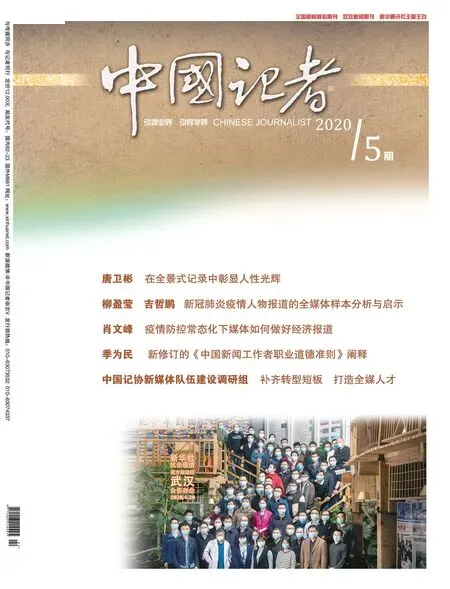融合時代重大主題報道的創新探索
——以紹興市新聞傳媒中心《向海》系列報道為例
□何國永
內容提要 融媒體時代傳統媒體如何擺脫重大主題報道標簽化、平面化的痼疾,堅守內容生產,提升傳播影響力?紹興市新聞傳媒中心《向海——紹興“擁抱大灣區融入長三角”系列述評》緊扣重大主題,立足全局視野,辯證客觀梳理,平和親切說理,為相關報道提供了參考。
融媒體時代,傳統媒體重大主題報道如何擺脫標簽化、平面化的慣性束縛,強化議題設置和表達創新,堅守內容為王、立意高遠,提升傳播影響力,這是一個亟需破解的共性課題。在2019年度浙江省新聞獎重大主題報道獎評選中,由紹興市新聞傳媒中心選送的《向海——紹興“擁抱大灣區融入長三角”系列述評》(含《紹興之醒》《紹興之行》《紹興之新》三篇),獲得重大主題報道獎一等獎。
綜觀這組報道,緊扣重大主題,立足全球視野、中國高度,辯證客觀梳理,平和親切說理,起到了統一認識、明晰方向、認清路徑、鼓舞信心的作用。有讀者認為,這也是紹興日報近年來直面紹興發展機遇和挑戰,以媒體的勇氣和擔當進行客觀報道的一大創新舉措。
一、選題突破:在重大題材中尋找報道方位
2019年,長三角一體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在這樣的宏闊視野下,每座城市都在尋找新的發展突破點,紹興發展也迎來了一個風口。這組報道敏銳地把握住了這個歷史性的節點,橫向以長三角一體化為視野,縱向追溯到改革開放以來紹興發展的短板,作了深刻、系統的審視,以梳理發展思路,展望未來前景。
這個節點的發掘和把握,得益于對紹興之“過去”和“現在”的深刻洞察——紹興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蘊、改革開放的先發優勢和特殊的地理位置,經歷了一條先揚后抑的發展曲線:改革開放初期,敢闖敢冒的紹興人抓住短缺經濟和國家取消化纖原料供應限制的歷史機遇,通過創辦鄉鎮企業實現了紡織工業的大飛躍,從而催生了龐大的民營經濟群體,形成獨特的發展優勢。
然而,本世紀初,隨著城市化浪潮的推進,夾在杭州寧波兩大城市之間,紹興的先發紅利漸漸耗盡,“大樹底下不長草”的困擾日益突出。近20年來,紹興一直在苦苦掙扎,尋求突破路徑,其曾經的輝煌和后來的彷徨,既有著獨特而鮮明的個性,也有著地市級城市普遍面臨的共性。
2002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紹興視察時強調:紹興要放在“長三角”的范圍來審視發展地位,調整發展戰略。
揚帆起航需東風。17年后,機會終于來了:長三角一體化戰略的推進,給紹興帶來了“跳出紹興”的契機。紹興市委市政府審時度勢,以足夠的敏銳性和擔當,動員全市上下凝聚起干大事的雄心和決心。早在2019年上半年即開始謀劃“擁抱”大都市圈大灣區建設的紹興方案,在長三角一體化綱要出臺后,迅速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和行動。動作之快,力度之大,跑在了兄弟城市的前面。
作為本土主流媒體,紹興新聞傳媒中心敏銳地“嗅”到了不一樣的氣息,并萌生了以此為契機策劃一組重大主題報道的設想。
然而,這組報道從哪里入手、如何展開、怎么定調和定論,卻也是個難題。

紹興的發展,至今還存在很多有爭議的地方。譬如紹興之痛,是在一輪輪的優勝劣汰中沒有完全抓住機遇而慢慢形成。早年同時起步、曾經并駕齊驅的城市如無錫、蘇州、常州等,如今早已一騎絕塵。分析他們的崛起之路,其實就可以找到紹興焦急的根源:自身的文化資源優勢沒有得到與時代共鳴的開拓性延伸,又錯過了本世紀初制造業轉型的機遇,再加上城市規模和地理位置的局限。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習慣了眼睛向內看發展,關起門來干自己的事,沒有與世界形成共生共振共榮。
長三角一體化,對紹興而言,面臨著理念之變、體制之變、路徑之變,一切發展的根源其實囿于體制而始于觀念,既要到歷史當中去尋找答案,又要基于現實,面向未來,作理性的瞭望。以避免以往媒體對敏感話題“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尷尬。
基于這樣的認識,這組報道不回避爭議,不煽動情緒,對紹興20年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理性、平和的分析,對紹興的機遇、優勢進行客觀呈現,這也是媒體在一個重大歷史節點的職責所在。
二、思想突破:從全球化視野、長三角坐標審視發展
傳統媒體的重大主題報道,往往容易陷入標簽化、平面化的解讀。尤其地市級媒體,往往局限于本地視角,參照體系也缺乏科學性、標準化,從而造成報道缺乏厚度和高度。
紹興新聞傳媒中心在錨定《向海》系列報道的題材后,就把“跳出紹興看紹興”,以題材產生影響力、以思想給人以啟迪作為本組報道的追求目標。
一是跳出傳統重大主題報道的窠臼,從大灣區、長三角、全球化的廣闊空間去尋找標尺。我們系統了解了世界各地的灣區經濟、長三角一體化推進對區域發展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的樣板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思考紹興發展,認識更清楚、理念更系統。
二是圍繞產業、城市、人才、文化等區域發展的要素進行了全方位審視、大范圍觀察。抽調骨干記者組成報道小組,赴杭州、上海、合肥等長三角重要節點城市進行深入調研和采訪,比對紹興的短板優勢和努力方向,不斷調整報道思路。廣泛搜集社會各界甚至國際社會對紹興的評價,特別是把紹興或浙江籍鄉賢徐揚生、袁寶成、周漢民等對紹興發展的精到分析和獨特思考,充實到報道中。
三是在歷史的縱深坐標上觀察、剖析一座城市的得失。我們以時間為軸,設置了紹興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三個篇章。《紹興之醒》,冷靜理性地分析了紹興積累多年的產業和城市發展困惑,以及對一體化機遇的渴求。《紹興之行》通過“兩業經”“雙城記”“活力城”高質量發展組合拳和推進“四大體系”建設借勢起跳、向高攀登的行動,描述了紹興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的路徑、思路和行動。《紹興之新》從“金扁擔”“特長生”“弄潮兒”多個維度,展示了紹興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氣象。同時,為這組報道配發的評論《向海而盛,我們期待》,則從基因、胸懷、機遇、希望四個層面闡釋了紹興“向海突圍”的內涵和意義。
區域的發展不僅僅是產業和經濟。思想如何解放?城市怎么突圍?人才高地如何打造?文化競爭力如何形成?我們立足紹興論紹興,跳出紹興看紹興,通過廣泛的采訪,用豐富的觀點、多元的視角,進行深入的梳理和論述,形成了報道的事實支撐,賦予了作品鮮活而富有思想的生命力,讓讀者看到了過去沒有看到的觀點,聽到了過去沒有聽過的聲音,開闊了思路,獲得了啟迪。
三、思辯突破:以客觀理性的方式與讀者平等交流
《向海》系列報道刊登以后,在業界和社會各界產生了巨大反響,收獲海量點贊和熱議,“學習強國”和澎湃新聞等都作了轉載推送。紹興不少機關還主動將這組報道作為學習材料,組織全員學習。
這組報道敢于客觀正視紹興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短板,道出紹興廣大干部群眾一直面臨的發展陣痛和困惑,是其引起巨大社會反響的最大亮點。報道刊發后,浙江省委常委、秘書長陳金彪高度肯定了這組報道,認為“報道體現了媒體的責任和勇氣,感受到了紹興干部群眾想發展、謀發展、促發展的熱情和激情”。紹興市委書記馬衛光作出批示,肯定“報道對紹興發展作了深刻的回顧,把大家所思所想擺在面前,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共鳴”。
大家普遍認為,這組背景深刻、主題宏大的主題報道,既有思辯之美,又有表達之新,將一個沉重的題材以富有美感的形式、輕松平和的敘述、娓娓道來的文筆,進行了從面到點的書寫,輕松好讀、故事性強,這在重大主題報道中是不多見的。
一是突破了思維禁區,直面紹興發展的矛盾和短板。
如何看待紹興“大樹底下難長草”的內因和外因?位于杭州和寧波之間,地理位置的先天不足是不容回避的外因。但一個區域的文化基因,則是外因產生作用力的土壤和環境。只有當內因和外因互相接納,才會使不利于發展的杠桿作用力最大化。我們覺得在分析原因時,內因和外因都要敢于面對。尤其是紹興人瞻前顧后、安于現狀,是把外因的作用力放大的根本原因。
如何看待發展的局限?在《紹興之醒》報道中,對紹興很多年來內生動力不足有一定篇幅的闡述,但也充分看到了這些年的努力和所做的貢獻。雖然,從歷史的客觀性來講,區域發展的快與慢,跟干部和企業家隊伍的能力、理念與責任意識休戚相關,但很多東西又往往受到內外部環境交織的影響,不管是考慮到報道刊登后的社會反響,還是考慮到事實的客觀性,報道還是以辯證的思維來科學、公正看待。
如何看待現狀與出路?不管是從橫向還是縱向比較,紹興確實像“起大早,趕晚集”,但是不是真的來不及了呢?并非如此。雖然我們在跑道上落后于人家,但我們可以改變起跑的方式和路徑,發展的機會永遠都有。尤其在長三角一體化背景下,也意味著紹興的厚積薄發能迸發出更大的能量。這是媒體必須能看到的優勢和必須要鼓舞的信心。理性、平和的態度,辯證的思維模式,是直面問題的最好方法。
二是突破了表達慣性,讓主題報道呈現親和力和閱讀美。
首先是儀式之美。這組報道,從行文架構到標題制作,都呈現出強烈的整體性和儀式美,既勢大力沉,又富有儀式感。為什么開篇之作的主標題定為《紹興之醒》,第二篇和第三篇分別是《紹興之行》到《紹興之新》?這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展現的是一座城市從過去到現在和未來的發展邏輯。每篇文章的小標題又緊扣主標題,自成體系。如《紹興之醒》,由“紹興之困”“紹興之惑”“紹興之機”三部分組成,形成完整的邏輯鏈。《紹興之行》謀篇時,本來設計的是“向海突圍”“向高攀登”“向內破壁”三個層次,反復推敲覺得邏輯遞進不夠清晰,后來改成“借勢起跳”“向高攀登”“破壁突進”。《紹興之新》,則從“金扁擔的自信”“特長生的底氣”“弄潮兒的未來”,完美詮釋了“新”的內涵。
其次是理性之美。把鮮明銳利的觀點蘊藏在平和理性的文字中,是這組報道最大的特色。雖然直面歷史的困惑和問題,但見報后不僅沒有因觀點或事實選取的敏感引發不同聲音,反而讓各方都覺得講出了自己想說的話。其實,就是做到了用客觀、辯證、理性的思維和語言表達爭議,娓媚道來、平和親切,在文章中看不到劍拔弩張、居高臨下。比如關于紹興“大樹底下不長草”的表述,在初稿中引用了很多他人的回憶與講述,雖然每個人都講得很精彩,但最后對大量的事實進行了提煉,留下了有共性的部分,不少讀者表示,報道中講清了問題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