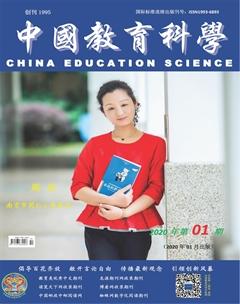語言有溫度 字詞知冷暖
戴亞兵
“詞語是最小的能獨立運用的語言單位,卻能使有限的語言最大限度地表現出無形的情感。”可見,詞語教學在整個小學語文教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字、句、段、篇”教學的橋梁和紐帶,是學生理解句子、領會課文內容、體悟作者情感的重要途徑。因此,語文老師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引領學生“沉入詞語的感性世界”,在各種簡約有趣的學習活動中主動地、富有個性地學習,不斷觸摸詞語的溫度、點染詞語的亮度、開掘詞語的深度、提升詞語的效度,努力讓詞語成為學生言語表現的鮮活元素,從而更好地促進自我認知能力和思維能力的發展。
一、對接生活,讀“透”詞語
一篇課文里往往有最富表現力、最能幫助讀者理解整個作品主題的關鍵詞句,它們是文章的“文眼”,是作者著力刻畫的中心點、觀察的出發點、選材的側重點、內容的核心點、結構的銜接點、情感的升華點、思想的閃光點、主題的凝聚點。在教學中,如果能緊扣文眼突破開去,便能牽一發而動全身,啟迪學生感悟知識的靈性,收到舉一反三、刪繁就簡的效果。
在教學《嫦娥奔月》時,我根據教學目標,遵循文本的規定性和編者的意圖,緊扣“威逼”這個“文眼”,用心選擇文本中的語言文字,引導學生切己體察、揣摩探究、想象領悟,激活學生的生活經驗、閱讀積累和認知圖式,使抽象的語言文字創造性地生成各自理解的鮮活的情境與畫面,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將自己融入文本角色。例如,學生會用“踢”“闖”“架”“兇相畢露”“惡狠狠”“嚷”等詞語以及逢蒙的語言,生動再現逢蒙威逼的全過程,從而準確表現了逢蒙的奸詐與貪婪。
二、品味比較,讀“深”詞語
唯有辨字詞于毫發之間,才能析義理于精微之處。語文學科的本位就是對文本語言的品析與體味,只有語言品味做到位了,才能讓學生感知到語言文字背后的價值取向和人文精神,引發學生對母語學習和玩味的興趣,從而使我們的語文課充滿更濃郁的語文味。而比較就是語言品味中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它通過對語言材料的比較,培養學生辨析語言的能力,讓他們會心作者在語言運用上的精妙之處,并開始主動探索語言的運用方式,從而提高自己的閱讀鑒賞能力和寫作表達水平。
在教學《司馬遷發奮寫〈史記〉》時,我緊扣一個“埋”字進行一番咬文嚼字,不僅咬出了字義,還嚼出了意蘊。課上,我抓住課堂生成的有利時機,因勢利導,為學生創設情境,引領學生走進“埋藏屈辱”的意象世界,讓他們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想象“埋”的過程,并在“埋”與“藏”“關”“壓”的比較中,揣摩到“埋”比其他字更能表現司馬遷強忍內心痛苦的不容易:痛苦、屈辱一次又一次爬上心頭,可是司馬遷一次又一次把它們“深深地埋在心底”。此時,“埋”這個詞不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抽象的漢字符號,而是一幅幅生動形象的畫面,深深地印在他們的腦海中,嵌入他們的心靈里,成為他們精神世界鮮活的生命元素。
三、朗讀聯想,讀“活”詞語
特級教師于永正老師曾說過:“任何一種語文能力的得來,都離不開讀。讀,它本身既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方法——學習語文的根本方法。”在聲情并茂的吟誦中,在抑揚頓挫的涵詠中,精湛的語言、優美的文字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的語言素質。
在教學《狼牙山五壯士》時,我在看到學生已經理解了“斬釘截鐵”這個詞語后,便不失時機地引導他們通過朗讀升華內心的感悟。學生通過想象品讀,激活已有表象,創造新的形象,使“復活”詞語的本來面目生動地投射在學生的心湖上。他們舒展地聯想,入境地朗讀,讀出了詞語的內涵,讀出了自己的情感。
四、言語表現,讀“厚”詞語
詞語教學的最高境界是“表現”。學生學習詞語不能只停留在“理解”的層面,而是要指向于“言語表現”,否則就會變成沒有生命力的僵死符號。因此,教學詞語要結合課文內容,創設“語用”情境,讓學生在情境中寫話、說話,在說和寫的訓練中讓大腦中的“消極詞匯”能很快地轉化為“積極詞匯”。
在教學《詹天佑》時,我設計了一個教學片斷“讓學生面對塑像寫出想對詹天佑說的話”。在特定的語境中,學生借助詞語進行寫話、說話的訓練,這是一種指向于“表現”的訓練。這種“表現”,不是外加給學生的,而是有著內在的需要,有著明確的表達目的和交流對象,有著特定的話語情境的言語實踐活動。在這種活動中,學生運用學過的語言來表達自己新的思想情感,充分實現了“外部語言”向“內部語言”、“消極語言”向“積極語言”的轉化,使學生更能掌握詞語的內涵和精神。
詞語教學不是機械的給予,也不是簡單的告訴,而是與學生的精神生活和情感領域息息相關的生命活動。教學實踐證明:語言只有融入到兒童的精神生活里,與孩子們的精神同構共生了,才能真正在主體心靈中獲得持久的生命力,成為孩子們的精神元素。
(作者單位:江蘇省南通市竹行小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