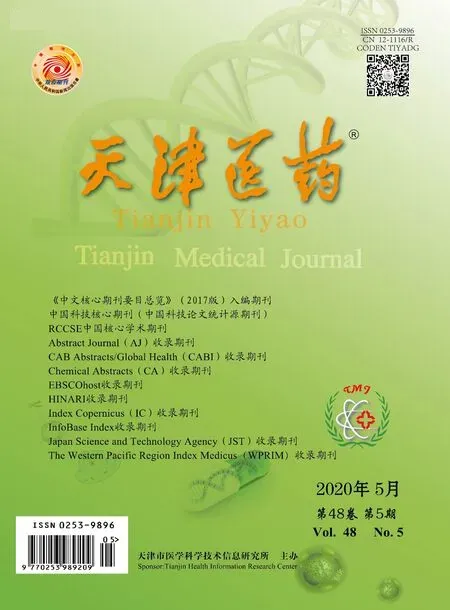骨保護素參與高磷誘導大鼠血管平滑肌細胞鈣化調節的機制初探
竇建新,孫麗萍,劉長山,王秀軍,明義,蘇亮
血管鈣化是動脈粥樣硬化及高血壓、糖尿病血管病變等普遍存在的共同病理表現[1-2],是心血管疾病發病和死亡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也是心血管事件發生的重要預測因素[3]。既往認為血管鈣化是一個被動的、不可避免的過程,然而最近研究顯示血管鈣化類似于骨發育、軟骨形成,是一個主動的、可調節、可預防的過程。骨保護素(OPG)是由380 個氨基酸組成的一種分泌型糖蛋白,是腫瘤壞死因子受體超家族的新成員,廣泛分布于心、血管、肺、腎、肝、腦和骨骼等組織細胞中。最近研究顯示OPG 不僅參與骨的形成,而且與血管鈣化關系密切[4-6]。然而其在血管鈣化進程中潛在的機制尚不明確。本研究以β-磷酸甘油誘導大鼠血管平滑肌細胞(VSMC)鈣化模型,探討OPG干預對VSMC鈣化的影響及機制。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動物和材料 6只健康雄性清潔級SD大鼠(體質量100~150 g)購自上海斯萊克實驗動物有限責任公司。胎牛血清、高糖DMEM、胰蛋白酶-EDTA購自美國Gibco公司,SP免疫組織化學染色試劑盒、山羊抗小鼠IgG二抗購自北京中杉金橋生物技術有限公司,BCA蛋白質定量檢測試劑盒購自上海碧云天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茜素紅S、OPG購自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術有限公司,β-磷酸甘油購自美國Sigma公司,堿性磷酸酶(ALP)檢測試劑盒購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兔抗大鼠GAPDH多克隆抗體購自美國Sigma公司,兔抗大鼠Notch1抗體購自美國CST公司,兔抗大鼠RBP-JK抗體、山羊抗大鼠Msx2抗體購自美國Santa Cruz公司,兔抗大鼠Jagged1單克隆抗體購自北京博奧森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小鼠抗大鼠α-平滑肌肌動蛋白(α-SMA)單克隆抗體、山羊抗兔IgG二抗、兔抗山羊IgG二抗購自武漢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2 原代大鼠主動脈VSMC 的培養鑒定及鈣化模型的建立 無菌條件下取出大鼠胸主動脈,置于無菌培養皿中,PBS沖洗,眼科剪剝除主動脈外膜,縱向剪開主動脈,鈍物刮除內膜,PBS 沖洗;眼科剪剪成約1 mm×1 mm×1 mm 大小的組織塊,將組織塊平鋪于培養皿底部,滴加少量胎牛血清,覆蓋皿底,置于37 ℃、5%CO2培養箱中4~6 h(如組織貼壁不牢可延長時間);待組織與培養皿底貼附后,沿培養皿壁加入含20%胎牛血清的DMEM 培養液,置于37 ℃、5%CO2培養箱中培養;絕對靜置培養3 d,此后每3 d 換液1 次。7 d 后可見到細胞從組織塊邊緣長出,待大多數組織塊邊緣的細胞達4~5層以上時,用移液管輕輕移動組織塊,棄去組織塊與培養液,更換新鮮培養液,隔日換液1 次。細胞呈單層生長狀態達到80%融合時即可傳代。細胞為梭形、不規則三角形,胞質向外伸出3個左右長短不等的突起,細胞呈束狀排列,細胞匯合成片后相互重疊生長,呈典型的“峰-谷”樣表現。通過形態學及對VSMC 進行α-SMA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鑒定。貼壁于蓋玻片的原代VSMC,PBS 沖洗3 次,4%多聚甲醛固定,3%H2O2孵育,山羊血清封閉,α-SMA 單抗(1∶100)孵育,PBS沖洗,二抗孵育,辣根過氧化物酶標記鏈霉卵白素孵育,DAB顯色,脫水,透明,封片鏡檢,α-SMA陽性染色以胞質出現棕黃色或棕褐色為準。95%為陽性,純度符合實驗要求。
VSMC鈣化模型建立與實驗分組:將細胞以5×104/L接種于6 孔細胞培養板中,選擇消化后生長良好的第4~8 代VSMC,以含10 mmol/L β-磷酸甘油的DMEM 培養基培養誘導鈣化10 d。實驗分為5 組:PBS 為對照組,以10 mmol/L β-磷酸甘油誘導鈣化10 d為鈣化對照組,β-磷酸甘油誘導鈣化同時予以劑量梯度(1、4、8 μg/L)的OPG干預為OPG干預組。
1.3 茜素紅染色 吸棄培養基并用PBS沖洗3次。95%乙醇固定15 min,去離子水洗滌2次,加入1%茜素紅S溶液,室溫避光30 min,去離子水洗去染液,顯微鏡下觀察鈣結節染色情況。
1.4 鄰甲酚酞絡合酮比色法檢測細胞鈣沉積含量 每組設3個復孔,細胞干預10 d后,進行鈣含量測定。給予PBS洗滌3 次,每孔加入0.6 mol/L 的鹽酸1 mL 進行細胞脫鈣,次日收集并檢測其鈣含量。PBS 洗滌6 孔板中的細胞3 次后,加入0.1 mmol/L NaOH 或0.1%SDS裂解細胞,提取上清液,BCA 法檢測細胞蛋白含量。結果以鈣含量/蛋白含量表示。
1.5 ALP 活性測定 用PBS 洗滌6 孔板中的細胞3 次后,加入0.1%Triton X-100裂解液500 μL裂解細胞,離心后收集上清。按試劑盒說明書操作,比色法測定ALP活性。BCA法檢測細胞蛋白含量,用蛋白量校正ALP含量。
1.6 Western blot 各組細胞用預冷的PBS沖洗2遍,加入RIPA裂解液,刮取細胞提取總蛋白,取上清后采用BCA法進行蛋白定量。取30 μg蛋白進行SDS-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轉膜,封閉,加入兔抗大鼠Notch1抗體(1∶400)、兔抗大鼠Jagged-1單克隆抗體(1∶200),兔抗大鼠RBP-JK抗體(1:300)、山羊抗大鼠Msx2抗體(1∶400)4 ℃孵育過夜,加入二抗IgG(1∶5 000),室溫孵育1 h,ECL試劑盒顯影,以GAPDH為內參進行數據標準化,以對照組為參照樣本,計算各組目的蛋白的相對表達水平。
1.7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16.0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處理,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多組間均數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較采用SNK-q檢驗,檢驗水準為雙側α=0.05。
2 結果
2.1 鈣化模型誘導 普通倒置顯微鏡下可見VSMC鈣化模型及茜素紅染色后VSMC的紅色鈣化結節,見圖1。

Fig.1 Calcification model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induced by β-glycerophosphate圖1 β-磷酸甘油誘導VSMC形成鈣化模型
2.2 OPG干預對大鼠VSMC鈣化的影響 給予劑量梯度的OPG 干預后,β-磷酸甘油誘導的大鼠VSMC鈣化結節減少,見圖2。

Fig.2 Effects of OPG on the calcification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induced by β-glycerophosphate圖2 OPG對β-磷酸甘油誘導大鼠VSMC鈣化情況的影響
2.3 OPG 干預β-磷酸甘油誘導大鼠VSMC 鈣化各組鈣含量及ALP 活性比較 與對照組比較,鈣化對照組及OPG 干預組的大鼠VSMC 鈣含量明顯增加,ALP活性明顯增強(P<0.05)。與鈣化對照組比較,OPG 干預組(1、4、8 μg/L)的大鼠VSMC 鈣含量明顯減少,ALP 活性明顯減弱(P<0.05),且呈劑量依賴性,其中以8 μg/LOPG干預組最為明顯,見表1。
Tab.1 Effects of OPG on the calcification and ALP expression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induced by β-glycerophosphate表1 OPG干預β-磷酸甘油誘導大鼠VSMC鈣化各組鈣含量及ALP活性的比較(n=8,±s)

Tab.1 Effects of OPG on the calcification and ALP expression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induced by β-glycerophosphate表1 OPG干預β-磷酸甘油誘導大鼠VSMC鈣化各組鈣含量及ALP活性的比較(n=8,±s)
**P<0.01;a與對照組比較,b與鈣化對照組比較,c與1 μg/L OPG干預組比較,d與4 μg/L OPG干預組比較,P<0.05
組別鈣含量(mg/g蛋白)ALP活性(U/g蛋白)對照組鈣化對照組1 μg/L OPG干預組4 μg/L OPG干預組8 μg/L OPG干預組F 10.34±1.82 36.93±4.03a 29.42±1.91ab 28.37±2.89ab 17.51±3.99abcd 93.410**10.37±2.62 109.75±5.49a 81.25±5.90ab 61.75±7.26abc 43.37±7.56abcd 311.432**
2.4 OPG 干預β-磷酸甘油誘導大鼠VSMC 鈣化后Notch1/RBP-JK 通路蛋白表達情況 與對照組比較,鈣化對照組大鼠VSMC Notch1、RBP-JK、Jagged1、Msx2 蛋白表達水平明顯升高(P<0.05)。與鈣化對照組比較,給予1、4、8 μg/L OPG干預后,細胞Notch1、RBP-JK、Jagged1、Msx2 蛋白表達水平明顯下降(P<0.05)。此外,與1 μg/LOPG 干預組比較,較高劑量(4、8 μg/L)OPG干預組的Notch1、RBPJK、Jagged1、Msx2 蛋白表達水平明顯下降(P<0.05),見圖3,表2。

Fig.3 Expressions of Notch1/RBP-JK pathway after OPG intervention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圖3 OPG干預VSMC后Notch1/RBP-JK通路蛋白表達情況
Tab.2 Comparison of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Notch1/RBP-JK pathway after OPG intervention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表2 OPG干預VSMC后各組Notch1/RBP-JK通路蛋白表達的比較(n=6,±s)

Tab.2 Comparison of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Notch1/RBP-JK pathway after OPG intervention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表2 OPG干預VSMC后各組Notch1/RBP-JK通路蛋白表達的比較(n=6,±s)
**P<0.01;a與對照組比較,b與鈣化對照組比較,c與1 μg/L OPG干預組比較,P<0.05
組別Notch1 RBP-JK Jagged1 Msx2對照組鈣化對照組1 μg/L OPG干預組4 μg/L OPG干預組8 μg/L OPG干預組F 0.30±0.07 0.86±0.07a 0.62±0.07ab 0.47±0.11abc 0.41±0.06abc 44.604**0.40±0.08 0.95±0.12a 0.69±0.09ab 0.53±0.10bc 0.46±0.06bc 34.480**0.60±0.09 1.21±0.07a 0.89±0.09ab 0.64±0.16bc 0.52±0.13bc 37.558**0.20±0.04 0.76±0.10a 0.56±0.09ab 0.40±0.06abc 0.37±0.03abc 53.523**
3 討論
血管鈣化在動脈粥樣硬化、糖尿病血管病變、慢性腎臟病和血管損傷中普遍存在。當血管鈣化發生后,血管壁彈性及脆性增加,會損害血管的舒縮運動,易導致心肌缺血、斑塊破裂、血栓形成,是心血管事件、腦卒中發生的重要預測因子。深入了解血管鈣化的發病機制,尋找血管鈣化相關抑制因子可能成為治療血管鈣化的潛在靶點。血管鈣化的中心環節是VSMC 在高磷等因素作用下發生表型分化,轉化為成骨樣細胞、表達骨化及礦化相關蛋白及發生凋亡的過程,因此本研究采用β-磷酸甘油誘導大鼠VSMC鈣化模型為研究對象,探討OPG干預對VSMC鈣化的影響。
OPG 是骨代謝疾病的重要調節因子,在抑制骨吸收、防止骨量丟失中有重要作用。目前越來越多的臨床和基礎研究均顯示OPG 與心腦血管疾病及血管壁的鈣化關系密切[7-9]。Caraiola等[10]研究顯示OPG 水平與冠心病進展呈正相關。另有研究顯示OPG水平是冠心病和外周動脈疾病患者死亡風險的強預測因子[11]。Krzanowski等[12]研究OPG水平與組織學評價的橈動脈鈣化和頸動脈內膜中層厚度的關系發現,血清OPG 水平升高與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的存在和橈動脈鈣化的嚴重程度獨立相關,認為循環OPG 可作為中動脈鈣化和動脈粥樣硬化的標志物。然而也有不同報道,Kurnatowska等[13]在為期30個月的隨訪研究中發現,最初無血管鈣化而至研究結束時仍無鈣化發生患者的OPG 水平一直明顯低于鈣化的患者,從而認為OPG 可以作為血管鈣化的一個重要預測因子。動物研究發現OPG 基因缺陷小鼠除了出現嚴重的骨質疏松之外,還會出現腎動脈和主動脈中膜鈣化,而且鈣化的動脈是內源性OPG 表達的部位[14],這表明OPG可能有保護這些動脈免受病理性鈣化的作用。Price 等[15]研究發現OPG 干預可顯著抑制華法林和維生素D誘導小鼠血管鈣化的發生,OPG 在防止動脈粥樣硬化和鈣化中可能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中應用β-磷酸甘油誘導大鼠VSMC發生鈣化過程中,成骨標志物ALP 及鈣含量顯著增加,表明大鼠VSMC鈣化過程中有礦物質沉積,伴有VSMC 表型改變和成骨因子激活。給予OPG 干預后,ALP及鈣含量顯著減少,說明OPG在高磷誘導的VSMC 鈣化的過程中發揮抑制作用。但目前有關OPG參與血管鈣化調節的分子機制尚未闡明。
血管鈣化過程中多種細胞因子及通路參與調節,近年來多項研究顯示Notch1-RBP-JK 通路在血管鈣化中起調節作用[16-17]。Notch1-RBP-JK 是一個高度保守的信號轉導通路,當Notch1 受體與配體結合后,受體的胞內區與轉錄抑制因子(RBP-JK)相互作用使轉錄激活。Msx2 是Notch1-RBP-JK 的下游因子,是血管鈣化的核心調控因子,Notch1-RBP-JK通路可以通過增強Msx2 表達,促進血管鈣化形成[18]。本研究結果顯示,β-磷酸甘油誘導的VSMC鈣化過程中存在Jagged1-Notch1-RBP-JK 通路的激活,Msx2表達升高。給予OPG 干預后Notch1-RBPJK及Msx2信號通路的激活被抑制,Msx2表達降低,Msx2 降低將抑制VSMC 向成骨樣細胞分化,故給予OPG干預后,隨著Msx2表達的降低,細胞鈣化結節、鈣含量及ALP 活性均明顯下降,且該抑制作用有一定的劑量依賴性。因此,推測OPG 可能通過抑制Jagged1-Notch1-RBP-JK 通路激活參與高磷誘導大鼠VSMC鈣化的調節。
OPG 水平在眾多心腦血管疾病中顯著增高,其不再是單純的骨調節因子,而可能是骨質疏松、血管鈣化橋梁性因子,在老年性骨質疏松及急慢性血管疾病中發揮重要作用。研究OPG 作為骨代謝、血管調控的橋梁作用,探究OPG 參與血管鈣化調節的機制,有助于加深對血管類疾病的整體思考和研究,對疾病的診治有指導意義。